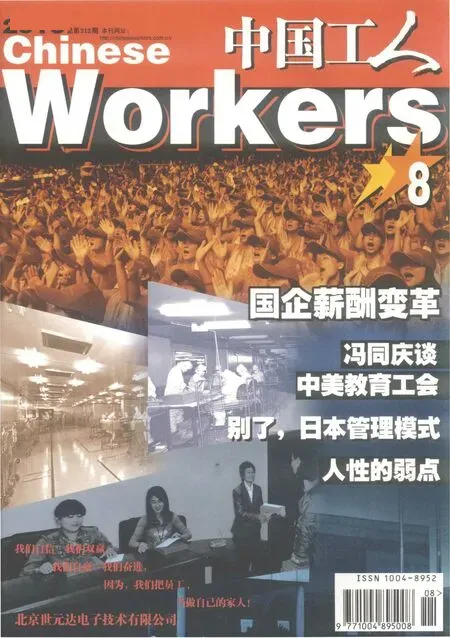央企屬性與高管薪酬:理性的思考與現行制度的重新評價
中央財經大學會計學院教授 魯桂華
央企屬性與高管薪酬:理性的思考與現行制度的重新評價
中央財經大學會計學院教授 魯桂華
企業高管薪酬似乎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
世界銀行副行長法喬杜里表示,有些公司高管的薪酬水平已到了不道德的程度,而歐盟官員更是將之斥為“社會禍患”。美國總統奧巴馬則向那些高薪的企業高管喊話:“你們財富已超百萬,同時還在著手解雇工人,你們至少應該愿意作出一些犧牲吧”。
在我國,央企高管薪酬問題,也一直是民眾、媒體和有關政府主管部門關注的焦點。這些關注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目前央企高管薪酬水平是不是過高?有人用高管薪酬和員工薪酬的比例來判斷央企高管薪酬是否恰當;有人通過比較民企和央企高管薪酬來評價央企高管薪酬是否過高;有人比較不同行業央企的薪酬,研究決定央企高管薪酬的行業因素,進而評估這些因素是否具有合理性;有人考察央企高管薪酬與央企業績是否同步增長來評估薪酬是否達到了預期的激勵效果。顯然,前三種比較關注的焦點似乎是公平性問題,第四種比較似乎更重視薪酬是否具有效率的問題。央企高管薪酬水平的設計與監控應突出公平還是效率?如果強調效率,又應當采用何種效率標準?
第二,如何科學合理地確定央企高管薪酬?比如央企高管薪酬除了基本薪酬之外,是否還包含與業績相關的部分?是否還應該包括長期的激勵?央企高管的薪酬應該由哪些部分組成?是由政府以立法的方式來規范央企高管的薪酬,還是國資委依據每一個央企的具體情況來確定央企高管薪酬,還是由國資委授權企業董事會來確定央企的薪酬水平?高管薪酬應該按何種標準來確定?僅依賴業績是否科學?如果需要考慮業績,那么如何界定央企的業績?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上述問題,如僅僅將思考聚焦在這些問題本身,永久不可能有科學的答案。我們應該首先厘清央企的屬性與央企的目標,然后才能科學地界定央企高管薪酬的標準。惟有如此,才能科學地評價央企高管薪酬水平是否恰當。
第一,央企不僅僅是企業,它還具有許多非企業的屬性,或者說央企還具有公共品的屬性。
央企為社會提供的產品和服務,一部分通過其產品與服務的價格得到了補償,但有時候,其產品與服務的價格,并沒有完全補償它們所提供的產品與服務的成本。人們經常說,央企除了盈利之外,還肩負著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就是對這種外部性的直觀描述。如國家電網、中國神華、中石油等央企,除了盈利目標之外,它們還承擔著保障國家能源安全,為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充足、穩定的能力等社會責任。
第二,央企的屬性決定著央企的社會職能與目標,進而決定著央企高管薪酬的基本原則。
一般而言,處于競爭性行業的央企基本不具備公共職能,我們可以將其界定為企業,其占有的公共資源主要是國有資本,其社會職能是為社會提供產品或服務,其成本主要通過產品或服務的價格補償,其社會目標與財務目標是一致的,即為國有資本創造價值增值,其核心的業務評價指標自然是價值增量,高管承擔的主要是企業家的職能,其薪酬給付標準與激勵目標也應該著眼于價值創造。
而處于壟斷性行業的央企則在不同程度上承擔了公共職能。這些承擔了公共職能的企業,它不僅占用了國有資本,還占用了許多公共資源,比如國家特許其壟斷經營某些行業的權利,其目標應該是提升社會福利,而盈利與價值創造只是社會福利的一個部分而不是全部,其關鍵業績指標也應該是社會福利指標而不是盈利、價值指標。這些企業的高管,兼具公務員與企業家的雙重屬性,其薪酬也應該體現這一特點,即應當更多地激勵他們承擔社會責任而不是激勵他們去逐利。
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強調國有企業“不與民爭利”,是對這些央企公共屬性的一種認知和自覺,但同時也恰恰說明此前央企確實存在與民爭利的現象。央企與民爭利,一方面,是對國家特許其經營某些壟斷行業這一公權利的濫用,另一方面也表明現行的央企高管激勵政策偏離了這些企業的公共職能,不恰當地強調了這些企業的私人屬性。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們現行的央企高管薪酬制度設計,幾乎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缺乏清晰的理性思考,對央企屬性與社會功能缺乏科學的認知。
第三,確定央企高管薪酬的基本原則應當是效率優先。
判斷是否具有效率的基本標準應該是帕累托改進。假設某企業上年度創造的社會凈福利為100億元,如果本年度該企業創造的、未剔除高管薪酬的社會福利增加到200億元,其中高管以薪酬的方式拿走60億元,這就是一個帕累托改進,即高管的福利增加了60億元,而社會凈福利增加了40億元。如果不支付高管60億元的薪酬,就沒有40億元的社會福利凈增加。兩種情形,孰優孰劣,相信讀者不難辨別。我們還可以看一個更為極端的情形:如果支付給高管的薪酬為99億元,剔除高管薪酬之后的社會福利凈增加1億元,仍然是一個帕累托改進,仍然是一個效率的提升!
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只看高管拿走了多少薪酬,更應該學會去看高管拿走這些薪酬后,還給我們創造了多少福利增量。只要增量的高管薪酬小于他們所創造的福利增量,全社會的福利,包括高管的福利,都在增進,我們為什么不要這種福利增進呢?
李榮融表示,在過去三年里,央企1500多名高管的總薪酬每年增長4500萬元左右,卻換來了每年1500億元的利潤增長。如果利潤是社會福利的恰當度量,那么李榮融無疑在替央企高管們在向人們說明,這是一個富于效率的薪酬制度,高管與社會公眾的福利都在增進!然而,值得我們質疑的恰恰是這里的假設。我們的問題是,利潤是社會福利的恰當度量嗎?
第四,利潤并不是衡量央企高管業績的恰當指標,經濟增加值也許更為科學。

我們不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央企增加了1500億元的利潤,假設他們占用的資本增加了30000億元,即央企的投資報酬率僅為5%。進一步思考這樣一種情形,假設民營企業創造1500億元的利潤增量只需要占用15000億元的資本,即民營企業的投資報酬率為10%。即央企占用的30000億元的資本,創造的利潤增量,僅相當于民企15000億元資本創造的利潤增量!如果我們假設,央企應該至少達到和民企同等的投資報酬率,那么央企占用的30000億元的資本,應該創造30000×10%=3000億元的利潤!從央企實際利潤增量中,減去央企應該賺取的利潤,即扣除央企所占用資本的機會成本,即為經濟利潤或經濟增加值!用公式表達,就是:
經濟增加值=1500億元的利潤增量-30000億元的資本
占用×10%的必要報酬率=-1500億元
如果我們的這一系列假設是成立的話,那么國資委就需要反思了,4500萬元的央企高管薪酬增量,激勵出1500億元的利潤增量,要是放在民企,則能夠激勵出3000億元的利潤增量。換言之,4500萬元的增量薪酬,激勵出央企-1500億元的經濟利潤。這顯然不是一個富于效率的安排!只要將國資委掌門人評價央企高管薪酬的經濟效果的評價標準從利潤指標更改為經濟增加值,我們就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李榮融認為4500萬元的增量薪酬不高這一結論,可能是完全錯誤的。我們豈能如此簡單、草率地評價央企高管的薪酬?
第五,如何評價央企占用的資本?
正如同我們對央企屬性界定時指出的那樣,由于央企具有公共屬性,因而國家賦予央企許多社會職能,并且特許央企壟斷經營某些行業的權利。這種權利是否能夠為央企帶來超額利潤?能夠帶來超額利潤的資源,是不是央企占用的資產?我們在計算央企占用的資源,以及計算這些資源應該賺取的最低利潤量時,能否忽略這些資源?以中國移動為例,如果移動通信牌照發放的門檻更低,中國移動還能日進三個億的純利嗎?因此筆者經常說,許多央企最大的資產,是國家特許其經營某些壟斷行業的權力,而這一資產恰恰沒有反映在央企的資產負債表中。如果考慮這一資產以及這一資產應該賺取的最低利潤,央企創造的經濟增加值將會更低,央企高管薪酬將會顯得更高,其激勵的效果也就顯得更糟!
仍援引上例,假設央企占用的這些特許權資產的價值為15000億元,那么央企占用的資本就不再是30000億元而是45000萬元,其經濟增加值為
1500億元的利潤-45000億元的占用資本×10%的必要報酬率=-3000億元。
讀者可以思考,央企占用了壟斷經營某些行業的特許權資源,是不是應該賺取更高的利潤呢?央企的監管部門在考察央企業績時,是不是需要考慮央企占用的、資產負債表內沒有體現的這些特許經營權資產應該賺取的最低利潤?為什么會出現中石化天價吊燈和豪華裝修事件?如果我們在考查中石化的業績時,剔除這些壟斷經營特許權應該賺取的最低利潤,是不是會有助于抑制類似的現象發生呢?
換句話來說,央企的利潤,我們稱之為產出,央企高管勤奮工作的態度、謹小慎微的工作作風,我們稱之為投入。我們應該激勵投入,還是應該激勵產出?基于利潤的薪酬制度,會不會產生激勵的偏差?答案是顯然的,我們應該鼓勵投入,而不是激勵產出。對于央企而言,利潤好,既可能因為高管在努力工作,更有可能是因為央企高管幸運地成為了央企的高管,從而擁有了賺取高額利潤的特許權。從央企的利潤中,扣除其占用資本應該賺取的最低利潤,并且扣除特許壟斷經營權應該賺取的最低利潤,余下的利潤,才有可能是高管努力工作、謹小慎微工作帶來的利潤增量。正是從激勵投入而不是激勵產出的角度來看,央企高管薪酬不應該與利潤掛鉤,而應該與經濟增加值掛鉤,并且在計算經濟增加值時,要考慮特許壟斷經營權的價值。

第六,向國際接軌,如何接軌?
國資委副主任邵寧在解釋央企薪酬是否偏高時,曾經引用過一組數據:“像美國,經營層高管人員和普通人員的差距非常大,尤其是CEO,差距上百倍,而日本差距非常小,大概在20倍上下,韓國更小一些,大概在12倍和13倍左右。這個差距跟我們差不多”。談到歐洲時,邵副主任說:在挪威,“高管和工作十年左右員工的薪酬差距是4-5倍”。
我對邵副主任的這些數據的理解是,與國際接軌并不等價于和美國接軌。央企高管和央企員工一樣,是央企的雇員而不是央企的“老板”。雇員從企業取得薪資而“老板”從企業取得剩余,即扣除各項成本之后的利潤。所以,對央企高管激勵制度的核心應該在于,央企高管的薪酬與經濟增加值相關,以消除利益沖突。換言之,薪酬的變動,較之于薪酬水平,可能更為重要。也就是說,經濟增加值增減變動時,央企薪酬隨之而增減變動,就能夠引導央企高管去創造社會福利,就能夠起到激勵效果;反之,薪酬再高,但與經濟增加值無關,也不會起到任何的激勵作用。
第七,到底應該由誰來制定央企高管的薪酬制度與薪酬標準?是由董事會來制定薪酬標準嗎?
筆者不能認同這種觀點。理由如下:其一,央企是由國家或政府授權高管特許經營的,因此政府也就擁有通過制定法規和預算來管理央企薪酬的權力。其二,在內部人控制的背景下,董事會可能是由管理層任免的,因此董事會難以獨立于管理層。此時,由董事會制定高管薪酬,等價于高管自己獎勵自己。正是出于這些思考,由政府以法律、法規或預算的方式調控高管薪酬,在這一約束的框架內,由央企董事會確定薪酬,可能較之完全授權董事會要好一些,雖然這樣做可能會令國資委難受,但豈能因為難受而逃避應該承擔的責任?
總而言之,央企的企業屬性與央企的公共職能,決定了央企的目標和央企高管的業績評價標準。對央企屬性的理性思考,是我們確立央企高管薪酬制度的標桿,也是我們評估現行央企高管薪酬制度的標準。正是基于這一認識,筆者認為,現行央企高管的薪酬制度,沒有充分反映央企屬性,這是諸如“與民爭利”、“天價吊燈”等現象的源泉,也是導致央企高管薪酬偏高的內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