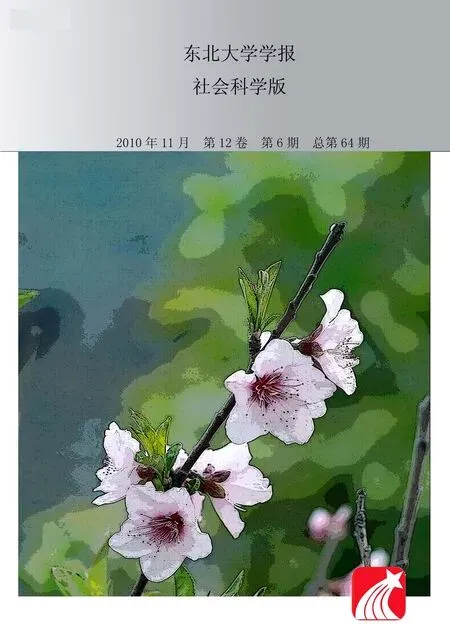政策網(wǎng)絡(luò)視角下的社區(qū)治理失靈問題研究
楊海濤,李德志
(1.吉林大學(xué)行政學(xué)院,吉林長春 130012;2.吉林財經(jīng)大學(xué)公共管理學(xué)院,吉林長春 130117)
一、 政策網(wǎng)絡(luò)理論及其適用性
“政策網(wǎng)絡(luò)”(policy network)是將網(wǎng)絡(luò)理論引入公共政策科學(xué)而形成的一種分析途徑,一般認(rèn)為,政策網(wǎng)絡(luò)是指政策過程中國家與社會、政府和其他行動者之間基于協(xié)商、利益和資源依賴等而產(chǎn)生不斷互動的正式和非正式關(guān)系類型的總稱[1]。
1. 政策網(wǎng)絡(luò)理論的發(fā)展
政策網(wǎng)絡(luò)理論興起于20世紀(jì)70年代,產(chǎn)生于美國,發(fā)展于英國,現(xiàn)流行于西方學(xué)界。近年來,政策網(wǎng)絡(luò)逐漸取代多元主義、統(tǒng)合主義及其他傳統(tǒng)模式,開始成為西方政策分析領(lǐng)域中的核心范式。其相關(guān)研究可分為以下三類:
(1) 美國學(xué)者的微觀層次研究
美國學(xué)者從政策次系統(tǒng)的角度出發(fā),在微觀層面研究政策過程中主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強調(diào)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關(guān)系而不是制度間的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特別是赫柯羅(Heclo)提出議題網(wǎng)絡(luò)的概念,給政策次系統(tǒng)的本質(zhì)賦予了新的定義和解釋,引發(fā)了歐洲學(xué)者的學(xué)術(shù)興趣,推動了政策網(wǎng)絡(luò)研究的深化和發(fā)展[2]。
(2) 英國學(xué)者的中觀層次研究
英國學(xué)者的政策網(wǎng)絡(luò)研究建立在對多元主義(pluralism)和合作主義(corporatism)的批評之上,是對兩者的一種替代[3]。英國學(xué)者重視從中觀角度分析利益集團(tuán)與政府之間的關(guān)系,政治機構(gòu)間的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是政策網(wǎng)絡(luò)構(gòu)成的關(guān)鍵部分[4],其代表人物是羅茲(Rhodes)。在英國學(xué)者的發(fā)展和推動下,美國傳統(tǒng)的鐵三角和議題網(wǎng)絡(luò)逐漸被政策網(wǎng)絡(luò)和政策社群所取代。
(3) 歐洲大陸學(xué)者的宏觀層次研究
歐洲大陸學(xué)者的研究以德國和荷蘭為代表,主要從宏觀層面研究政策網(wǎng)絡(luò),但兩國學(xué)者的觀點稍有差異。德國學(xué)者將政策網(wǎng)絡(luò)視為一種與政府、市場并立的第三種社會結(jié)構(gòu)形式和新的國家治理模式[5],可以彌補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而荷蘭學(xué)者則認(rèn)為政府在治理中已不能扮演萬能的角色,政策主體之間的協(xié)商至關(guān)重要。因此,成功治理的關(guān)鍵在于實現(xiàn)有效的網(wǎng)絡(luò)治理[6]。
2. 政策網(wǎng)絡(luò)分析框架的適用性
政策網(wǎng)絡(luò)理論一方面為我們提供了富有解釋力的分析模型,另一方面又能引導(dǎo)出應(yīng)對多元參與主體的復(fù)雜問題的治理策略。因此,它既是一個解釋性的框架,同時也是一個建構(gòu)性框架,可以根據(jù)這一框架構(gòu)建一個具有實際操作意義的政策過程。一般認(rèn)為,政策網(wǎng)絡(luò)有兩個適用條件:一是復(fù)雜的政策過程,另一個則是多元參與主體。
社區(qū)是國家權(quán)力末梢的管理(控制)領(lǐng)域,也是城市居民的生活場所。作為國家權(quán)力與民間公共權(quán)力交接的場域,社區(qū)治理過程正逐漸發(fā)育為一個相當(dāng)?shù)湫偷恼呔W(wǎng)絡(luò),而其體現(xiàn)出來的特征與政策網(wǎng)絡(luò)的適用條件是高度吻合的。
第一,盡管近幾年來我國在社區(qū)治理方面不斷摸索,并取得了一定的經(jīng)驗,但是仍然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矛盾和問題。社區(qū)治理行政化色彩濃厚,行政越位或缺位現(xiàn)象嚴(yán)重,缺乏參與式治理的制度規(guī)范和協(xié)調(diào)規(guī)則,社區(qū)秩序混亂不堪,公共服務(wù)缺乏,居民糾紛長期得不到解決等等,對基層社區(qū)建設(shè)造成了嚴(yán)重危害。將政策網(wǎng)絡(luò)分析框架引入社區(qū)治理研究,在“去行政化”的基礎(chǔ)上反思社區(qū)治理危機,將是解決復(fù)雜的社區(qū)問題、促進(jìn)社區(qū)善治的首要選擇。
第二,從國內(nèi)眾多實證經(jīng)驗來看,社區(qū)治理過程既有別于傳統(tǒng)科層治理下的行政強制,也不是理想的自治行為集合,而是發(fā)生在多元治理主體之間權(quán)力和利益關(guān)系的互動博弈之中。在社區(qū)治理過程中,忽視多元利益主體,仍然沿用單線的、強制性的“決策—執(zhí)行”機制,是當(dāng)代出現(xiàn)社區(qū)治理失靈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政策網(wǎng)絡(luò)分析框架有利于從“實然”的角度提供更完整、更真實的解釋。
第三,在現(xiàn)實的代議制民主實踐中,由于公民參與政治的途徑有限,又難以對民意代表、民選官員和政治家進(jìn)行有效的監(jiān)督和制約,因此,“政策民主”就成為一個突破口。借助政策網(wǎng)絡(luò)分析有利于在地方層面吸納更多的非政府主體參與政策過程,從而提高社區(qū)充權(quán)(community empowerment),真正實現(xiàn)“居住改變中國,民主從社區(qū)開始”。
二、 我國社區(qū)治理失靈的政策網(wǎng)絡(luò)分析
政策網(wǎng)絡(luò)最終將體現(xiàn)于政策網(wǎng)絡(luò)與政策結(jié)果的關(guān)系,馬什(Marsh)曾指出:“政策網(wǎng)絡(luò)的根本作用就是用來解釋政策后果”[7]。對此,有兩種不同的觀點:結(jié)構(gòu)決定論認(rèn)為政策網(wǎng)絡(luò)的結(jié)構(gòu)影響政策結(jié)果,代表人物為馬什和羅茲(D. Marsh & R. Rhodes);而行為決定論認(rèn)為政策網(wǎng)絡(luò)中的行動者的資源交易和互動影響政策結(jié)果,代表人物為都丁(J. Dowding)。前者過于重視政策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的制約性,而忽視了行動者的意圖性和能動性;后者則專注于行動者的目的性行為,而忽視了他們之間的關(guān)系結(jié)構(gòu)。
基于以上兩種解釋途徑各自的缺陷,相關(guān)學(xué)者提出了一些修正政策網(wǎng)絡(luò)分析的具體途徑、框架或模型,以進(jìn)一步加強政策網(wǎng)絡(luò)對政策結(jié)果的解釋力。其中,馬什和史密斯(Marsh & Smith)由此發(fā)展出了辯證分析模型(dialectical model),此模型結(jié)合了宏觀政策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中觀政策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及微觀政策網(wǎng)絡(luò)行動者三個層面,強調(diào)政策網(wǎng)絡(luò)與政策結(jié)果之間的關(guān)系不是簡單的、單向的,而是蘊涵著三者的辯證的交互關(guān)系[8]。為此,本文將從辯證分析的視角來解釋我國社區(qū)治理政策失靈的原因。
1. 政策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分析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jīng)濟(jì)體制,國家對城市基層社會的整合和控制基本上是通過單位制度實現(xiàn)的。1952年前后新中國對私人資本進(jìn)行了一次徹底清理,此后直到1978年,中國境內(nèi)所有企業(yè)均為國營或集體所有制企業(yè)。此外,事業(yè)單位、機關(guān)團(tuán)體、學(xué)校、商店等一切社會組織均隸屬某個上級單位,最終歸屬于中央政府。相互獨立的單位組織分別掌握著特定職業(yè)群體的政治、經(jīng)濟(jì)權(quán)利,并承擔(dān)了大部分福利供給任務(wù)。此時,街居制度,即街道辦事處指導(dǎo)下的居委會管理體制,其作用的發(fā)揮只是為了把那些沒有單位的街道居民組織起來,以減輕區(qū)政府和公安派出所的負(fù)擔(dān)。單位制與街居制相互補充、交叉配合,完整地嵌入基層社會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一張嚴(yán)密的管理網(wǎng)絡(luò)。不同群體間的交往和聯(lián)系較少,社會生活高度同質(zhì)化、簡單化,社會公共事務(wù)和公共問題的發(fā)生幾率也保持在低度水平。
長期的計劃經(jīng)濟(jì),讓人們已經(jīng)習(xí)慣于一種格式化的、有組織、有紀(jì)律的社會環(huán)境,習(xí)慣于把自己“捆綁”在單位上的工作和生活模式。然而,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啟動后,國家和社會開始步入一個不自愿的結(jié)構(gòu)分化進(jìn)程。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社會環(huán)境發(fā)生巨變,“社區(qū)單位化”或“單位社區(qū)化”逐漸土崩瓦解。尤其是20世紀(jì)80年代中期開始的國有企業(yè)改革和政府機構(gòu)改革,在社會保障體制沒有健全的背景之下,大量下崗、分流人員脫離了原來那種“溫暖”的有“保障”的體制,一下子變成了無依無靠的社會“棄兒”。除此以外,20世紀(jì)90年代初期開始的人口流動大潮,也給城市政府帶來了大量的管理任務(wù),使得城市綜合治理能力嚴(yán)重不足的狀況更為凸顯。
國家掌控的總體性社會的解體緩解了國家的財政和公共服務(wù)壓力,卻把大量的治世壓力拋向一個羸弱的社會。然而在這種背景之下,社會管理的空白卻沒有得到社會力量的及時彌補。盡管我國在法律上明確規(guī)定社區(qū)為自治共同體,但實際上當(dāng)前社區(qū)治理的行政色彩依然過于濃厚,行政權(quán)力對社區(qū)的微觀管理和干預(yù)過多,社區(qū)體制改革依然在街居體制內(nèi)兜圈子。
2. 政策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分析
政策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是指政策網(wǎng)絡(luò)行動者之間的關(guān)系形態(tài),具有客觀制約性,不同類型的政策網(wǎng)絡(luò)對政策結(jié)果產(chǎn)生不同的影響。
西方學(xué)者對政策網(wǎng)絡(luò)類型的分類多種多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馬什和羅茲的分類,依照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從緊密到松散的次序劃分為五種類型:政策社群(policy community)、專業(yè)網(wǎng)絡(luò)(professional network)、府際網(wǎng)絡(luò)(intergovernmental network)、供應(yīng)網(wǎng)絡(luò)(producer network)和議題網(wǎng)絡(luò)(issue network)[9]。
在街居制向社區(qū)制的轉(zhuǎn)型過程當(dāng)中,我國社區(qū)治理已體現(xiàn)出多元治理主體的趨勢,也涌現(xiàn)出一批社區(qū)建設(shè)的先進(jìn)典型,例如,深圳鹽田模式、北京魯谷街道模式、上海盧灣模式、江蘇南京白下區(qū)模式、浙江寧波海曙模式等等。但總體來看,在社區(qū)治理過程中還存在著以下幾方面共性問題:
第一,由于政府放權(quán)不徹底,以及社區(qū)自身力量還未成長和強大到足以支撐社區(qū)發(fā)展建設(shè)的全部過程,嚴(yán)格來說,我國的社區(qū)治理實踐既不屬于完全的行政性模式,也不屬于完全的自治性模式,而是處于從行政性向自治性的過渡階段。
第二,社區(qū)中的組織機構(gòu)大都與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沒有形成一套完整有效的機制來保證和鼓勵社區(qū)居民和社區(qū)內(nèi)的營利及非營利組織共同參與社區(qū)事務(wù),政府以外的組織和個人在社區(qū)治理中發(fā)揮的作用十分有限。
第三,沒有通過明確多元治理主體的責(zé)權(quán)利來建立網(wǎng)絡(luò)運行機制和制度規(guī)范,社區(qū)內(nèi)的治理主體隸屬于不同的行業(yè)和系統(tǒng),相互之間缺乏橫向聯(lián)系,形成一種“條塊分割”的局面,不利于社區(qū)資源的整合利用。
依據(jù)馬什和羅茲的政策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分類及其特征并結(jié)合我國具體實踐來判斷,我國在社區(qū)治理中形成的政策網(wǎng)絡(luò)比較類似于議題網(wǎng)絡(luò),而非政策社群,具體分析如下:
在組織緊密、較為封閉的政策社群中不存在絕對的支配性力量,治理主體通過信任機制和協(xié)調(diào)對話的方式結(jié)成一個非零和博弈的互動網(wǎng)絡(luò),政府只是網(wǎng)絡(luò)中的對局者之一,盡管可能是最強大的參與者。網(wǎng)絡(luò)成員之間的相互影響非常頻繁,使得政策網(wǎng)絡(luò)能夠持續(xù)、穩(wěn)定,有助于建立網(wǎng)絡(luò)的共同價值觀和信任。在網(wǎng)絡(luò)成員頻繁的相互影響的過程中,網(wǎng)絡(luò)追求的目標(biāo)、實現(xiàn)目標(biāo)的工具、網(wǎng)絡(luò)活動的準(zhǔn)則等等會逐漸制度化,并反過來制約和影響網(wǎng)絡(luò)主體的行為[8]。
而我國的社區(qū)治理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則體現(xiàn)出結(jié)構(gòu)松散、制度化程度較低、政策結(jié)果難以預(yù)測等等議題網(wǎng)絡(luò)特征。擁有資源的不平等導(dǎo)致了網(wǎng)絡(luò)機會和權(quán)力的不平等,網(wǎng)絡(luò)互動的變革性作用比較小,更容易因環(huán)境的變化而產(chǎn)生不穩(wěn)定的關(guān)系。政府的強勢地位明顯,并同其他網(wǎng)絡(luò)成員進(jìn)行零和博弈,導(dǎo)致社區(qū)治理的成本過高、效用下降,甚至產(chǎn)生公地悲劇。
3. 政策網(wǎng)絡(luò)行動者分析
政策網(wǎng)絡(luò)行動者擁有特定的結(jié)構(gòu)位置、各自的資源和不同的互動策略,具有主觀能動性。政策網(wǎng)絡(luò)行動者分析,即從政策網(wǎng)絡(luò)行動者互動行為的細(xì)節(jié)入手來探討政策結(jié)果。
作為一個“關(guān)系型”的社會,我國的社區(qū)治理過程存在著比西方更為復(fù)雜的政策關(guān)系網(wǎng),政策網(wǎng)絡(luò)的“人格化結(jié)構(gòu)”特征十分明顯。正如王思斌教授所說:“社區(qū)建設(shè)是一個公共活動,……社區(qū)是政權(quán)政治與政權(quán)外政治相互作用的場域,社區(qū)政治是復(fù)雜的,因為社區(qū)建設(shè)參與主體的多元化,其中包括上級政府、街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民間組織和社區(qū)居民,他們在具體的活動中參與和追求存在差異。政府力圖減少對社區(qū)的干預(yù),同時還要維持城市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居委會作為法定自治組織希望通過滿足政府和居民的雙方面需要增強獨立性和自主性;至于居民則因為需求結(jié)構(gòu)的不同而對社區(qū)建設(shè)持有不同的態(tài)度。”[10]
根據(jù)傳統(tǒng)微觀經(jīng)濟(jì)學(xué)的自我利益最大化假設(shè),作為策略行為者都具有搭便車的機會主義傾向,都力圖付出的代價最小而獲利最大。同理,社區(qū)治理網(wǎng)絡(luò)中的每個主體,在既定的環(huán)境下,對其可供選擇的行為也必然要經(jīng)過自身的理解和利益選擇的過濾。
因此,社區(qū)治理主體利益訴求的多元化,不可避免地導(dǎo)致了共同治理過程當(dāng)中的競爭和博弈,加之缺乏行之有效的制度規(guī)范、監(jiān)督協(xié)調(diào)機制以及激勵保障措施,在社區(qū)實踐中往往出現(xiàn)一種集體行動的困境和多中心治理的失靈。
三、 重塑我國社區(qū)治理過程以英國鄰里振興計劃為例
基于政策網(wǎng)絡(luò)視角重塑我國社區(qū)治理過程,與社區(qū)網(wǎng)絡(luò)化治理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它更強調(diào)政策流程的創(chuàng)新和組織機構(gòu)的變革,它意味著決策權(quán)下移,告別“全能政府”的治理思路并弱化官僚機制,即自下而上地構(gòu)建政策流程,由鄰里基層來界定社區(qū)發(fā)展建設(shè)的具體政策項目和目標(biāo)群體,并提供方案創(chuàng)意。為了更好地加以解釋和說明,下面以英國的鄰里振興計劃(Neighborhood Renewal)為例進(jìn)行具體分析。
1. 鄰里振興計劃
鄰里振興計劃是英國政府于2001年發(fā)起的一項旨在“振興落后社區(qū),消除社會排斥”的大型社區(qū)振興項目,其政策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可用圖1表示[11]。

圖1 鄰里振興計劃的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
如圖1所示,在鄰里振興計劃中共有四項制度安排:
(1) 鄰里振興基金(NR Fund):是一種“非定向撥款”(non ring fenced grant),其實質(zhì)是由基層提出具體政策項目,中央政府撥款,并視具體情況提出某些特定的管理要求。
(2) 地區(qū)戰(zhàn)略伙伴(local strategy partnership,簡稱LSP):是一個開放性的合作平臺,其參與者包括中央政府在地方的行政代表、地方立法代表,以及地區(qū)的商業(yè)、社區(qū)、志愿組織等的代表。
(3) 地方區(qū)域協(xié)議(local area agreement,簡稱LAA):是經(jīng)LSP參與各方討論協(xié)商后共同簽訂的戰(zhàn)略行動方案,通常是每三年一簽,其實質(zhì)就是一個地區(qū)戰(zhàn)略伙伴之間的功能角色定位與權(quán)責(zé)關(guān)系約定。
(4) 鄰里管理(neighborhood management,簡稱NM):是一種基層社區(qū)的自治組織,其主要成員是那些被基層公眾選舉出來的代表,此外還包括地方政府、相關(guān)政策部門以及活躍于本地的非營利組織代表。
其中,LSP具備正式地位,但沒有行政權(quán)力,主要功能是促進(jìn)基層社區(qū)、地方政府以及中央政府的溝通,在地區(qū)層面上推動政府部門之間、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的協(xié)調(diào)與合作,并在此基礎(chǔ)上討論地區(qū)發(fā)展戰(zhàn)略,提出合適的政策建議;LAA的原則在于充分發(fā)揮中央政府、政策部門、市場及公民社會各自的優(yōu)勢,以形成政府、市場和非營利組織共同向基層社區(qū)提供資源的互補格局;NM從“鄰里振興基金”得到運作經(jīng)費,并通過聘用職業(yè)化的“鄰里經(jīng)理”(neighborhood manager)充分調(diào)動各個網(wǎng)絡(luò)行動者的既有潛力,既向各種非營利組織和志愿機構(gòu)尋求合作,也向市場或相關(guān)政策部門購買服務(wù)。英國政府對NM的組織形態(tài)和具體功能并不作統(tǒng)一要求,而是鼓勵其量身定制,以保證基層參與的自生長性及相關(guān)服務(wù)的創(chuàng)新性。總之,LSP像一個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開放系統(tǒng),用LAA將所有參與主體聯(lián)絡(luò)起來,NM則是在它之下的社區(qū)合作平臺,兩者的關(guān)系實質(zhì)就是公民社會的組織原則,即網(wǎng)絡(luò)化[11]。
2. 基于政策網(wǎng)絡(luò)視角重塑我國社區(qū)治理過程
以上分析旨在說明,政策網(wǎng)絡(luò)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當(dāng)中,都能夠為我國的社區(qū)治理提供另外一種政策過程的想象。基于政策網(wǎng)絡(luò)視角重塑我國社區(qū)治理過程,并最終達(dá)到社區(qū)善治的目標(biāo),特別須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1) 還原社區(qū)本質(zhì)
政策網(wǎng)絡(luò)視角下的社區(qū)治理過程是一個動態(tài)的、復(fù)雜的、各主體間相互依賴的政策參與過程,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權(quán)力中心,而變成了整個政策網(wǎng)絡(luò)的推動者和管理者。因此,我國社區(qū)建設(shè)的當(dāng)務(wù)之急是拋棄傳統(tǒng)的、單線的、強制性的“決策—執(zhí)行”機制,理順政府(包括街道辦事處)與社區(qū)的關(guān)系,還原社區(qū)本質(zhì)。
眾所周知,在社區(qū)治理實踐中,許多政策議程已不再局限于單一的政策領(lǐng)域和部門,政策協(xié)作(policy coordination)顯得異常重要,而政策網(wǎng)絡(luò)所擅長的正是這樣一種復(fù)合式的跨部門議程。為此,必須首先明確圍繞復(fù)合議程的各個政府組織及其他各類市場和社會組織,并予以充分的包容。
特別需要強調(diào)的是非營利組織的參與,因為它是政策網(wǎng)絡(luò)得以形成的關(guān)鍵一環(huán),也是社區(qū)治理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此外,政策網(wǎng)絡(luò)視角下的社區(qū)治理過程還為實施分權(quán)和培養(yǎng)民主習(xí)慣提供了最佳訓(xùn)練場。我國的社區(qū)居民普遍缺乏現(xiàn)代社區(qū)主義意識,缺乏對社區(qū)共有價值的認(rèn)同感和群體歸屬感,因此,要培養(yǎng)社區(qū)居民的主人翁意識,明確參與社區(qū)公共事務(wù)不只是一項權(quán)利,更是每個社區(qū)公民應(yīng)該承擔(dān)的公共責(zé)任。
(2) 確立政策網(wǎng)絡(luò)的運行規(guī)則
正如羅茲所強調(diào)的那樣,政策網(wǎng)絡(luò)的參與群體間必須形成一種長期穩(wěn)定的關(guān)系架構(gòu),且以法律化和制度化的形式加以固定,從而在不斷的互動過程中尋找解決復(fù)雜問題的新方法。中國的特殊國情決定了社區(qū)發(fā)展需要中央及各級地方政府提供法律依據(jù)、制度規(guī)范、運行規(guī)則和政策支持,才能夠有章可循、良性發(fā)展。因此,政府必須擺脫對社區(qū)事務(wù)的具體管理,站在更高的層次上統(tǒng)攬全局、把握方向,充當(dāng)社區(qū)規(guī)則架構(gòu)的創(chuàng)建者和監(jiān)督者,從而保障整個政策網(wǎng)絡(luò)的合法性和權(quán)威性。
首先,改革政策流程,優(yōu)化社區(qū)政策體系。凡與社區(qū)發(fā)展建設(shè)有關(guān)的活動和項目,應(yīng)自下而上地構(gòu)建政策流程,由鄰里基層來界定社區(qū)發(fā)展建設(shè)的具體議題和目標(biāo)群體,并提供方案創(chuàng)意,以便形成更可取的項目運行策略。為此,應(yīng)將街道政府權(quán)力平行轉(zhuǎn)移,不斷完善社區(qū)居委會組織,大力培育社區(qū)非營利性組織及各類志愿組織。
其次,積極發(fā)展社區(qū)民主,增強信息透明度。要積極拓展社區(qū)居民表達(dá)自身利益的渠道,如進(jìn)行關(guān)鍵目標(biāo)群體接觸和居民調(diào)查,開展居民對社區(qū)服務(wù)水平的監(jiān)督評價,組建公民咨詢委員會,開辦公民系列論壇等等。此外,要及時公布與社區(qū)治理有關(guān)的各種信息,并隨時接受社區(qū)居民的政務(wù)、財務(wù)監(jiān)督。
(3) 形成資源的優(yōu)勢互補
根據(jù)政策工具理論,可以將政策網(wǎng)絡(luò)中不同參與群體分別具有的優(yōu)勢資源分為財政資源、行政權(quán)威、組織機構(gòu)和知識信息四大類[11]。
首先,中央政府的優(yōu)勢主要在于財政資源和行政權(quán)威,側(cè)重于財政管理、提供激勵及規(guī)則監(jiān)督。中央政府應(yīng)設(shè)立長期的專項預(yù)算,并根據(jù)各地區(qū)提出的具體政策項目進(jìn)行撥款,加大社區(qū)的活動設(shè)施建設(shè)力度,不斷增加社區(qū)自治組織的活動經(jīng)費。同時,借助社會力量發(fā)展社區(qū),做到政府出資,社區(qū)辦事。
其次,地方政策部門和營利組織的優(yōu)勢主要體現(xiàn)為組織機構(gòu),側(cè)重于提供服務(wù)。其中,地方政策部門為社區(qū)發(fā)展提供各類公共服務(wù),通過政策進(jìn)行調(diào)控和監(jiān)督,引導(dǎo)不同主體之間相互服務(wù)、相互支持,從而降低交易費用,尋求資源共享;營利組織與社區(qū)是一種休戚相關(guān)、合作共贏的關(guān)系,其優(yōu)勢在于提供各類市場服務(wù)。良好的“社區(qū)公關(guān)”形象具有“多米諾骨牌”效應(yīng),能夠為其營造更好的外部環(huán)境,因此,營利組織須要將社區(qū)作為自身發(fā)展的一個組成部分,視社區(qū)公眾為“準(zhǔn)自家人”,在資金支持、居民就業(yè)、公共設(shè)施建設(shè)和環(huán)境保護(hù)等方面為社區(qū)發(fā)展提供幫助。
最后,非營利組織以及公民社會的優(yōu)勢在于提供知識信息,特別是執(zhí)行方案的創(chuàng)新,側(cè)重于提供關(guān)鍵信息、服務(wù)傳導(dǎo)與組織協(xié)調(diào)。正如彼特·杜拉克所說:“社區(qū)問題的解決之道,就在社區(qū)里面。非營利組織就是社區(qū),我們正透過它們來塑造一個公民社會非營利組織,它不但已成為社會的主流,更是其中最不同凡響的一大特點。”[12]社區(qū)非營利組織主要包括業(yè)主委員會、社區(qū)中介組織和志愿團(tuán)體等,應(yīng)該在政府的支持和引導(dǎo)下,獨立地開展各項有償、低償或無償?shù)姆?wù),通過優(yōu)質(zhì)的服務(wù)來換取政府的支持、企業(yè)的資助、社區(qū)居民以及社會各界的認(rèn)同。
四、 結(jié) 語
縱觀世界上一些比較成熟的社區(qū)治理過程,無論是新加坡的政府主導(dǎo)型、美國的社區(qū)自治型,還是日本的混合模式,事實上都形成了一種社區(qū)自治及公民參與的政策網(wǎng)絡(luò)。由此可見,這并不是少數(shù)國家或城市社區(qū)治理的特色,而是當(dāng)今時代具有普適性的社區(qū)治理法則。
從政策網(wǎng)絡(luò)視角探索重塑我國社區(qū)治理的過程,并非想取代國家中心或市場中心,而是在政府資源權(quán)威性分配優(yōu)勢和市場基于個人理性自利的簡化假設(shè)之間,提供另一種體現(xiàn)人性關(guān)懷、信任及公民參與的治理過程。總之,要解決社區(qū)治理失靈問題,就必須擺脫單向度的、行政直線式的治理模式,讓社區(qū)自治主體能夠在一個上下結(jié)合、多元互動的政策網(wǎng)絡(luò)中,更大程度地分享公共權(quán)力和公共資源,使社區(qū)公共事務(wù)真正變成社區(qū)居民自己的事情,而不再僅僅是政府一家的事。
參考文獻(xiàn):
[1]楊道田,王友麗. 政策網(wǎng)絡(luò):范疇、批判及其適用性[J]. 甘肅行政學(xué)院學(xué)報, 2008(4):32.
[2]Howlett M, Ramesh M. Studying Public Policy Cycles and Policy Subsystem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3]Rhodes R A W. Policy Networks in British Political Science[M]∥Rhodes R A W. Understanding Governance: Policy Networks, Governance, Reflexivity, and Accountability.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7.
[4]Howlett M, Ramesh M. Policy Subsystem Configurations and Policy Change: Operationalzing the Post Positivist Analysis of the Policy Process[J]. Policy Studies Journal, 1998,26(3):446-481.
[5]Kenis P, Schneider V. Policy Network and Policy Analysis: Scrutinzing a New Analytic Toolbox[M]∥Martin B, Mayntz R. Policy Network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Theoreticl Considerations.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Verlag, 1991:25-29.
[6]Kickert W J M. Public Governance in the Netherlands: An Alternative to Anglo-American “Managerialism”[J].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97,75:731-752.
[7]Marsh D. Comparing Policy Networks[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8.
[8]Marsh D, Smith M. Understanding Policy Networks: Towards a Dialectical Approach[J]. Political Studies, 2000,48:4-21.
[9]Marsh D, Rhodes R A W. Policy Communities and Issue Networks: Beyond Typology[M]∥Marsh D, Rhodes R A W. Policy Networks in British Governme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10]王思斌. 體制改革中的城市社區(qū)建設(shè)的理論分析[J]. 北京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 2000,37(5):5-13.
[11]郭巍青,涂鋒. 重新建構(gòu)政策過程:基于政策網(wǎng)絡(luò)的視角[J]. 中山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 2009,49(3):166-168.
[12]彼特·杜拉克. 杜拉克看亞洲[M]. 臺北: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998: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