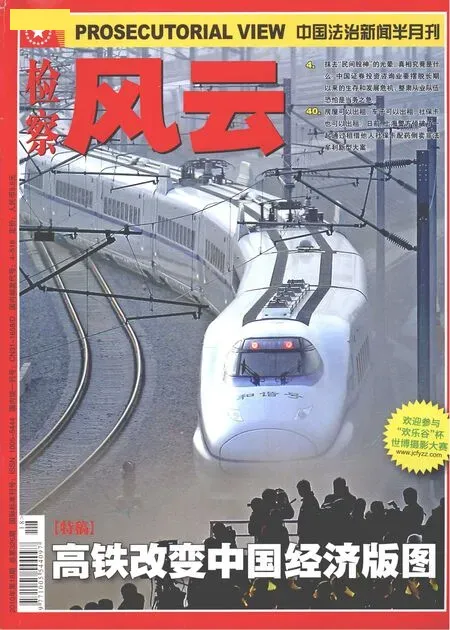“危險駕駛”如何入罪
游偉 華東政法大學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法學教授
“危險駕駛”如何入罪
游偉 華東政法大學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法學教授
編者按:近日,有關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欲增加“危險駕駛”的條款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8月2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分組審議這部草案時,就這一新增條款紛紛發言。不少組成人員建議修正案草案應加重對醉酒駕駛的懲罰力度。
審慎對待“醉酒駕駛”入罪問題
由于近年來酒后駕駛造成危害后果的案件數量急劇攀升,尤其是因醉酒駕車造成重大傷亡的惡性案件引發社會強烈關注,致使對醉駕肇事案定罪量刑的傳統標準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在個別“影響性案件”的法律適用上,確實呈現了值得重視的司法變化現象。
比如一向以過失犯罪對待的交通肇事罪,如今似乎很難再使用于醉駕造成嚴重后果的案件了,常常代之以“故意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論處。其實,醉駕肇事,甚至在肇事后逃逸又造成重大人員傷亡的,按照被告人的實際心理狀態分析,也不是一定都具有“放任危害結果發生”的犯罪故意。但由于行為后果嚴重,似乎超出了一般“肇事”的范圍,人們往往想不到運用同樣是過失犯罪性質的“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去定罪量刑。在重刑思想的指導下,更愿意去使用故意類的犯罪罪名,并適用重刑乃至死刑。而如果同樣的行為造成并非特別嚴重的后果,認定過失性質并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處刑,似乎并不會產生太多的問題。看來,從危害后果出發去尋找“量刑適當”的罪名,然后對犯罪事實予以“必要解讀”,已經成為一種思維定勢,并直接構成了對現實司法的影響。

然而,以“故意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處理此類案件,畢竟存在著“不典型”問題,難免有“變通”的嫌疑。于是,在面臨刑法討論修訂之機,提出增設新罪名并加重刑罰量,便又成了一種必然的選擇。在剛剛結束的本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上,提請審議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中就擬定有一個“醉酒駕駛罪”,并設置了最高刑為拘役六個月的刑罰。這個條文雖說“刑罰”較輕,但入罪條件非常特別,并不需要產生實際的危害結果,只要有“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行為,即可定罪判刑。有些參會委員和學者甚至認為法案中的刑罰依然規定得偏輕,提出了可以提高至三年或者五年有期徒刑的建議。
應該看到,醉酒駕駛行為在以往的治安管理處罰案例中,真正被嚴厲處罰的其實也不常見,即使是在全國交通安全整治活動中,行政處罰的力度也據情而有所區別,行政執法并非一律“頂格”適用行政拘留十五日處罰(有些學者甚至認為對其中情節嚴重的,最重可以處以勞動教養。筆者認為這不盡妥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似有理由認為,對醉酒駕駛行為的行政處罰力和實際威懾力并沒有得到完全、充分的發揮;而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醉酒駕駛畢竟是其可能肇事的實害行為的“先期行為”,究竟應當定性為故意還是過失,從專業的角度上講,仍有進一步探討的余地,其可能造成的危害,也確實與過失決水,過失爆炸、失火,過失投放危險物質等不能相提并論。因此,將它設置為“行為犯”、“危險犯”,也一定會有相當的爭議。在這種頗有爭論的狀態下,如果便匆忙根據“民眾的呼聲”迅速單獨設罪并“加大刑罰處罰力度”,其本身是否科學,是否真能起到遏制此類行為“高發”效果,著實值得質疑和商榷。雖說,刑法規范并非是僵硬和一成不變的,它也需要符合社會需要、與時俱進,但法律的穩定性、科學性和平衡性,始終也是一條重要原則。因此,審慎對待和仔細論證“醉酒駕駛”是否需要單獨入罪問題,對于科學認識此類行為的違法屬性、切實把握刑罰的功能效用、正確處理行政與司法的關系等,應該都會有更加積極的意義。
飆車醉駕入罪值得期待
陳英鳳 《生活創造》編輯

近年來,一起起血淋淋的交通事故慘案,引發人們對酒后駕車、飆車的空前關注。為此,2009年8月以來,我國掀起了一場猛烈的治酒駕風暴,在一定程度上打擊和震懾了酒后駕駛違法行為。然而,仍有不少人漠視法律規定,頂風作案。公安部的一組數字顯示,2009年8月15日至9月15日,全國共查處酒后駕駛違法行為65397起,其中醉酒駕駛10711起,分別比2008年同期上升了86%和91%;因酒后駕駛發生的交通事故仍達到320起,死亡118人。根據最高法統計,僅酒后和醉酒駕車肇事,2009年1月至8月,發生3206起,造成1302人死亡。
在我看來,酒駕飆車之所以屢禁不止,關鍵原因在于現在對酒后駕駛和飆車行為的處罰太輕、量刑標準過低,缺乏震懾和懲戒作用,導致司機存在僥幸心理。《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的網上調查顯示,有97%的人承認身邊存在酒后駕駛現象,有81%的人認為我國對酒后駕駛處罰過輕,有70%的人認為“違法成本過低”是酒后駕駛現象屢禁不止的主要原因。確實,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對酒后駕駛處罰過輕。如德國、美國、加拿大、英國、日本、新加坡和印度等國家以及我國香港地區,把嚴重酒后駕駛行為列為犯罪,可能被處以6至12個月的監禁,情節嚴重的甚至要處3年徒刑。而我國刑法中的交通肇事罪僅適用于違反交通安全法規、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物遭受重大損失的結果犯,而對尚未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未將其設定為犯罪,只能給予行政處罰。在這種情況下,對現行酒后駕駛的有關法律規定進行修改,增設“危險駕駛罪”,加大對酒后駕駛、飆車等嚴重交通違法行為的懲處力度,從法律制度層面建立遏制酒后駕駛違法行為的長效機制,成為現實的迫切需要。一旦“危險駕駛罪”寫入刑法修正案,其所能起到的警示效應和社會效果,是多少次的嚴查、多少次的從重判決都難以比擬的。
與此同時,增設“危險駕駛罪”還是統一我國法律適用,維護法治權威的需要。酒后駕駛違法行為應當如何定性歸罪,在司法實踐中爭議也很大。2009年5月,沈陽人吳凱因酒后駕駛造成3死2傷,被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刑7年,但杭州人魏志剛酒后駕駛造成1人死亡,則是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被處以有期徒刑2年3個月。同樣對醉酒駕駛肇事后造成重大傷亡,有的地方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有的地方定為交通肇事罪,這種“同案不同罪”、“同罪不同刑”的現象時有發生,損害了法律適用的統一性。增設“危險駕駛罪”,將有助于法律適用的統一。
危險駕駛如何入罪還需仔細斟酌
李克杰 山東政法學院法學院副教授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增加“危險駕駛”的條款引起了社會各界高度關注。2010年8月2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分組審議這部草案時就這一新增條款紛紛發言,不少組成人員建議修正案草案應該加重對醉酒駕駛的懲罰力度。
其實“危險駕駛”條款存在的缺陷和問題,不僅僅是懲罰力度不夠,至少需要從四個方面進行充實完善:
首先是要進一步厘定應當入罪的危險駕駛行為范圍和種類。草案目前規定的危險駕駛行為僅限于醉酒駕駛和馬路飆車兩種行為,并沒有涵蓋與之危險性相當的其他危險駕駛行為,如吸毒后駕駛、無證駕駛以及嚴重超速和疲勞駕駛等,有的危險駕駛行為已經嚴重威脅了公共安全,造成了重大人員傷亡和巨額財產損失的后果,同樣需要入罪加以遏止。特別是這個條款采用列舉式規定,而沒有概括性的兜底式規定,大大降低了未來對形勢變化的適應性,甚至也完全排除了以法律解釋方式擴大其適用范圍的可能性,顯然是值得商榷的。
其次是危險駕駛行為的最低入罪條件問題,具體來說就是確定罪與非罪的標準問題。有委員指出,只要醉酒駕駛,無論該行為是否存在惡劣情節,都構成犯罪,應當承擔刑事責任,建議刪除修正案中“情節惡劣”的表述。關于這一點,筆者認為個別委員存在誤解。從草案條款的表述看,醉酒駕駛構成犯罪并不以“情節惡劣”為條件,“情節惡劣”是限定馬路飆車的,也就是說,“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才構成犯罪。
在這個問題上,一些委員還存在混淆“犯罪情節”與“犯罪后果”的傾向。比如有委員就質問:“何為‘情節惡劣’?惡劣到什么樣的程度?是不是惡劣到一定要死了人或者造成重大事故才算是惡劣?”死了人或者造成重大事故,已不屬于“情節惡劣”而屬于“后果嚴重”了。“情節”往往指飆車嚴重超速、飆車屢教不改、在道路繁忙的路段飆車或因飆車造成市民驚慌、交通擁堵等等,而一旦出現事故或人員傷亡就是有了“嚴重后果”。事實上,危險駕駛罪是一種行為犯,也是一種危險犯,并不要求后果出現。因此,草案的這個條款在文字表述上已經非常嚴謹,不存在問題。
第三個問題危險駕駛罪的處罰力度以及危險駕駛造成嚴重后果的罪名銜接問題。草案擬定的法定刑是“拘役并處罰金”,罰金往往受到犯罪人經濟條件的制約,存在執行能否到位的問題,因而能否完全起到懲罰震懾作用,或在兩可之中。如此一來,刑罰的威懾力就只能寄希望于主刑了,那么,一至六個月的拘役能否與醉酒駕駛和馬路飆車的巨大危險性相適應,恐怕很值得懷疑。特別是它屬于故意犯罪,最高法定刑為拘役明顯處罰過輕,同時幅度這么小的刑罰在適用上也很難與不同程度的醉酒相適應。
另外,當危險駕駛由行為犯轉變成結果犯,由危險性變成現實危害后,應該與哪個罪名相銜接,也是必須預先考慮的問題。由于危險駕駛罪是故意犯罪,當出現嚴重后果時,其主觀狀態也是明知而放任的間接故意,顯然不能與以過失為特征的交通肇事罪相銜接,如果直接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相銜接,則明顯跨度太大,因為該罪的法定最低刑是10年有期徒刑。為此,筆者建議刑法修正案草案增設“危險駕駛肇事罪”,根據不同的危害后果設置不同的法定刑,以便與危險駕駛罪這種純危險犯罪實現無縫銜接。
具體來說,就是讓危險駕駛成為一個完整獨立的罪名,其設置的法定刑種類和幅度能與危險駕駛行為的不同危害程度相對應,而不必在“情節特別嚴重”或者“造成嚴重后果”時再“借用”其他罪名。
編輯:靳偉華 jinweihua1014@sohu.com
book=0,ebook=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