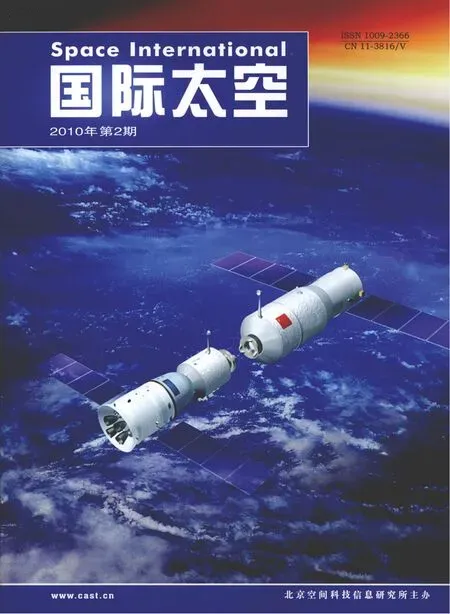火星之旅中航天員可能的心理危機分析

□□登陸火星是人類繼成功登月之后未來宇宙探索與開發的又一個極具風險卻又十分誘人的宏偉目標。然而,紅色星球距離地球如此遙遠,航天員需要在狹小封閉的飛船中“囚禁”36個月,以完成史無前例的漫長旅程,這將是一次難以想象的“心理測試”。目前,心理學家正努力在地面進行模擬實驗,以期找到克服心理危機的有效方法。
眾所周知,世界主要航天國家和歐盟的航天機構都擁有或正在籌劃各自的火星探索計劃。盡管飛赴火星所需動力形式的確定、飛行軌道的選擇和宇宙射線的防護等問題還在討論之中,但人類踏上火星的夢想很可能在21世紀中葉實現。從技術層面來講,具體方案的擬定不過是時間問題。
一艘執行登陸火星任務的飛船飛越數千萬千米抵達火星,著陸后停留數月再返回地球,耗時約3年才能再次實現“對于一個人來說只是一小步,對于人類來說卻是一大步”的偉大壯舉。然而,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依然擺在人們面前:航天員們能否為這樣的旅行作好準備?毫無疑問,第一個飛赴火星的航天員小組是精心挑選出來的。在正式啟程前,每位航天員都必須滿足身體和情智等方面極其苛刻的要求,這是保證成功完成任務的先決條件。但現在的問題在于,當男女航天員們被封閉在飛船中穿越茫茫宇宙飛向一個未知世界時,怎樣確保他們能夠在心理上承受得住這么長時間的火星之旅,對此目前尚無答案。歐洲航天局一位名叫馬克·赫伯內的官員直言不諱地說:“航天員的心理問題是迄今最沒有把握的。”
人們也許無法想象,一位通過極端訓練培養出來的航天員會因為一時的精神抑郁而毀掉一次登陸火星的使命。事實是,在征服太空的歷史進程中,這方面的例子曾不止一次地出現過。例如:蘇聯聯盟號載人飛船的2位航天員就曾因為發生口角而提前終止了本該持續2周的在軌飛行任務。在1999年莫斯科近郊進行的240天地面封閉模擬實驗中,一名俄羅斯航天員曾在微醉的狀態下粗暴地對待一位加拿大女航天員。再就是1973年美國“天空實驗室”軌道艙內的航天員小組,他們為表達抗議連續24h拒絕回復地面控制中心的指令。對于經過層層篩選而勝出的佼佼者來說,出現上述過激行為的確令人費解。然而,據來自法國蘭斯市應用心理學實驗室的心理學家伊麗莎白·羅斯奈解釋,“在精神過度緊張時,一些個體會表現出在平日從未有過的反應”。顯然,人類行為問題的深奧之處正在于它的不可預見性。
1 充分利用南極科考站的模擬條件
目前,人類對航天員在地球軌道或是在月面逗留時出現或可能出現的問題有了一定的了解,但火星之旅完全不同。“國際空間站”距地球約有400km,月球距地球也不過38.4萬千米,而火星距地球少則5600萬千米,多則4億千米。法國國家航天研究中心的安東尼奧·蓋勒醫生把這種情形概括為:“如果在‘國際空間站’出問題,人們可以考慮用幾小時、最多不過2天時間飛回地球;從月球返回地球也只需4~5天;而如果在火星上出問題,那就需要等6個月才能再次獲得一條火星與地球之間的有利軌道,進而脫離火星引力,之后還要9個月時間才能飛回地球: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為了更好地預測未來航天員小組在執行火星任務中可能出現的行為問題,心理學家采用了一種稱之為 “類比”的研究方法,即創造出與未來火星探險者可能遇到的情況相似的環境空間。例如:海洋中的石油平臺或遠航中的船舶就可以提供最初級的類似環境特點,不過最好的是法國和意大利聯合建造的康考迪亞(Concordia)南極科考站。由于在南極的整個冬季人類根本無法接近這個科考站,它就成為了地球上與世隔絕的地方,也因此成為進行封閉隔絕訓練的絕佳場所。3年多來,每年都有10余人(包括技術人員、地理學家、生物學家等)進駐那里,在2個總共1500m2、分上中下三層的圓柱體建筑里呆上9個月。巴黎環境心理實驗室女研究員卡麗娜·維斯認為,康考迪亞科考站與未來奔赴火星的飛船之間存在不少相似性。首先是生活單調孤寂,科考站之外一片冰天雪地,人們很難“越雷池一步”;其次是長期與世隔絕,盡管9個月的時間比火星任務的3年要短許多;再次是參與科考活動的人員間存在不同文化之間的沖突;最后是組成人員的數量,科考站是10余人,而奔赴火星的航天員預計是6人左右。

康考迪亞科考站
2 幾種明顯不當的行為及其原因分析
心理學家羅斯奈主持了一項為期4年、名為Psyetho的心理學研究項目。作為其中的一部分,參與該項目的維斯曾于2007年11月首次探訪了南極科考站的“志愿被困者”。在她看來,雖然南極的冬季總算順利挨過了,但有些人的行為仍表現出潛在的危險性。某些人會獨自走出科考站,并且不攜帶無線通信設備,他們覺得自己已經完全了解了周圍的環境。還有一個人拒絕工作,雖然他很清楚這種做法會影響整個團隊的協調配合。
研究極端條件下心理適應能力的專家認為,上述“出格”行為源自多種因素。第一個因素是孤獨,即身邊沒有親人、朋友,尤其是與同事相處時心情很難完全放松。誠如1999年在俄羅斯和平號空間站上逗留了186天的法國航天員讓-皮埃爾·埃涅雷所說:“航天員的選拔旨在完成極具挑戰性的任務。一旦進入工作崗位,作為‘操作手’的航天員就要按照事先制定好的計劃執行操作,靈活處置的余地極小,而且時時刻刻都在地面控制中心的監控之下。”不難想象,接受過各種訓練、擁有多種資質的航天員,在被要求完成極其機械、呆板的工作時是何種心態。羅斯奈認為,這種沮喪更多是由于人類個體遠離自己已經習慣的生活環境而陷入孤獨,進而抑制了自我肯定所造成的。在飛往火星的飛船上就如同在康考迪亞科考站里,原來由在職場共事、與家人溝通和在各種社會關系中交往所帶來的成就感、滿足感消失了。不僅如此,當遇到諸如親人過世等個人的不幸時,孤獨感有可能變得極其危險。假如正在執行火星任務的航天員遭遇上述不幸,是告知還是隱瞞,如何處理尚無萬全之策。
導致行為不當的第二個因素是封閉在狹小空間的被囚感。羅斯奈認為,在日常生活中,即使忙碌一天,人們總還能指望在晚間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在康考迪亞科考站也一樣,每人都有自己的房間;在太空中這顯然不太可能。曾在空間站工作過的埃涅雷介紹了他們的解決辦法。他說:“我們是經過調配給每個人留有一塊屬于自己的空間,你可以在那里放一些個人物品,其他人可以經過那里,但不可碰觸別人的個人物品。在這塊小小的空間里,你可以思考、謀劃,做自己的私事。”
導致行為問題的第三個因素就是飛船中的日常工作。如果說習慣于執行短期任務的航天員往往都是加班加點工作,那么長期任務對他們來說就顯得工作量不足。羅斯奈指出:“那將是可怕的。原因是需要做的事少了,留給人們想事的時間就多了,這對人的心理會產生負作用。”不僅如此,如果一位航天員沒能按預期完成所承擔的任務,就會出現不正常的心態;此時再加上孤獨感的作用,他就很難或者不可能從沮喪的情緒中擺脫出來。因此,心理學家們一致認為,除火星探險的主任務之外,航天員還要執行一些預先安排的其他工作或任務,如讀書、看電影或做體育運動等,這些有助于他們忘記火星之旅的單調乏味。埃涅雷講述了他自己的經歷:“當年在和平號空間站工作期間,我曾帶去了整套的攝影器材和一只薩克斯管。盡管當時我只是個新手,但渴望提高技藝、取得進步的愿望還是給了我滿足感和幸福感。”
潛在危險行為的第四個誘因源于不同文化碰撞引發的溝通困難,這種情況在執行極端任務時尤為明顯。平時也許只會導致小小的不理解,但在執行任務時完全可能加劇集體性的緊張氣氛和情緒。有一個例子很能說明問題:在康考迪亞科考站越冬科考期間恰遇一屆世界杯足球賽,法國人習慣邊看球邊大聲評論,并且滔滔不絕,而意大利人則更喜歡保持安靜。這在平常環境中也許算不上什么問題,倘若與其他問題攪到一起,那對多國科考隊就是一次心理考驗。

模擬火星之旅
3 火星500計劃
如何更好地幫助未來執行火星登陸任務的國際航天員小組克服孤獨、封閉、無所事事和文化差異等諸多方面的難題?一個多國混合的航天員小組能否保證飛船艙內的和平?除了這些問題,羅斯奈還設想了另一種情況:在太空旅行中如果誕生一對夫妻,那應該是件很好的事,當然前提是飛離地球之前他們都是單身,并且在航天員小組內部沒有出現情敵。但是,如果在任務期間要分手又該怎么辦呢?在地面的日常生活中這種問題很容易解決,大家不再見面就可以了,但在飛船中這就困難多了。即使對飛船的指揮采用軍隊的命令方式,也很難保證不出現過激行為。再進一步探究,是以個人才能為尺度選拔出類拔萃的個體,還是以成員之間能夠和睦相處為標準選擇個體組成一個和諧的小組?如何保證航天員小組有足夠的自治能力管理并處理好在飛船上所發生的各種情況?如此多的問題,目前都沒有答案。
關于自治管理的問題,在2009年就得到了初步的實驗結果。俄羅斯聯邦航天局和歐洲航天局合作推出了一項名為火星500的實驗計劃,有6名來自不同國家的志愿受試者被送往位于莫斯科郊外的模擬火星飛船的實驗艙接受測試。首期105天的測試在2009年7月15日結束。4名俄羅斯人、1名法國人和1名德國人于3月31日進入一個沒有窗戶、面積為180m2的封閉空間。為了測試他們的情緒和各種心理反應,模擬飛船艙內安置了監視設備,與外界通信聯系所需的時間也是從地球傳輸到火星所需的20min。其中一位受試者出艙后說:“與‘地面’聯系如此漫長,我們后來越來越傾向于自行解決問題。”法國受試者則說:“最痛苦的是沒有白晝與黑夜的交替,睡眠被擾亂,還有就是與家人隔絕。”但受試者普遍反映,他們之間沒有產生隔閡,相處很好。2010年年初,這些志愿受試者會被重新召回,參加為期520天的下一輪封閉測試。
歐洲航天局官員馬克·赫伯內認為,自治管理是往返火星旅程中最重要的問題,它在火星探索中的重要程度遠遠超過在近地軌道飛行或登月飛行中,尤其當航天員出現健康問題時更是如此。事實上,航天員如果在“國際空間站”遇到健康問題,可以被很快送回地球;假如在火星上或在已遠離地球去往火星的途中出現問題,那只能靠航天員自行解決了。
總而言之,專家們目前所能確知的只有一件事情:在未來的歲月中繼續積累研究測試經驗。蓋勒醫生認為,研究航天員的心理需要花費10年時間,至少需要做10次封閉實驗。然而,行為失控的危險就能因此得到有效控制嗎?即便所有的問題都被設想到,并且找到了解決辦法,但還是有一個問題沒有答案:當航天員從火星看到地球就是夜空中一顆不起眼的星星時,他們的心理會受到怎樣的沖擊?赫伯內坦言:“從火星上看,地球很小很小,如果你不知道它的準確方位,你根本找不到它!然而我們無法想象,當一個人被如此徹底地與自己的故鄉隔離時,內心會是怎樣的一種感受……”因為再不能看見藍色星球而引發的極度焦慮,會不會壓垮人的精神?只有當一個人用自己的雙眼搜尋火星的夜空、回望地球的方向而看不到地球時,才會真正找到答案。

志愿受試者
4 火星之旅需要獻身精神

未來登陸火星的航天員
完成火星之旅需要解決一個特殊的問題,即對生命的認識,這意味著完成既定目標比不惜代價保護生命更為重要。在埃涅雷看來,未來的火星之旅需要那些具有獻身精神的人。在啟程之前,他們已經對登陸火星產生了強烈興趣,并具備勇往直前的精神,即使付出不能返回地球的代價也在所不辭;但這種做法不符合現代人的觀念。此外,面對奔赴火星的征途,人們也許應該更多地借鑒哥倫布或麥哲倫曾經經歷的前途不明、生死不定的艱辛航程,而不是在近地軌道飛行或登陸月球這類航天活動。埃涅雷坦承:“登陸火星才是本質意義上的探險。我相信,人類命中注定要去探險,目的是給生命一個未來。到宇宙探險,這是人類未來之所在。” 王宏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