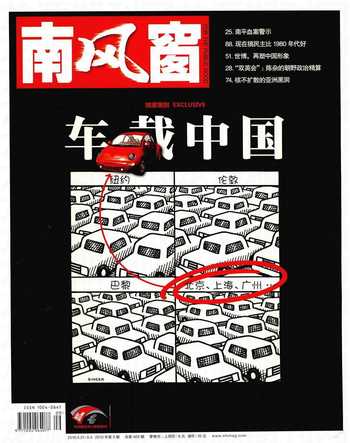“政府俘獲”:權力尋租的高級形態
盧正剛
長期以來,我國腐敗問題主要集中表現為執行性的腐敗,即政府公職人員在執行法律法規的過程中不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辦事,有意降低或者提高標準以謀取私利。一般來說,從事這種腐敗行為的官員主要利用法律法規賦予他們的自由裁量權,在法律規定的上下限之間給行賄人方便。直到郭京毅案曝光,人們才窺知權力尋租的高級形態:“政府俘獲”。
據公開資料顯示,原商務部條約法律司巡視員郭京毅在《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暫行規定》和《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兩部法規的制定過程中,故意通過含糊性和難以操作性的條文為外商能夠逃避監管進入敏感行業留下漏洞。3月18日,郭京毅案正式開庭審理,從法庭查明的案情來看,所涉金額并不很大,但該案卻是我國目前為止查明的唯一一起證據確鑿的“政府俘獲”案件。
所謂“政府俘獲”,通俗講就是立法腐敗,可以解釋為負責立法的政府公務人員接受企業(或集團)的賄賂,有意識地為企業制定有利于其獲得長期利潤的法律法規。它有以下幾個不同于其他腐敗案件的特點:
一、“政府俘獲”是資本和權力相互勾結滲透的升級化,是政策法規制定者和行賄者之間的買賣政策法規制定權的行為,能為行賄者帶來長期穩定的收益。與執行性腐敗相比,“政府俘獲”對企業或集團來說是資本權力化的過程,對法規政策的制定者來說則是權力資本化的過程,這表明權力尋租雙方不滿于過去的“小打小鬧”,而是朝著更深層次的利益結盟方向發展。
二、“政府俘獲”嚴重影響國家經濟安全。相對來說,執行性的腐敗只要官員換人,漏洞就可以彌補,而“政府俘獲”卻很難彌補,法規政策一旦被“定制”,會導致整個產業市場為某些企業集團所壟斷。郭京毅的行為更直接導致中國的產業市場被外資所控制,據北京交通大學產業安全研究中心近日發布的《2009中國產業外資控制報告》稱,近10年來,外資對中國第二產業即工業的市場控制程度穩步上升,平均控制率已接近1/3,超過一般行業市場控制度的警戒線。這其中固然有我國原來法律政策滯后的因素,但上述兩部法規的出臺顯然沒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三、“政府俘獲”行為具有更深的隱蔽性。長期以來,由于從事法規政策執行權的公務人員整天與企業直接打交道,因此對這些公務人員的監督是目前我國反腐敗的重點。而制定法規政策的官員一般與企業沒有直接的聯系,常被認為沒有“油水”可撈,所以至今不是紀檢監察部門重點防范的對象。這次郭京毅之所以被發現,是因為其同學兼同伙張玉棟被其惱羞成怒的情人執意告發才得以揭露,否則,法律制定過程中的技術性和專業性等足以作為借口遮掩其非法的行為。
四、“政府俘獲”行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雖然,郭京毅案是我國目前為止查明的唯一一起證據確鑿的“政府俘獲”案件,但這絕不是個別現象,如一些城市出租車市場壟斷就和出租車公司對相關政策制定者的收買相關,直銷行業的立法和直銷牌照對國外少數企業的頒發等。
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喬爾·赫爾曼等人在1999年對前蘇聯和東歐等22個轉軌國家的“政府俘獲”問題進行專門調查后發現,“政府俘獲”現象在轉軌國家普遍存在,其中11個國家非常嚴重。
但現狀卻令人尷尬,對這類腐敗行為,中國的刑法缺乏針對性的罪名,只能以受賄罪論處。而這類犯罪行為可能受賄金額不一定很大,但危害卻極大,如果以通常的受賄罪來論處,尚不能準確反映其罪行。有媒體提出以受賄加漢奸的指控而對郭京毅處以叛國罪,也不合適,因為“政府俘獲”行為既可以向外商出賣政策,也可以向國內利益集團出售。
根本上降低其危害,要通過加強對法規政策制定者權力的監督,并分散其立法權來實現。長期以來,我國部門性立法具有權力集中和不透明的弊端,加上立法權本身較強的專業性和技術性,導致公眾很難參與,為“政府俘獲”留下漏洞。對此,人大應強化立法權的行使,重要法律盡量自己制定,可以吸引專家學者參與,甚至可以外包。對于由政府部門制定的政策法規要加強監督,嚴格程序規定,特別是充分聽取吸收利益相關方的意見和訴求,公布草案接受社會公眾的參與和監督,實現由極少數人壟斷立法權向公眾參與立法的轉變。
另一方面,在具體人事安排上,應推動政策法規制定人員的崗位交流。郭京毅在外資政策制定崗位一干就是20多年就是一個典型,這為其利用對政策的諳熟和長期的人脈資源來尋租提供了條件。
喬爾-赫爾曼指出,轉軌國家的“政府俘獲”問題是一種內生性病癥,是資本和權力聯合的深化和發展,它將阻撓任何試圖改變這種狀況的改革者的努力。這就是在具體的對策背后,真正的挑戰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