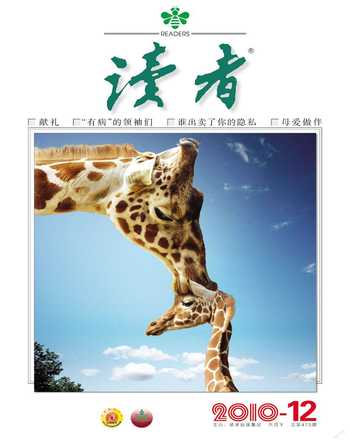凡人列傳
李愚



劉瑞英:“一條老命換3個小孩的命,很值!”
劉瑞英,女,生于1962年,福建省南平市人,南平市文體路環衛隊隊長。
2010年3月23日上午7時20分,劉瑞英正在南平實驗小學對面的路邊打掃。突然,她看到一個身高約1.7米、穿著灰色上衣的男子,抓住一個小女孩的書包不放。“我還以為是父親在門口教訓孩子,沒想到他竟然從背后掏出一把長刀!”接下來發生了駭人的一幕:男子手持長刀直接往女孩脖子上抹去,女孩當場倒下。男子接著抓住身邊的一個學生,用刀狂捅。看到這殘忍的一幕,劉瑞英的腦袋“嗡”的一下炸開了,一時嚇得不敢動彈。
“我看到還有學生從坡下上來,想喊他們快跑,嘴張得老大,就是喊不出聲!”
劉瑞英忘記了害怕,她用手上的掃把當武器,沖上前去,將掃把調過頭來,用木棍對著那個像屠夫一樣的兇手。
她身后是3個剛來上學的孩子。劉瑞英一邊和兇手對峙,一邊護著孩子往后退。這是現實版的“老鷹捉小雞”,此時的劉瑞英就像老母雞護雛一樣,張開雙臂,護衛著身后的3個孩子。
兇手不斷揮動著手中的刀子,幾次試圖沖上來,都被劉瑞英用大掃把擋開。那一刻,這道看似羸弱的屏障,就是人間真正意義上的銅墻鐵壁。事實證明,正是劉瑞英的這一舉動,讓瘋狂殺人的鄭民生停住了手,給學生們贏得了寶貴的逃跑時間。
由于太緊張,用力過猛,劉瑞英的臉上被掃把的竹刺劃出十幾道血痕。她說自己當時非常害怕,怕兇手拿著刀沖過來。“我的腿都在抖,上下牙齒在打戰。”劉瑞英說,當時連死都想到了。“他手里有刀,要是真的沖過來,我肯定死了。”“他離我就兩米多遠,手里拿著刀,他要刺死我我也沒辦法了,反正我不讓開。”
在那千鈞一發之際,這個連自己名字都不會寫的48歲女人,突然想得很坦然:“我都快50歲了,一條老命換3個小孩的命,很值。”
僵持了幾分鐘后,幾個晨練的人圍了上來,合力把兇手鄭民生制伏。此時的劉瑞英氣急了,“我用掃把拼命地敲打他的頭。”
看著孩子們被送走,劉瑞英重新拿起掃把,把剩下的路段掃干凈,這才回家。“我是隊長,當然要以身作則了。”
耿志蘭:“別叫俺孩子,叫俺姑娘吧!”
耿志蘭,女,生于1998年,山東省禹城市人。
禹城市西大橋下,兩米多高的橋墩旁有一堵廢棄的磚墻。靠著這堵墻,其余三面用廢棄的廣告牌、塑料布一圍,這塊四五平方米大的地方就成了耿志蘭一家四口的“蝸居”之地。
12歲的耿志蘭每天拉著9歲的弟弟,白天賣破爛,晚上撿野菜,破爛是錢,野菜是飯。耿志蘭要擔起的不只是姐弟倆的生活,還有父母的生存——父親耿向福去年在建筑工地上摔成腰椎骨折,癱瘓至今;母親有精神障礙,口中整日喃喃自語,卻聽不清她在說什么。
52歲的耿向福是禹城市房寺鎮九圣堂村人,小時候被人抱養到滕州市。養父母去世后,他帶著妻兒回到老家,但沒有居所,無處落腳。耿向福隨后到禹城市一處建筑工地打工,并租了一間平房把家人安頓進去。2009年10月,耿向福不慎從腳手架上掉下來,摔成腰椎骨折,無錢治療的他一直癱瘓至今。同年底,耿家人租住的房子拆遷。由于沒錢租樓房,他們建起了現在的“家”。耿向福說,自從他無法干重活后,全家的生活就只能靠耿志蘭姐弟倆撿破爛來維持。
“最多的時候一天撿的破爛能賣二十幾塊,少的時候只有七八塊。”“不辛苦,不辛苦,俺很樂觀的。”“別叫俺孩子,叫俺姑娘吧。”“俺上過半學期學,俺能說好多成語呢。”耿志蘭說。
她從三輪車上翻出一個小包,掏出一本《伊索寓言》,隨便打開一頁,迎著橋下微弱的光線,教弟弟念著她能認出的字。讀到不認識的字就用“什么”代替,不長的句子中“什么”出現了好幾次。她說:“俺只有這一本書,是小朋友送給俺的。別看就這一本,它可是俺的寶貝!”
看到同齡的孩子去上學,“姑娘”耿志蘭很羨慕:“俺好多回都夢見在讀書呢!”她希望自己能像以前一樣在課堂上讀書。“弟弟從未進過課堂,好想帶他去上學。”冷風勁吹下,姐弟倆的手臉被凍得通紅……
孫東林:“哥哥今生不欠人一分錢,不能讓他欠下來生債。”
孫東林,男,湖北省武漢市黃陂區人,自2004年起,一直在中國華北冶金建設有限公司天津東麗分公司務工。
2010年2月9日,為搶在大雪封路前趕回老家給農民工發工錢,武漢建筑商孫水林連夜從天津駕車回家。10日凌晨零時許,南蘭高速河南開封縣隴海鐵路橋段,由于路面結冰發生特大車禍,20多輛車追尾,事故造成多人死傷。孫水林一家五口不幸遇難。
“哥哥在北京和天津都有工程。”弟弟孫東林說,“2月9日,哥哥從北京趕到天津,嫂子和3個兒女都暫住在天津。”晚飯后,孫水林來到弟弟家。原本打算隔天再走的孫水林上網查看天氣預報時發現,從天津回武漢的沿途即將出現雨雪天氣,若降雪太大高速公路可能封閉,他當即決定連夜駕車回家。
春節前一個月,工地已陸續停工,孫水林已基本結清工錢,就差老家幾十名工友的尾款約30萬元。晚上7時許,他拿著要賬要來的11萬元加上從弟弟手里借來的15萬元,帶著妻子和兩個女兒、一個兒子連夜啟程,經京滬高速直奔武漢。
10日下午,孫東林打電話回家,發現哥哥仍未到家。他接連撥打100多遍手機,仍無人接聽。預感情況不妙的他開車上路,風雪中沿途苦尋。路上他接到老鄉的電話:哥哥的手機在河南蘭考縣人民醫院太平間。
11日凌晨,孫東林趕到蘭考縣公安局,抱著試試看的態度去了醫院太平間。“一個老人問我找的是不是一個50多歲的男人和一個40多歲的女人,我的預感越來越強烈。看到他們時我當即就暈倒了。”
“我有一種強烈的愿望,一定要替哥哥把工錢送到工人手里。”在民警的指引下,孫東林找到哥哥已被撞爛的轎車,他發現26萬元現金完好無損地放在后備箱下放備用胎的地方。“哥哥今生不欠人一分錢,不能讓他欠下來生債。”30多個小時沒合眼的孫東林動身往家趕。
12日上午,他趕回武漢老家。哥哥意外離世,賬單多已不在,孫東林不知道該給每位工友發多少錢。他讓工人們憑良心領錢:“大家說差多少,我就給多少。”孫東林給60多位工友發了33.6萬元——除哥哥留下的26萬元,他自己掏了6.6萬元,再加上母親的1萬元養老錢。
王保田:“為什么他們不理解什么是愛?”
王保田,男,生于1967年,安徽省阜南縣人。
43歲的王保田在北京承包了某單位的物業工作,月薪2000塊。妻子在某大廈當保潔員,月薪800塊。夫妻倆住在單位提供的一間6平方米的單人房里。讀高中的一雙兒女與爺爺奶奶一起在老家生活。
2009年11月4日,兒子王鑫在學校上廁所時突然暈倒,被診斷為急性腦出血,剛推進手術室,呼吸和心跳就停止了。從北京回老家的火車上,王保田聽醫生說要“準備后事”了,他立即決定捐獻兒子的遺體和器官。
不料,等著他的卻是一個遠超過他想象的復雜的捐獻之旅。轉入重癥監護室上呼吸機、輸液后,王鑫“死而復生”,似乎恢復了呼吸和心跳,臉紅撲撲的。王鑫并不能被界定為死亡,但醫生同時暗示:“已無搶救希望。”
這期間,王保田成了主治醫生和廣東省紅十字會間的電話轉接員,光打給深圳紅十字會負責人高敏的電話費就高達400塊。耗時一個月零兩天,完成繁復的“規定動作”后,醫生宣布王鑫“無搶救價值”。王保田夫婦終于得以與深圳紅十字會簽署器官捐獻協議,無償捐獻兩個腎臟、一個肝臟和一對眼角膜。
維持救治期間,王家在北京借的4萬塊、在老家借的4萬塊和王鑫的學校捐的3萬多塊已全部花光,還欠醫院2萬多塊。捐獻實現后,王保田拒絕“照慣例勾銷欠費”,他堅持“就算傾家蕩產,我也要還”。從第一例器官捐獻以來,整個中國不過130例,像王家這樣自己舉債要捐器官的絕無僅有。
火化、埋葬兒子后,王保田向北京的朋友借的1萬塊還剩2700塊。他揣著這些錢去醫院準備還賬,在電梯間錢被偷走。搶救兒子的32天里,王保田沒哭過,但這次他止不住掉眼淚。他說:“我不是為兒子哭,也不是為自己的錢財哭,我為這個世界擔憂——為什么他們不理解什么是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