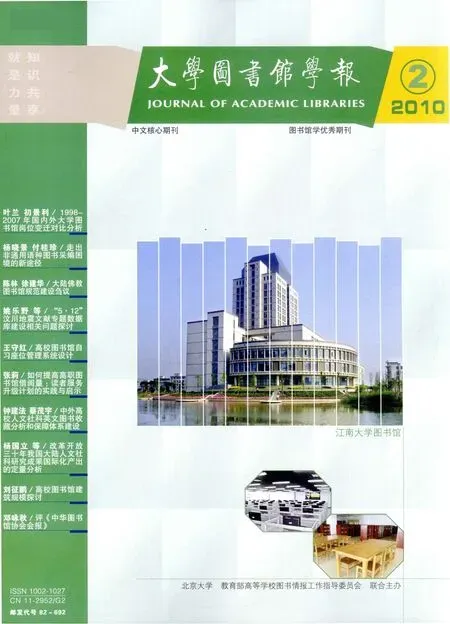評《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
□鄧詠秋
《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①《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發行時間長(1925-1948),卷期多(共發行21卷102期),目前海內外大圖書館也很少能有完整無缺的收藏。2009年6月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將該刊全部按原樣影印出版,精裝為5大冊,另附一冊新編的索引(趙俊玲等編,單獨列為一冊,即第6冊),本文的寫作要感謝這部索引的指引和幫助。(以下簡稱《會報》)與中華圖書館協會是分不開的。中華圖書館協會于1925年4月25日成立于上海,并于6月2日在北京舉行成立儀式,在抗戰前,總辦事處一直設在北京。作為中華圖書館協會傳達消息的刊物,《會報》于當年6月30日在北京創刊發行。該刊為雙月刊,于1948年5月出版第 21卷第 3、4合期后停刊。從1925年至 1948年,僅有一年停刊(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共發行了21卷 102期(第2期和第3期合并刊行,只算作一期)。
《會報》與《圖書館學季刊》、《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并稱為民國時期三大圖書館學期刊。以往的研究比較重視另兩種刊物的價值,相對比較忽視《會報》的價值。但筆者認為,《會報》在中國圖書館學發展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它的地位獨特,不可替代。本文打算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探討《會報》的價值。
1 有助于增強圖書館界的凝聚力,促進事業發展
從學術高度來說,《會報》不及《圖書館學季刊》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但是在揭示全國圖書館界的狀況、增強本行業的凝聚力方面,它發揮了重要作用。在中國,現代圖書館事業和圖書館學的歷史不長。要想取得較快的發展,并且在社會上得到承認和重視,光靠一個館或幾個人的努力是不行的。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當時圖書館界和教育界的一些人士認識到群策群力的必要性,同時受到美國圖書館界友人的推動,于是組織成立中華圖書館協會這個全國性組織,以便在圖書館界內部加強合作與交流,對外以圖書館界集體形象去爭取本行業的權益。《會報》全面報道、廣泛刊載全國各地圖書館界的各種信息,實際上辦成了全國圖書館事業的總通訊社。“本報為本會傳達消息之刊物,極愿以此為全國圖書館事業之通訊機關。凡圖書館或各地圖書館協會之任何消息,皆愿代為露布”[1]。《會報》設有“圖書館界”欄目,報道國內外圖書館界的各種消息,如與圖書館有關的法令頒布、某某圖書館工作近況、某圖書館最近獲得一批特色館藏、圖書館學暑期學校招生、圖書館界的新發明、湖北黃安七里坪設農民圖書館、香港輪渡上設圖書室等,都有介紹。《會報》對與圖書館有關的各種信息皆盡量刊載。通過這個獨特的平臺,圖書館界人士的行業認同感和自信心得到了強化。
在促進事業發展方面,《會報》曾發表《圖書館學書目舉要(初學書目)》、《圖書館學中西書目舉要》等,這些對于促進圖書館員繼續學習是很有用的。還刊載過《圖書館員的生活》(金敏甫)、《圖書館員立身準則》(于震寰譯)、《圖書館員應有之真精神》(喻友信)、《辦民眾圖書館者該怎樣鼓勵人民樂于來館閱覽?》(朱金青)、《辦理農村圖書館應注意的幾點》(楊海樵)、《創設和辦理圖書館應注意之點》(方金鏞)、《彈性組織之縣市圖書館》、《對于圖書館建筑應注意之數點》等,這些文章涉及圖書館工作的方方面面,或者飽含專業熱情和創意,或者介紹成功經驗,對圖書館界很有指導意義,有助于促進圖書館事業整體發展。
2 有助于更好地發揮中華圖書館協會的行業領導作用
中華圖書館協會是一個在自愿基礎上組成的民間團體,它不具有政府組織的強制性權力。作為行業協會,中華圖書館協會要想發揮引領全國圖書館事業健康發展的作用,必須通過開展多方面的工作,提供有效的服務,以獲得行業內的認可和尊重。比如,協會的主要經費來源是個人會員和機構會員上繳的會費,關于這些會費的使用情況,《會報》上有詳細的記載。通過這種公開透明的方式,可以讓會員了解協會的財務情況,并加以監督,使大家信任協會。另外,協會的各種活動、周年總結等,都在《會報》上有詳細刊載,中華圖書館協會還開展過許多有價值的活動,如調查全國圖書館等,這些也反映在《會報》上。可以說,因為有了《會報》,就有了集中宣傳中華圖書館協會所做工作的陣地,協會的領導能力和凝聚力得到了增強。
協會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是對外爭取本行業的權益。據《會報》所載,中華圖書館協會曾致電當局,反對印刷品郵資加價;向立法院力爭,強調圖書館這種社會教育機關的重要性,要求私立圖書館及民教館之獎勵或補助應列入憲法;還曾力爭平津書籍免稅等。通過《會報》的出版,協會在這方面所做的工作得以傳播到全國圖書館界,使他們面對政府和其他行業時,不再只是孤獨的一個館,而是有一個全國性行業協會代表他們發出強有力的聲音,這樣一來,也讓圖書館界更加信服協會的領導。
3 推動學科建設,提高圖書館學在學科之林的地位
《會報》與《圖書館學季刊》都是中華圖書館協會辦的刊物,但它們在刊載內容上有區別。《圖書館學季刊》主要刊載圖書館學專業的長篇論文。而《會報》上很少刊登長篇學術論文,它雖設有“論著”欄目,但主要刊登的是對圖書館實踐工作有指導性的文章,或某圖書館的概況。可是,我們仍然強調《會報》具有推動學科建設的貢獻,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一)《會報》雖不直接刊載長篇學術論文,但它經常通過小消息和“新書介紹”欄目,簡要而廣泛地報道圖書館學術界的研究進展,如圖書館學界的主要研究成果、創新與發明,常在《會報》上有介紹。(二)中華圖書館協會下設圖書館教育委員會、分類委員會、編目委員會、索引委員會、出版委員會等,這些委員會的研究活動和研究成果,經常在《會報》上介紹,這對于推動本學科的發展是很有益的。(三)《會報》重視刊登對圖書館實踐工作有指導性的文章,還經常發表有關文獻學研究、索引編制的成果,如《永樂大典現存卷目》(袁同禮)、《山西藏書考》、《冊府元龜索引》(呂紹虞、于震寰編)、《川大舊藏書版修印紀》(孫心磐)、《東北事件之言論索引》(錢存訓)、《進行中之各種索引》等。這表明,當時的圖書館界一方面繼承傳統目錄學的思路,在文獻整理方面繼續努力;另一方面則借鑒西方圖書館學注重編制索引、提高檢索效率的思路,在參考服務方面做了不少實事。通過報道這些研究成果,《會報》營造了一個很好的專業研究氛圍,有助于鼓勵圖書館界開展類似工作,從而推動學科建設,并提高圖書館學在學科之林的地位。
4 保存了很多重要的圖書館史資料
《會報》是民國三大圖書館學期刊中發行時間最長的一種,跨越24年(1925—1948),保存了很多重要的圖書館史料。在內容上,《會報》很重視報道圖書館界的動態,廣泛刊載國內外圖書館界的消息、協會的各種活動、會員消息、新書介紹等,這些資料本身研究性不強,卻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極為寶貴的基本資料,我們可以在其基礎上開展很多研究。
《會報》不僅報道大圖書館的動態,也相當重視對小圖書館,如縣圖書館、鄉村圖書館和特色圖書館的報道。現在我們研究圖書館史,諸如國家圖書館、浙江圖書館等大館的資料并不難找(因為大館常編有館刊、本館概況等文獻),但是如果想從全局和宏觀上把握當時圖書館界的情況,如全國到底有多少圖書館,各圖書館的經費和讀者情況,全國圖書館教育開展情況,抗戰時期的圖書館事業等等,我們就必須求助于《會報》。《會報》對當時各圖書館的經費、章程、藏書、讀者人數等都有相當的報道。這些調查數據對于我們研究圖書館史是很珍貴的。尤其是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在條件艱難、很多期刊停刊的情況下,《會報》編輯部仍輾轉昆明、成都、重慶三地,堅持出版,報道全國圖書館界消息,為我們保留了一份相當可貴的歷史資料。可以說,離開《會報》,就寫不了抗戰時期的圖書館史。
而且,并不是每個行業都如此幸運。比如在研究出版史時,由于當時出版業沒有這樣一個全國性行業組織和這樣一份內容豐富的“會報”,因此我們很難獲得當時全國出版社的各種宏觀數據,因此在研究民國出版史時,現有的研究不得不過分集中于商務印書館等少數大出版社。
5 會員交流的平臺
《會報》有一個重要的欄目是“會員消息”,主要報道協會個人會員的消息,如工作變動、地址變更、新著出版、婚喪嫁娶等。被報道的會員達600多人,有些比較活躍的會員多次被報道。從當時來說,《會報》起到了會員之間互相聯絡的作用。從對后世的作用來說,這些會員消息也是我們研究當時圖書館學人生平脈絡的重要線索。
由此,我想到,當前圖書館界也有不少新聞消息(或稱“八卦”),但往往分散在小范圍,處于一種無序流傳的狀態。民國時期的圖書館界已經很重視這些業內同人的新聞消息,通過《會報》來網聚行業內的新聞,加以系統的整理和刊布,這種做法或許也能給我們今天的工作帶來一些啟示。圖書館界是否仍然需要類似的平臺,來集中發布一些本行業的娛樂和非娛樂新聞?我想,類似的行業平臺,對于聚集行業人氣、提高行業歸屬感和從業快樂感,會有一定幫助。
6 有助于國際交流,相互了解
中華圖書館協會成立后,代表中國圖書館界,派員參加國際圖書館協會年會,與國外圖書館協會平等往來,在促進交流與發展方面都發揮了作用。這些在《會報》上都有體現。《會報》為中國圖書館界提供了開眼看世界的機會,使他們能從全世界范圍汲取養分,從國外同行那里取其所長,從而發展中國圖書館事業。如國際圖書館大會代表沈祖榮撰寫的《參加國際圖書館第一次大會及歐洲圖書館概況調查報告》[2],使許多無緣出國參會的國內同行能夠分享他的所見所得。又如,中華圖書館協會推舉美國圖書館學家杜威為名譽會員。1925年 9月,74歲的杜威致信給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上刊登了這封信的英文原文和中文譯稿[3]。在信中,杜威回憶了自己于49年前創立美國圖書館協會的情形。他說,美國圖書館協會成立之初,會員僅30人,經費全無,杜威服務其中,不僅沒有報酬,而且經常要自己負擔費用。而49年后,美國圖書館協會會員將近一萬,并且通過其努力,獲得了社會的認可,還獲得了包括卡內基在內的基金會的資助。杜威以此為中華圖書館協會打氣,鼓勵中國同行克服草創時期的困難,以圖將來協會和全國圖書館事業的大發展。可以說,類似的國際交流,對于鼓舞中國同行的信心是很有益的。《會報》還積極報道國外優秀的圖書館界研究成果和工作經驗,如《日本圖書館學雜志目錄》、《圖書館員職業道德規約》(美國圖書館協會職業道德規約委員會擬訂)、《關于索引的方法》(黎劭西譯)等。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侵略者對中國圖書館和文化事業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從《會報》來看,中華圖書館協會開展了一些工作,如致函各國圖書館協會并爭取到國際上的同情與支持。這些活動促進了當時國際圖書館界的互相了解。
簡要地說,《會報》的價值可以從兩方面來探討,一方面是它在當時的意義和價值,另一方面是它對后世的意義和價值。就當時來說,《會報》的出版,給全國圖書館界提供了一個交流的平臺,增強了行業的凝聚力,對于事業發展和學術研究都有促進作用。從后世來說,《會報》留給我們一筆豐厚的歷史數據,不僅對于研究圖書館史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即使不專門研究圖書館史,我們也可以從這些豐富的數據中找到學術研究的興奮點,獲得事業發展的靈感。
1 本報啟事一.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1925,1(3):2
2 沈祖榮.參加國際圖書館第一次大會及歐洲圖書館概況調查報告.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1929,5(3):3-29
3 杜威博士來函(致中華圖書館協會董事部函,中英文).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1925,1(3):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