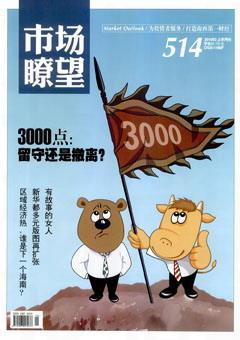幸福沙巴
王海燕
施舍·餐廳
從Hanoi到Lao Cai,混在黝黑瘦小的本地人之間,坐了幾個小時的火車,整夜不能睡,困倦夾雜著不安讓抵達沙巴的最后一個小時車程顯得漫長而無望。加上整整一個月的長途旅行使身體的疲累積壓到某種極限。綿密的細雨,以及山區的冷洌,我盼望任何形式的停留,洗個熱水澡,喝杯熱咖啡,成了最迫切的渴望。
土布扎染的衣裙,藍色花紋的綁腿,我沒有任何疑慮地跟隨著那個洋溢著純凈笑容的當地女孩走進了這家擁有三層樓房的Lotus Hotel,這一路,蓮花盛開。
紅色的三角形屋頂、奶油色的方形粉墻和棕黑色的條形窗框,回旋的樓梯鋪滿美麗的馬賽克,環形的廊道怒放著艷紅的花蕾,連房間里的床亦掛著公主的白色帷蔓,宮廷般高貴與典雅。打開房門,看得到群山環繞的山谷,云霧繚繞的小鎮,真的無法不為這蓮花所感動。
因為這深秋的冷,每天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去沿街的小餐館一杯兩杯三杯地喝熱巧克力,直到心也溫暖起來。我喜歡那直直開啟著的落地的玻璃門,聞得到空氣中的潮濕味道,然后有兜售著手工布衣的寨子里的女人們依著門向你展示她的心靈手巧。
餐廳的角落里坐著三五個來避暑的年輕人,他們一邊打量著一邊竊竊私語,然后有個男生怯生生地走過來用生硬的英語問我,你從什么地方來。我回答了他,然后司是不是你贏了?他羞澀地點點頭,然后得意地回去告訴同伴。再后來在教堂前的夜市上遇見,他幫我買了紫色的烤紅薯,不可思議地看著我捧著它滿臉幸福香甜。
廣場·教堂
寬闊的廣場邊豎立著偉岸的沙巴教堂,一百年前的法國傳教士留下來的灰色建筑在薄紗般的白霧里萬般不真實,晦暗、瘦削的體形加上風蝕雨襲得傷跡累累的外墻,處處透著滄桑與荒涼。沒有彌撒,沒有唱詩班,安靜地坐在那窄小的,冷硬的木條凳里。
真的是經歷太多戰爭苦難和風雨洗禮了,教堂內部破落到凄慘,連那彩色的格子玻璃亦不再擋得住風雨,瘦弱的耶口被無情地掛在十字架上,周圍有五彩的花束,風琴的聲音悠揚起來,Komert for orgel in a manjor演奏了幾十年的樂曲霎那間充滿了整個空蕩蕩的教堂,仿佛來自天堂的呼喚,荒涼破敗的建筑擁有了無與倫比的神圣和純凈,而心靈也像被洗過一般。抬起頭看不到掩在風琴后年輕的神父的臉,想著這琴聲是這個不會英語的神父獨特的交流方式了吧。海拔一千八百米的清秋,迷霧里的冷,我裹緊身上的衣,不再奔忙不再行走,只一心一意在這里聆聽上帝的聲音……
側門出來,經過有籬芭圍起來的小小花園,轉身看到蒙族的年輕夫妻肩并肩坐在教堂前的石階上,女人膝上放著小小的嬰孩,男人的身邊放著被塞得滿滿的竹簍。坐了一會兒,男人起身接過孩子放列女人的背上,然后從簍里拿出一塊上彩的寬長布匹,女人接過來,熟練地在胸前背后綁了個x型包裹住背上的孩子,然后,男人小心地整理了一下包在外頭的那塊繡滿紅色花紋的蠟染背帶,女人直起背,男人背起竹簍兩人并肩走進那暮色里,隱隱約約,空氣里彌漫開一種叫做幸福的味道。
想起旅館的背包里那塊裹背要比女人身上的更精致更鮮艷,可是,天注定,這塊裹背將會失去其最質樸的作用,絕不會有一個這樣的穿著粗布藍衣的男子將一個孩子放在我的背上,與我并肩歸家。也許是裹背的悲哀?
黑蒙族·紅瑤族
整個沙巴的生活就是山與山之間的行走,云霧繚繞中的漫步。趁著午后若隱若現的陽光Walk to Cat Cat Village恐怕是最愜意的。
進入這里的第二天,早已入鄉隨俗地穿上了黑蒙族的粗布藍衣,前襟是精致的十字繡片,胸前,有清脆的鈴鐺代替鈕扣,百褶裙、花綁腿,甚至以為自己可以去巴士站做沙巴最美麗的旅館接待員。
三公里的山路并沒有想像中的容易,不停地上坡,下坡,從一座山繞到另一座山,直至見到隱在山谷里的小村落。有梯田,有瀑布,這里遠比不上元陽哈尼人的山寨,可是,這里依然有我渴望的遠離城市的靜謐。簡易的染坊邊掛滿了靚藍色的衣料,早已有原住民圍上來兜售手工刺繡的衣物,我假裝生氣地挽起袖子給她們看因為植物染料褪色所造成的藍皮膚“瞧,你們把我變成了藍色的。”她們拿著自己手上的織物捂著嘴咯咯地笑,取笑我是藍色的。我拉過其中一個的手,開心地笑“你也是藍色的。”彼時彼地,我確是她們中的一員,坐在路邊的石階上和她們一起歡笑,我問那個怯怯躲在人群后面的小女孩“我像不像你的姐姐。”她聽不懂,只是躲在大人的身后偷偷看著我笑。
我當然像,來的路上遇到兩個法國人非要與我合影,照片拍完才發現我手里的相機,一問一答才知道上了當,大方與其合影的并不是她所期待的Black HMong,而是中國人。我對著她得意地笑說不用謝,法國女人滿臉尷尬。
下了一夜的細雨,沙巴新的一天又在這糾纏不清的薄霧里開始。
餐廳的招待說,從Sapan到Tay族的聚居地Banho只需四十五分鐘,然后走過吊橋,穿過稻田進入紅頭瑤的村寨LanFu,下行過河上山到Lancom,最后抵達XaFo,這一路視野開闊風景秀麗,是“best way”,他似乎忘了告訴我雨后的山路舉步艱難。
在Sapan村口,我堅定地拒絕了當地人推銷的竹棍,并且得意洋洋的告訴她們我有三個腳的鐵架子,事實證明,泥濘的鄉間小道上,沉重的角架只會帶來負擔,抵達Banho,終于有個瑤族的男孩子自告奮勇要做我的向導。十二三歲的孩子,藍色的衣衫下身子單薄得讓人心驚,我開著玩笑問他蒙族的帽子是黑色的,你是瑤族為什么不戴個紅帽子,他低聲回我只有女人才戴。他將手里的竹棍梯給我,扛起我的角架拎上我的水瓶以三五倍的速度向前走,轉身看到我在泥濘濕滑的鄉間小路上狼狽蝸行,為了不落下距離,我努力加快速度,然后終于以某個非常難看的姿態滑倒在地,聽到我的驚呼,他折回來猶猶豫豫地伸出手,眼里寫著羞怯。
風雨兼程兮誰人與共,路漫漫兮何人為伍,在這遠離家鄉的偏遠村落,我竟然如此無助地依靠于這般瘦小的他,我絕不能想像如果沒他,這段七小時的路程將如何走完,在沙巴,親近的接觸泥土的味道,也感受一個孩子的堅強。
旅行者·原住民
街邊的咖啡館里,坐著徒步回來翻著旅行手冊的年輕人;灰褐色的陽臺上倚著短袖短褲不怕冷的鬼佬;金發綠眼的法國女孩穿著藍黑色繡花立領的民族服裝,遠遠看像極了黑蒙族的孩子,路邊的水泥地上坐著曬得黝黑的日本人用笛子吹著不成調的“茉莉花”。
街上三五成群的藍黑色本地人四處游蕩地兜售著她們的土產;廣場上的孩子蹲在街邊烤著雞蛋、板栗以及顏色怪異的紅薯;從偏遠的村寨里趕來購置生活用品的瑤族盛裝出現在市場里,年輕的Tay族女子倚在門前問里面的人可不可請她吃個冰淇淋。
從上了年紀的老太太那里買了全套的本地行頭,她喜悅地抱住我與我合影告訴我她有多么喜歡我;不會一句漢語的女人告訴我她跋山涉水走了一星期才從中國的山寨走到這里,并遞給我看她手上的銀鐲子里刻著的中文名字;火車上坐在我對面的河內人在沙巴街頭與我相遇,卻沒有辦法溝通,于是拉住擦肩的紅瑤族,他跟紅瑤說越南語,她翻譯成英文告訴我,然后我再用英文回答,她再翻譯給他聽,有好奇的法國人湊上來,然后紅瑤族又開始說動聽的法語。
沙巴是個神奇的城市,各種的文化在這里交融,所有人都會在這里找到合適的生活方式,做著手工活兒的少數民族,避暑的越南人,度假旅行的法國人,這個城市在迷霧一樣的山谷里散發出它獨有的味道。
離開沙巴的那一天,我在你送給我的旅行筆記上寫下一句話:遠離你,遠離痛苦;遠離你,靠近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