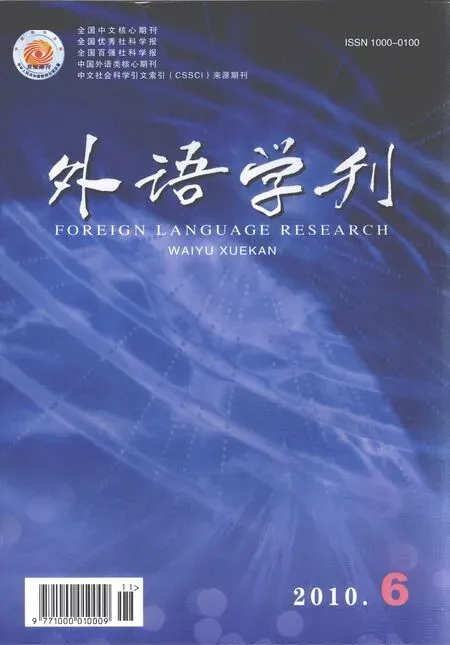《爵士樂》的后現代性及其語用學闡釋*
——文學語用學的一個范例
荊興梅 馮敬玉
(江南大學,無錫214122;無錫職業技術學院,無錫214122)
文學語用學(literary pragmatics,簡稱LP)起始于20世紀70年代。本論文力圖通過語用學理論視角觀照小說《爵士樂》的寫作特征:分別用預設理論、關聯理論和禮貌原則來闡釋文本的“反偵探小說模式”、“開放性文本”、和“主體性”等后現代主題和敘事策略。
1 預設理論與反偵探小說模式
德國邏輯學家弗雷格(Frege)在1892年提出預設(presupposition)概念,20世紀50年代后納入到語言學研究領域,是自然語言中一種特殊的推理手段,也是命題成立必須具備的相關前提條件(涂靖2005:71)。語用學認為,交際雙方并非一方說一方聽的單向過程,而是相互協作和制約的互動過程。說話者為了能夠使自己的信息和意圖為聽話者接受,需要對社會文化語境、談話內容的上下文和聽話者知識結構等,作出合理估計和預測。在文學語用學范圍內,作者和讀者被視為通過文本進行交流的主體,預設實際上指的是讀者的閱讀期待,是作家在創作時對讀者群體的社會意識形態、閱讀水平、閱讀程式的綜合考慮。卡勒在《結構主義詩學:結構主義、語言學和文學研究》中把文類看做一種程式:“人們可以說,文類是一種語言程式的約定俗成功能,一種聯系世界的特定關系,這種關系起到了引導讀者在與文本的接觸過程中的規范或期待作用”(Jonathan Culler 1975:136)。也就是說,作者和讀者之間有著心照不宣的默契,一般情況下,唯有符合傳統寫作框架,才能讓讀者心滿意足。比如散文有散文的格式,詩歌有詩歌的形態,而科幻小說和言情小說,又有著各自獨具一格的模式,對這一切讀者早就了然于心,這就是所謂的文學程式。涉及偵探小說時,卡勒說,“說明文類程式力量的特別好的例子是偵探小說:人們認為小說人物從心理學上說是可理解的,犯罪會得到解決,這一解決最終會被揭示,相關的證據會被出示,但解決的過程會有些復雜,所有這些都是構成這類書的快樂的不可缺少的東西”(Jonathan Culler 1975:148)。
小說《爵士樂》,顯而易見違背了偵探小說的文學程式。在傳統的偵探小說中,懸念疊出機關重重,通過觀察、推理和判斷等,搜集犯罪證據,推斷犯罪動機,最終以抓住兇手使之鋃鐺入獄結束。《爵士樂》以驚心動魄的謀殺案開場,喬因為爭風吃醋槍殺了多卡絲,而在多卡絲的葬禮上,維奧萊特氣急敗壞地闖進去,不顧一切地企圖用刀劃破死者的臉。開篇短短幾頁,敘述者不僅讓兇手及其謀殺動機大白于天下,還言簡意賅地介紹了故事的來龍去脈和各個主要人物的相互關系。并且也沒有安排兇手被繩之以法大快人心的結尾,而是一反常態地讓人們對喬的所作所為不予追究,使他和維奧萊特重歸于好,回復到正常和諧的家庭生活中。可見,小說對傳統的偵探小說文學程式進行了徹底顛覆,在和盤托出情節主線之后,不遺余力地探尋主人公的心路歷程和歷史淵源。這就是為后現代作家們推崇備至的反偵探小說模式,它擁有消解懸念、結局前置等諸多解構主義和后現代性特征。
反偵探小說模式與語用學范疇內的預設沖突(presuppositional clash)不無關系。如果說預設表達的是根深蒂固的傳統程式,那么預設沖突表達的就是預設的信息(指被期待的信息)和語篇的信息形成沖突和矛盾,也就是人們常常說的“出乎意料”。休特說,“預設沖突是理解喜劇、荒誕作品的主要機制之一”(Short 1996:236)。《爵士樂》有別于這兩種文類,它的反偵探小說模式卻與語用學中的預設沖突一脈相承。在預設沖突機制下,反偵探小說挫敗了讀者根深蒂固的閱讀期待,另僻蹊徑向傳統挑戰,使文本具有了厚重的歷史維度,對主題的提升和渲染功不可沒。
2 關聯理論和開放性文本
小說《爵士樂》借鑒了同名音樂的敘事風格,留下了大量空白和盲點,這顯然與話語交際中的關聯理論背道而馳。作品分為10章,各章既沒有標點也沒有序號,章與章之間用兩頁空白紙隔開,開創了敘事形式變革的先河。首先,文本采用了非線性陳述模式。比如第二章中,第一部分回憶了1906年喬和維奧萊特滿懷憧憬奔赴北方大都市的情景,第二部分又回到了1926年“爵士時代”紐約哈萊姆黑人社區,此時的喬正對多卡絲心醉神迷欲罷不能。其次,文本具有爵士樂即興、隨意的特征。多卡絲死后不久,維奧萊特邀請多卡絲的朋友費莉絲來到家中,冷不丁冒出一句:“萊諾克斯大道上的三角丑聞就這樣開始了。這事好不了,指不定誰要朝誰開槍呢?”(托妮·莫里森2006:5)讀到此處,人們不禁心存疑惑:三角丑聞不是剛剛結束嗎?如果卷土重來又會是誰深陷其中呢?明明主要人物都獲得了一定的人生啟示,難道一切又付之東流嗎?再次,文本充滿了爵士樂般跳躍、突兀的格調。作為有教養的中產階級婦女,維奧萊特竟然去偷竊別人的嬰兒!這本來就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再加上對處理過程和結果沒有任何交代,就更加令人大惑不解。從語用學的角度來看,所有這些描寫都屬于不關聯,完全違背了說話者需要“明示”的原則。
然而,這正是作家托妮.莫里森的偉大和不同凡響之處,她在文本中設置了眾多盲點,來挑戰讀者的智力水平,增強文本的審美價值。后現代文學批評理論稱之為“鬼魂章節”,意指在不連貫的情節之間留下空白,讓讀者去思考和想象,從而體會深邃的言下之意:回憶和當下的情景交相輝映,表現出歷史對于現實的重要觀照作用;那句即興的“三角丑聞就這樣開始了”,表明黑人在現代和后現代社會遭遇到新的生存困境,這是一個發人深省的人類普遍命題;維奧萊特偷別人的嬰兒,是因為種族沖突害得她家破人亡,孤兒身份令她飽受心靈的創傷和煎熬,因而她年輕時發誓不要孩子以免他們遭罪,而如今她又追悔莫及。后現代作家致力于“開放性文本”的苦心經營,對于傳統的“封閉性文本”不屑一顧,目的在于消解作家至高無上的話語權,積極邀請讀者參與文本意義的建構。如果說傳統的“封閉性文本”帶給讀者的是“閱讀的愉悅”,那么“開放性文本”帶來的則是“閱讀的狂喜”,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式的痛快淋漓。正如Grice在合作原則中所闡述的,說話者可能有意不去遵守某一準則,但他相信聽話人會察覺出這一點,并認為他仍然是合作的;而聽話者也知道,說話者并不成心讓他蒙蔽,而是希望運用智慧理解其中的含蓄意義,這就產生了“會話含義”(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Grice 1975)。“在閱讀有較多暗含意和文化空白的文學作品時,我們會花費更多的努力處理,但卻可以得到更大的語境效果。因為文學作品的藝術效果大多存在于暗含意和文化空白中,每一部作品都帶有本民族文化的印記,并由此體現文學作品的審美價值。通過更大的處理努力,我們可以享受到文學作品所特有的含蓄美。”(廖巧云2003)
3 禮貌原則和主體性建立
利奇(Leech)對Grice合作原則中各項準則的普遍適用性產生質疑,意識到合作原則的不夠完備和健全,遂提出了“禮貌原則”(Politeness Principle,簡稱PP)。它包含6條準則:得體準則、寬容準則、贊揚準則、謙虛準則、贊同準則、同情準則。而布朗和列文森(Brown&Levinson)的“面子保全理論”(face saving theory),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這一理論認為交際中人的面子事關全局,可以分為消極面子和積極面子兩種,前者希望擁有一定的自由度,自己的行為不受干涉;后者希望得到他人的首肯和贊許。實際上,許多言語行為都威脅到人的面子問題,成功的交際往往在禮貌的氛圍中展開,盡量顧全交流雙方的尊嚴和面子。Sell說,“所有的交際行為,所有的語言,都是在禮貌參數范圍內運作”(Sell 1993:215)。
《爵士樂》中維奧萊特最終用愛和寬容重新接納了喬,要歸功于愛麗絲的一次又一次暢談和啟迪,而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恰恰是禮貌原則中的得體準則。大鬧多卡絲葬禮后,維奧萊特依然心煩意亂,她不厭其煩地頻頻造訪多卡絲的姨媽愛麗絲,意圖是微妙而復雜的:既有興師問罪的沖動,又有一探究竟的急切,更有大吐苦水的欲望。愛麗絲先回憶了當年自己丈夫的出軌事件,立即贏得了維奧萊特的響應和共鳴,這為后面雙方交流的成功和解決爭端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愛麗絲接著講述了多卡絲不堪回首的悲涼身世:“然而,愛麗絲相信自己比誰都更知道真相。她的姐夫……他被人從一輛有軌電車上拖下來活活跺死了。愛麗絲的姐姐聽到了這個消息,就回到家里盡量忘掉他內臟的顏色,這時,她的房子被點燃,她在火焰中被燒焦了。她唯一的孩子,一個叫多卡絲的小女孩,在馬路對面的好朋友家睡覺,沒有聽見消防車從街上呼嘯而過,因為人們呼救的時候它沒有來”(托妮·莫里森2006:59)。在東圣路易斯市1917年的種族暴亂中,多卡絲的父母雙雙死于非命。喬和維奧萊特都是歷經滄桑的孤兒,飽嘗種族歧視的苦難,相同的命運讓維奧萊特對多卡絲產生了強烈的認同感,欣然接受了愛麗絲的忠告:“斗什么,跟誰斗?跟一個親眼看見自己父母被火燒死的苦孩子?”;“我來跟你說一句。用你所剩的一切去愛,一切,去愛”(托妮·莫里森2006:118)泰戈爾這樣來闡述主體性(人格):“人生的整個目標是解放其自我人格為靈魂人格,將其內在力量轉變為向著無限的運動,從個人欲望的自我吸引轉變為靈魂在愛中擴散……我們的最高快樂在愛中……在這樣的愛中,我們的人格找到了它最高的實現”(Tagore 1917:97)。
錢冠連強調,言語得體是指在適當的時間和適當的場合,對適當的人說了適當的話(錢冠連2002:164)。語境是評判話語是否得體的重要標準,其中隱性語境所起的作用最為關鍵,因為隱性語境可以是交際雙方所共有的知識背景,可以是約定俗成的傳統習慣、定型的文化背景、習得的百科知識、必要的思維能力和語言運用原則等在人們頭腦中內在化、認知化的結果,具有潛在性、長期性和抽象性等特征,所以在隱性語境下考察話語的得體性更為復雜,更具有實際意義(金力2005:114)。在愛麗絲和維奧萊特的交流中,相同的個人遭遇、家族變遷和種族歷史等隱性語境,是她們的言語交際行為沖破阻礙獲得成功的關鍵因素。
4 結束語
文學語言與普通語言(或自然語言)本質上是相同的,并不存在顯著的差異,因此文學文本納入到語用學范疇進行研究,已經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青睞。《爵士樂》就是一個很好的范例,它的一系列后現代特征,如反偵探小說模式、開放性文本和主體性等,都可以運用語用學原理,如預設理論、關聯理論和禮貌原則得到鞭辟入里的闡釋。作者和讀者通過文本進行言語行為交際,文本中的人物也是不可忽視的交際對象,交流的循序漸進,意味著作品情節層層推進、主題不斷提升和審美逐步加強。正如言語行為理論所揭示的那樣:有時候完全遵守某些原則,會讓文本的演進如行云流水;而對某些原則的有意偏離,又會產生出奇制勝的閱讀效果,令讀者喜出望外。羅蘭·巴特曾說過,“語言是文學之在”(Ann Jefferson 1980:50)。文學語用學的發展呈方興未艾的趨勢,相信國內這方面研究碩果累累的局面將指日可待。
金 力.話語交際的三重解讀[J].浙江大學學報,2005(3).
廖巧云.關聯理論對合作原則的發展[J].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3(6).
錢冠連.漢語文化語用學[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
托妮·莫里森.爵士樂[M].海南:海南出版公司,2006.
涂 靖.語用理論和文學批評[J].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5(6).
Ann,Jefferson.The Nouveau Roman and the Poetics of Fic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Grice,H.P.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Cole and Morgan[A].Speech Acts[C].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5.
Jonathan,Culler.Structuralist Poetics:Structuralism,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M].Ithaca and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5.
Sell,R.D.Literary Pragmatics[C].Amsterdam: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1993.
Short,M.Exploring the Language of Poems,Plays and Prose[M].London:Longman,1996.
Tagore,R.Personality[M].London:Macmilan,1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