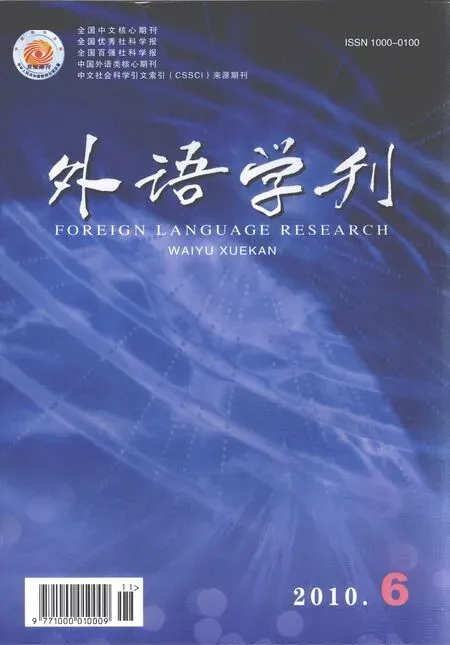本體論視域中的后期維特根斯坦語言觀*
——后期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思想系列研究之二
劉 輝
(黑龍江大學,哈爾濱150080)
1 引言
近年來,“語言本體論”成為語言哲學界的一個熱點(高云球2008:1-4,李洪儒2008a:14-17)。在世界-語言-人組成的系統中,語言發揮著中介的作用。人憑借語言同世界建立聯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后期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L.)探索的日常語言同世界和人具有相等的地位。也就是說,“語言處于人與世界之間,屬于多元世界中的一元”(李洪儒2008b:2)。本文將通過對比本體論語言哲學(ontolog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和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思想來論證后者語言觀的本體性。
所謂本體論語言哲學,是指“與分析性語言哲學(analytic philosophy of language)對應,把語言視為在者/是者(beings),探討語言如何在如何是,通過語言分析和解釋來揭示人和人的世界(包括人生活的外在物理世界)的科學”(李洪儒2008b:17)。本體論語言哲學涵蓋的范圍主要包括起源并發展于歐洲大陸的一些哲學流派,如結構主義、現象學、存在主義、解釋學、法蘭克福學派和后現代主義等。他們大多具有本體論思想的傳統,在各自的發展中,不同程度地表現出語言本體論傾向。反觀后期維特根斯坦,他的語言哲學思想可以大致理解為:語言是生活形式(form of life)中具有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s)的語言游戲(language-game)。只有通過語言的使用,人們才能理解語言的規則,并獲得判斷意義的標準。通過簡單比照我們可以看出,雙方至少在三個關鍵問題上存在契合點:語言的本質、語言的存在方式以及世界、語言和人三者之間的關系。
2 關注語言的本質
語言的本質問題一直是困擾語言學家和哲學家的難題。千百年來,人們從未停止過對它的追問。本體論語言哲學家們認為,語言本質上是一種特殊的在者/是者。其中,在歐洲大陸居于主流地位的現象學始終進行著語言本體論的探索。
現象學創始人胡塞爾(Husserl,E.)認為,語言一方面是日常交往和理解的工具;另一方面,也包括主體在心靈中使用的思維或意識。顯然,后者更接近語言的本質。有學者指出,胡塞爾對“語言”的理解可以是一種“符號意識”,也完全可以是一種“直觀行為”(倪梁康2007:443)。在這個意義上,語言是人意識的符號化。而胡塞爾的現象學又專注于意識領域,研究人在其中“內在的方面所發現的東西”(胡塞爾1992:100)。因此,對語言的研究自然也就成為現象學研究的核心。此外,由于意識是對客觀實在的一種內在反映,對意識符號化的語言同樣具有反映實在(實體)的能力。這樣一來,胡塞爾通過對語言的研究構建了一個關于“意識世界”的體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現象學對語言本質的理解具有明顯的本體論色彩。現象學的出現揭開了歐洲大陸哲學發展的新篇章,此后的哲學解釋學、存在主義和解構主義等流派的發展都受到它的影響。“整個歐洲大陸對于語言的觀察都是隨著胡塞爾意識世界的提出和建構才變得越來越清晰的。”(李洪儒2008b:50)
事實上,在維特根斯坦的前期思想中已經蘊涵了對語言本體性的思考。前期維特根斯坦認為語言與世界具有邏輯上的同構性,只有通過對語言的分析,才能最終達到對世界的認識。對此他說道,“我的語言的界限意味著我的世界的界限”(Wittgenstein 1922:119)。他的這一思想最終發展為“語言批判”(critique of language)理論,并真正引發了現代西方哲學的“語言轉向”(linguistic turn)。“語言批判是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思想的基點,是理解維特根斯坦全部思想的指針。”(謝群2009:26)該理論在確立語言在哲學中的核心地位的同時,也凸顯出語言的本體性特征。它表明語言不僅是我們認識世界的手段,也是我們認識的目的。這種手段與目的的一致,表明語言決定我們對世界的認識。我們只能在語言的范圍內完成對世界的認識。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語言的本體性特征才逐漸地顯現出來。
后期維特根斯坦站在反對本質主義的立場上,認為語言沒有本質。他說,“我不想指出一切我們稱為語言(sprache/laguage)的東西的共性,我想說我們根本不是因為這些現象具有共同點而用同一個詞來指稱所有這些現象”(Wittgenstein 1958:31e)。顯然,維特根斯坦眼中的語言是沒有共性或沒有本質的。他認為,語言是以目的為導向的、復雜的社會活動——語言游戲。對語言的反思或批判應該在語言的使用中進行。雖然維特根斯坦本人沒有界定這一重要概念,也沒有對其進行相應的歸納,但是,一些學者根據他的描述,歸納出語言游戲具有一些基本特性,如自主性、多樣性、易變性、目的性和自明性等(江怡1998:171-174;涂紀亮 2005:21-22)。這些特征表明語言不僅僅是簡單意義上的工具,而是一種更為復雜的現象。這些復雜的語言游戲從不同的角度反映著人和人的世界,同時也折射出語言自身的某些特質。更為重要的是,維特根斯坦認為語言具有某種本體性的色彩。他說,“紅色的東西可以被消除,但是紅色無法被消除,因此‘紅色’一詞的意義可以獨立于紅色的東西而存在……我們一但忘記某種顏色的名稱,對我們而言它就失去了意義;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再用它進行某種語言游戲了”(Wittgenstein 1958:28e)。這說明意義(使用中的語言)具有能夠獨立于外在指稱對象而存在的性質。不能出現在語言游戲中的語言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因而也就不存在了。在這里,語言同“存在”(to be)一樣,超越了存在與不存在的對立,成為一種本體。因此,同胡塞爾等人一樣,后期維特根斯坦語言觀是一種本體論意義上的語言觀。
3 注重語言的存在方式
既然語言是一種本體,那么它必然以本體的方式存在。但是,語言是一種特殊的在者/是者,是目的與手段的統一,一定會同現實發生聯系。換句話說,本體的語言一定要在具體的現實中展現自己。這就涉及到語言實際存在方式的問題,即它如何是、如何在的。
海德格爾(Heidegger,M.)認為,“語言的本性當然只能在那個發生的維度中獲得理解”(張祥龍2003:251)。也就是說,對語言本體性特征的理解只能在具體的時間和空間中進行。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我們如何將本體性與現實性統一起來?因為超越時間和空間的語言本體性,同展現在具體時空中的語言現實性之間存在著矛盾。對此,海德格爾給出的辦法是“把作為語言的語言帶向語言”。他解釋道:“無疑,這個公式首先指示著那個已經把我們本身攝入其中的關系網絡。尋找一條通向語言之路的意圖已經被糾纏到一種說話活動中了,這種說話恰恰要呈放出語言,以便把語言作為語言表象出來,并且把被表象的東西表達出來;而這同時也就表明,語言本身已經把我們糾纏到這種說話之中了”(海德格爾2004:239)。在這里,海德格爾強調的是語言的兩面性:本體性和現實性。這句中的三個“語言”既是相同的又是不同的。第一個“語言”強調語言的本體性;第二個“語言”強調語言的現實性;而第三個“語言”強調語言的統一性。這樣一來,他的這句話可以解釋為:把作為本體語言的現實語言帶向(統一的)語言。而實現這種統一的方式就是使用。通過使用,本體的語言具有了現實意義;通過使用,本體的語言展現在現實之中,并獲得自身的統一。
在這個問題上,維特根斯坦認為現實中的語言通過家族相似性而相互聯系。所謂家族相似性,是指“兩個相鄰的環節可能有共同的特征,而且互相類似,而屬于同一家族相距很遠的兩個環節不再有任何共性。事實上,盡管一種特征是家族所有成員所共有的,它不一定就是規定概念的那種特征”(維特根斯坦2003〈第4卷〉:66)。家族相似性決定語言存在的同時也展現語言的本體性特征。此外,維特根斯坦還用繩索的比喻來解釋這種相似性:“一段繩索的強度,不取決于任何一根能夠貫穿始終的纖維,而在于所有纖維之間的相互交織”(Wittgenstein 1958:32e)。顯然,本體性語言的存在方式說到底就是一個“是之所是,在之所在”的問題——語言能夠是語言本身,而不是其他什么。正是由于家族相似性的存在,日常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語言游戲才能夠既區別又聯系,它使得本體的語言能夠以現實的方式存在于日常生活中。這是后期維特根斯坦語言觀的核心之一。通過這一概念,他為我們提供一種認識語言和世界的全新視角。它在瓦解社會科學中本質主義“堡壘”的同時,也促進了當代認知科學、心理學和語言學等學科的發展。對此有學者指出,“維特根斯坦不僅用它來處理命題概念、游戲概念、語言游戲概念,而且也用它去處理許多其他一般概念”(韓林合1996:141)。
例如,我們可以用家族相似性來解釋語言的譜系現象。目前,語言學領域的研究表明人類語言具有一定譜系性:自下而上依次為次方言(土語)、方言、標準語、語支、語族和語系。整個人類語言群體由十幾個相對獨立的語系構成。我們可以將某一地域內的次方言群體進行的一切活動的總和看做一種語言游戲。這些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語言游戲又會在更大區域內以某種方言為基礎構成更高層次的語言游戲。以此類推,最終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最終的語言游戲模式——由不同的語言群體依據家族相似性構成的人類社會。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將人類社會看做一種具有本體性的語言游戲體系。體系內部的各種語言游戲沒有所謂的本質,只有家族相似性。這使得家族相似性具有更具普遍意義的解釋力,同時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它的本體性特質。因此,在語言存在方式的問題上,后期維特根斯坦同本體論語言哲學具有內在的一致性。
4 反思世界、語言和人的關系
世界、語言和人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語言如何將人和人的世界聯系起來的問題。伽達默爾(Gadmer,H-G.)等人認為,在具有本體論性質的解釋學循環(hermeneutic circle)中,語言使人同世界發生聯系,同時也使人與人之間相互關聯。對此,伽達默爾說,理解的循環一般不是一種“方法論的”循環,而是描述了一種理解中的本體論的結構要素(伽達默爾2004:347)。在他看來,這種循環不是主觀或客觀意義上的一種形式化運動,無法從方法論的角度來把握。決定這種運動的是能夠將人和人的世界聯系在一起的語言。語言的本體性作用使得我們在理解現實世界時必須要以前人的理解為基礎,而后人的理解又是建立在我們的理解之上。這樣一來,就形成由語言的本體性決定的解釋學循環。從這個意義上說,語言是理解人和人的世界的一把鑰匙。利科(Ricoeur,P.)也認為,“一切理解,不論是歷史的還是美學的,都牽涉到某種語言性(Sprachlichkeit)。這樣理解以后,語言就是人借以‘擁有世界’的東西:這個世界,不僅是一個環境;而是他與其保持一定距離并迎面把握的世界”(利科2004:422)。此后的解構主義和其他后現代主義者,大多從解釋學循環的角度出發,發展和建立了不同的理論體系。福柯(Foucault,M.)、德里達(Derrida,J.)和拉康(Lycan,J.)的許多著作都在談論語言的問題。盡管他們主要是從某種“破壞性”的角度通過語言來解構世界,但是這也從另一個角度驗證了語言的本體性地位。總之,對解釋學循環本體性的認識深化了人們對語言本體性的理解,有助于我們更好地了解語言、人和人的世界。
后期維特根斯坦認為,生活形式體現著語言、世界和人之間的緊密結合。盡管他沒有定義這一概念,但是他卻指出“想象一種語言就意味著想象一種生活形式”(Wittgenstein 1958:8e)。維特根斯坦把語言游戲稱做“生活形式”只是為了強調語言游戲是活動,是語言實踐;構成語言符號意義或“生命”的是活動或實踐,而不是心理的伴隨物(范連義2008:8)。顯然,語言游戲同生活形式可以通過語言實踐緊密聯系。維特根斯坦引入這一概念的目的在于“強調組成共同體的語言和實踐(或行為)的復雜體系之間至關重要的關系”(McGuinn 1997:51)。“生活形式”的引入對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思想具有重要意義:它一方面拓展了家族相似性的適用范圍,另一方面也為語言游戲提供了必要的基礎。前文分別將語言游戲和家族相似性同本體論語言哲學的相關概念進行了對比。通過分析,我們得到的初步判斷是:它們都具有本體的性質。那么,生活形式是否也同樣具有本體性的意義呢?我們認為,至少應該從兩個方面來看待這一問題。
首先,同語言游戲相比,生活形式更為根本。維特根斯坦曾經通過河床與河水的比喻,來說明二者的關系。他說道,“這種神話可能變為原來的流動狀態,思想的河床可能移動。但是我卻分辨出河床上的河流運動與河床本身的移動;雖然兩者之間沒有什么明顯的界限”(維特根斯坦2003〈第10卷〉:208-209)。這一比喻生動地反映出語言游戲和生活形式之間的相互聯系:流逝的河水必須以堅實的河床為基礎;同樣,稍縱即逝的語言,也必須以變化緩慢的生活為依托。此外,河水與河床之間還存在著一種“有趣的”聯系:當下河水的流向取決于此前河床對河水的影響,而今后河水的去向必然要以現在河床對河水的作用為基礎。這表明,語言游戲和生活形式之間也存在著一種類似“解釋學循環”的關系。
其次,同家族相似性相比,生活形式更為基礎。在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觀中,語言游戲和生活形式密不可分。家族相似性則體現著不同語言游戲之間的相互關系。同時,由于生活形式對語言游戲的縱向支撐和家族相似性對語言游戲的橫向聯合,使得三者成為一個聯系緊密的整體。顯然,提供縱向支撐的生活形式發揮著更為根本的作用。因此,生活形式也相應地成為家族相似性的基礎。三者之間究竟是怎樣的密切關系呢?維特根斯坦回答到:“人類的共同行為是我們解釋一種未知語言的參照系”(Wittgenstein 1958:82e)。這一方面說明生活形式是理解語言游戲和家族相似性的參照基礎,離開生活形式的依托,它們將成為無源之水;另一方面也表明家族相似性強化了語言游戲和生活形式各自的特點,失去家族相似性,它們將成為一個個孤立的點,無法構成日常生活的絢麗畫卷。
總之,生活形式同語言游戲和家族相似性一樣都具有本體性的色彩。甚至在某些方面,生活形式還表現出更為基礎、更為根本的特征。這種特征突出地表現為生活形式所具有的本體性作用。因此,在反思語言、世界和人的關系這一問題上,后期維特根斯坦同本體論語言哲學依然具有很強的一致性。
5 結束語
語言游戲說、家族相似性、生活形式、意義即使用和遵守規則等觀點在折射本體論語言思想的同時,也表現出向歐洲大陸哲學融合的趨勢。這突出地表現為他的語言觀帶有濃厚的人本主義色彩——通過語言關注人和人的世界。通過本文的對比分析我們發現:無論從語言的本質,還是語言的表現形式,或者是語言同人和人的世界的關系這三個不同的維度出發,我們都能得到后期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同本體論語言哲學的交集。這表明兩種思想體系在對待語言的關鍵問題上存在非常大的相似性。據此,我們認為后期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具有明顯的本體論傾向,而他的語言觀則是一種本體論語言觀。
范連義.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思想中的語用蘊涵[J].外語學刊,2008(5).
高云球.試論語言本體論的哲學基礎[J].外語學刊,2008(5).
海德格爾.在通向語言的途中[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韓林合.維特根斯坦論“語言游戲”和“生活形式”[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1).
胡塞爾.純粹現象學通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
江 怡.維特根斯坦傳[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李洪儒.西方語言哲學批判——語言哲學系列探索之七[J].外語學刊,2008a(6).
李洪儒.現代歐洲大陸語言哲學研究——站在流派的交叉點上[D].黑龍江大學博士后工作報告,2008b.
利 科.哲學的主要趨向[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倪梁康.胡塞爾現象學概念通釋(第2版)[M].北京:三聯書店,2007.
涂紀亮.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思想研究[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維特根斯坦.維特根斯坦全集[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謝 群.語言批判: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的基點——前期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系列研究之一[J].外語學刊,2009(5).
張祥龍.朝向事情本身:現象學導論七講[M].北京:團結出版社,2003.
McGuinn,M.Wittgenstein and the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M].London:Routledge,1997.
Wittgenstein,L.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M].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 Inc.,1958.
Wittgenstein,L.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M].New York:Barnes & Noble Publishing Inc.,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