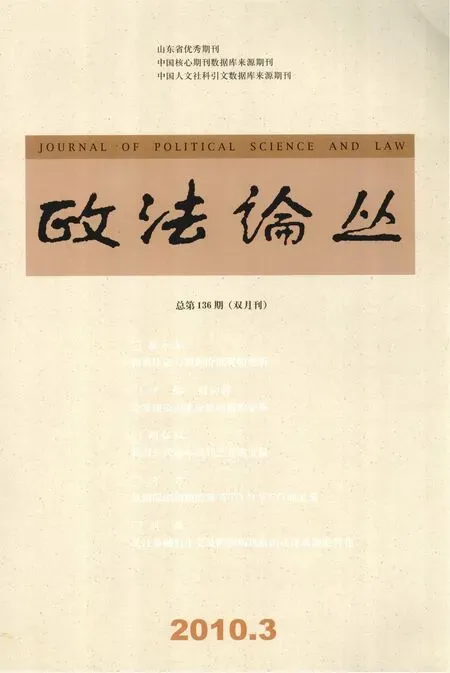宗教文化對中國傳統司法審判制度的制約與影響
張明敏
(山東省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山東濟南 250011)
宗教文化對中國傳統司法審判制度的制約與影響
張明敏
(山東省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山東濟南 250011)
宗教文化對中國傳統司法審判制度的滲透與影響是不容忽視的,表面看來宗教對中國傳統司法審判制度影響甚微,實際上宗教與傳統司法審判制度有著深層的糾葛,宗教成為歷代政治話語中法律權威性和神圣性的合理來源。其對司法審判制度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制度層面、司法理念層面、法律器物層面。
宗教文化 傳統 司法審判制度
宗教作為一種涉及面極廣的文化現象,一直對社會的各個方面產生著極其深遠的影響。在中國傳統社會,表面上看來宗教信仰不像西方國家那樣廣泛與普遍,宗教對法律影響甚微,在正式的司法審判程序里,也沒有用法律的形式明定鬼神的地位。但從中國幾千年的社會實踐來看,在中國古代,鬼神力量一直在潛生暗長,鬼神思想深隱藏于法律制度的背后,鬼神信仰成為中國歷史上從未間斷過的一種社會現象,法律運行中神靈的影響也一直揮之不去。本文試圖從制度層面、理念層面、法律器物層面探討傳統社會中宗教與司法審判制度的深層關聯,探究宗教文化對中國古代的司法審判實踐活動產生的深刻影響。
一、制度層面
(一)“神判”制度
“神判”制度即神明裁判制度,亦稱神示證據制度,指借助神力進行審判的一種鬼神定罪的審判方式,它是人類社會早期司法活動中經常采用的查明案件真相的重要方式。“神判”制度是“天罰”法律思想在司法審判領域中的體現。人類社會產生之初的原始社會,就普遍存在著對天地神鬼敬畏與崇拜的觀念,先人們認為冥冥之中有一種超人的神秘力量在左右和支配著自己,神會佑護正直無罪者,處罰邪惡之人。進入階級社會以后,公共的神被改造,并與王權、君權緊密結合,統治階級把自己的統治權和立法權、司法權說成是神的意志,任何觸犯現存政權和法律的行為,都被視作悖逆鬼神天帝的元惡大罪,就要受到“天”的懲罰。
神判制度在中國古代司法審判實踐活動的中,或強或弱地顯示著其作用。中國古代社會早期,神明裁判的現象在一定范圍內普遍存在。夏商時代,司法裁判的主要方式是神明裁判。根據古籍和甲骨卜辭記載,夏商“神判”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神獸定罪,二是卜筮決獄。神獸斷案,相傳在原始社會就已經出現。“獬豸者,一角之羊,性識有罪,皋陶治獄,有罪者令羊觸之。”[1]P231在商周時代的青銅器銘文里有一些提到訴訟時要由雙方向神靈宣誓的內容,如《甘誓》中啟即用“天剿絕其命”、“今予唯恭行天之罰”的旗號來討伐有扈氏。對其士兵,則用“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2]P249在商代,鬼神信仰廣泛而深刻地影響到商代社會的各個方面。商人沉迷于鬼神,他們把鬼神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我們從現存的史料就能窺見一斑。《禮記·表記》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商人凡事無不通過占卜向鬼神請示,如戰爭勝負、官吏任免等。在司法審判領域,定罪量刑也要訴諸鬼神。卜辭有:“茲人井 (刑)不?”占卜是否執行刑罰。“貞其刖”[3],占卜是否處以刖刑。“貞刖百”[4],占卜是否對百人處以刖刑。對處刑的后果也進行卜問:“貞其刖百人死”[5],貞問對一百人是否處以死刑。商代統治者在司法審判實踐中進行繁瑣的占卜,一方面反映出他們敬鬼神的神權思想意識,更深層的方面是利用鬼神麻痹被統治階級。“敬鬼神畏法令”(《禮記·曲禮上》),一語道破了“神判”的實際用意,“敬鬼神”是為了使人們“畏法令”。統治階級的法令被罩上了一層神秘的外衣后,就可借鬼神之名,“以教民事君”(《國語·周語上》)。進入封建社會后,神意裁判作為一種審判方式雖然已由明確的司法程序所代替,宗教信仰對司法審判制度的影響漸漸歸隱幕后,司法官吏一般不會像夏商時那樣直接讓鬼神介入司法審判,但具體的司法實踐中仍然保留了不少神靈的痕跡,神判與人判往往交織在一起。有的司法官吏借助神鬼蟲獸助獄斷案,依靠祈禱來求鬼神指明偵查方向。《論衡》載,東漢有個叫李子長的司法官吏,為了驗證被告說的是否是真情,制作了一個代表被告的木偶,放在蘆葦編的筐子里,據說如果被告真有罪,木偶就不會動,如果是無罪的,木偶就會動。[2]P216《晉書》、《折獄龜鑒》等書也記載了不少神鬼斷案的事例。至清代,有些偏遠的地方還有“神蛇斷案”、“沸油裁判”等迷信方式斷案的遺跡,在某些少數民族地區類似這種落后的做法,流傳的時間更久。如清人筆記《子不語》載,貴州平越府(今貴州福泉)衙門有個七尺高的石臺,衙門里還藏有十六只寫著“梵”字的佛經。按當地的慣例,凡有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不肯招供的,就請出佛經鋪在高臺上,要嫌疑人從佛經上滾過去。據傳凡無辜者滾過去平安無事,而有罪者滾到一半就會全身抽筋、目瞪身僵。這個習慣從元朝一直延續到清朝。
“神判”制度,使司法實踐活動與宗教信仰達到了前所未有的一致性、協調性,法律的神圣性與權威性借助宗教的神秘性而得以彰顯。但法律實踐的客觀規律性也被拖進了神秘的偶然性沼澤之中,難以顯示法律實踐本來的面目和力量。
(二)司法時令制度
司法時令制就是古人的天道觀念在司法實踐領域最主要的體現。古人認為,在司法活動中,行賞施罰必須順應天時,合乎時令,否則天將降災。春夏是萬物滋育生長的季節,秋冬則是肅殺蜇藏的季節,人間的司法活動也應與天道相配,順于四時,利用秋天的肅殺之氣強化行刑的嚴肅與震懾力。《左傳·襄公二十六年》中即有“古之治民,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的記載。《后漢書·章帝紀》記載:(元和二年)秋七月庚子,(章帝)詔曰:“《春秋》于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月令》冬至之后,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鞠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為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后漢書·陳寵傳》載: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是時 (章)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以為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事在于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十二月陽氣上通,……十三月陽氣已至,……若以此時行刑,……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為患。由此言之,災異自為它應,不以改律。”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此后,歷代帝王在確定大刑之日,要考慮陰陽節氣,唯恐違反時令會給國家帶來不利災害,以秋冬作為行刑決獄的傳統時間。《舊唐書·刑法志》記載: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金史·刑法志》記載:(世宗大定)十三年,詔立春后、立秋前,及大祭祀,月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未晴,夜未明,休暇并禁屠宰日,皆不聽決死刑,惟強盜不待秋后。“順天行刑”、“刑以秋冬”,成為歷代“秋后處決”的依據。自秦漢至明清,歷朝都有關于死刑執行時間的明確規定。唐律還把佛、道教的一些教規認可為法律,有關“十直日”的規定即是其中之一。《唐律疏議·斷獄》“立春后秋分前不決死刑”條規定:“其所犯雖不待時,若于斷屠月及禁殺日而決者,各杖六十。”其中的“禁殺日”就是“十直日”。十直日又稱“十齋日”,是佛、道教中有關每月中有十天禁止屠宰牲畜、釣魚及不準施刑的規定。此條在“疏議”羅列了這些日子,它們是每月中的“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凡在這些日子內行刑,唐律都要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以“杖六十”進行處罰。唐律還規定: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凡遇有大的祭祀活動、朔望日、上下弦、二十四節氣、雨未晴、夜未明、斷屠日,以及皇帝生日、元夕等法定假日,都不得奏決死刑。凡處決死刑犯人,都不得超過一天中的申時 (約下午三至五時),后世執行死刑的時間都習慣在正午前后。宋明以后基本沿襲不改。
(三)確立城隍的司法審判職能
在古代鬼神譜系里,與人們關系最密切的,莫過于城隍了。城隍在中國古代民間信仰中,是非常著名的陰間司法官,執掌審判世人善惡是非。但城隍神并非一開始就具有審判的職能,城隍神在唐以前,尚未被納入為統治階級政治服務的軌道。城隍神成為冥界重要的司法官,大致發生在中晚唐以后。[6]P321唐中葉以后,地方吏治敗壞,世間多不平之事,社會民眾需要一個具有公平、正直品格的超世俗的“平民化”的神來執掌審判職能。隨著城隍信仰在民間的逐漸傳播,部分地方官員也開始逐漸增加對城隍的尊敬,城隍地位大幅度提升,世俗權力抓住這一契機,開始有意識地利用城隍信仰。從唐代開始,封建政府將先前自然神性質的城隍神賦以政治功能,充分發揮其監察百官的職能。例如,唐代對城隆神己有封爵之舉,五代又陸續加封為王,宋代或加封號,或賜廟額 (匾額),明代更將城隍神與行政機構相配套,清代循而未改。朱元璋廢除宰相后,唯恐地方官吏不為己用,命令新官上任,必先齋宿城隍廟,參拜城隍神,向城神隍宣誓:“我等合府官吏如有上欺朝廷、下枉良善、貪財作弊、蠢政害民者,靈必無私,一體昭報!”每月的第一天和第十五天,官吏還必須到城隍廟兩次,申前誓。這類事情肇始于宋代,發展于明代,延續到近代。民國以前知縣、知府等地方長官上任時,按照慣例必須到城隍廟參拜宣誓。清代地方官吏在上任前,不僅要向城隍神宣誓,而且還要在城隍廟里住上一夜,聆聽城隍神的教訓,向城隍神坦露心跡。[7]
正由于統治者的需要,城隍執掌的職能與時俱進,逐漸從掌控陰間司法審判到常駐民間的司法官。①
自元代始,封建官吏便常把一些疑難案件放在城隍廟里審理。至明代,此風更甚。《大明會典》中十分具體地提到:“一府境內人民,倘有仵逆不孝、不敬六親者,有奸盜詐偽、不畏公法者,有拗曲作直、欺壓良善者,有躲避差搖,靠損貧戶者,似此頑惡奸邪不良之徒,神必極于城隍,發露其事;如有孝順父母,……畏懼官府,……神必達之城隍,陰加護佑。”[8]P576這就是說,每個府州縣都有一個城隍神,若有不孝犯上、奸盜詐騙、欺壓良善、躲避官府賦役的不良之徒,必有小神(如土地神、灶神之類)去匯報給城隍,城隍給予懲罰;若有孝順父母、畏懼官府的良民,小神也會報告給城隍神,城隍神則在陰間保佑這類良民。為了補救法網的疏漏,官吏們對城隍神抱有極大的期望。如清代著名的刑名幕友汪輝祖在遇到解決不了的疑難案件時,就常到城隍廟焚香黔禱,祈求神助。清代城隍神司法職能的被強化更是登峰造極,見下列案例。[4]《庸閑齋筆記》載:順治年間,海上強盜侵擾縣府,清朝總兵官王憬督戰辱師,損兵折將。老百姓聚集一處,罵他無能。王憬聞言大怒,訴之當地姓周的巡撫,誣蔑民眾與海寇有勾結。周巡撫以為是真,準備等到夜間雞叫之后,派兵吏去屠殺那些百姓。這天傍晚,城隍神降至官署,站在階下,周巡撫恍惚若見。半夜時分,周還沒有放棄天亮之前屠戮百姓的打算,結果他又仿佛看見城隍神直視他,撞頭數次。這下子可把周嚇壞了,終于取消了屠戮百姓的決定。[9]P341
《信征錄》載:康熙二十二年,山西祁縣一個姓劉的人平常無惡不作,人們對他都恨得咬牙切齒。一天,他忽然自己跪到縣衙門,兩手自然反背,口稱奉縣城隍之命前來自首,求縣令派人把他押到府城隍廟去問罪。縣令以為他患了精神病,讓人把他從衙門驅逐出去。然而他轉而又來。沒有繩子捆綁他的雙手,但好幾個人都解不開他反背的雙手。如此數日,縣今只好差人送至府城隍廟。劉氏來到廟前,即跪在臺價下面,號呼痛苦,說城隍神在對他施刑。刑畢之后,他站起來又說城隍將他發回本縣,游街示眾。后來游街完畢之后,他便七竅流血而死尸。《果報類編》載:平湖進士張虎候的兒子,貪狡無賴。看到一戶鄰居家境富裕,便眼紅,想撈一把。他編造謊言,唆使這家和冤家打官司,而自己從中周旋料理,獲利百金,得意至極。七月初一,他赴城隍廟燒香,跪在城隍爺神像前,再也站不起來了,感到似乎有人猛擊其背,即刻吐血數升。抬到家里之后,他自述作惡之事,并說今日遭到城隍的誅譴。第二天他就一命嗚呼了。《新齊諧》載:福建莆田王監生,素來強橫鄉里。看到張妮的五畝田地與自家田地搭界,便偽造地契,賄賂縣令,斷為己有。張心中忿然,經常在王家門口斥罵。王監生讓人毆殺張妮,然后讓其子來看尸體,并當場將其子五花大綁,送往官府,誣告其子殺了母親,數人作證,屈打成招,擬判凌遲。總督蘇昌聞而疑之,乃下令讓福州、泉州兩知府會審于城隍廟。兩知府各有成見,仍照縣令所論定罪。其子受綁將出廟門,大叫:“城隍,城隍,我一家奇冤極枉,而你全無靈響,還有什么面孔享受人們的祭掃!”剛說完,廟的兩廂突然傾倒。知府、判官們以為是廟柱年久已朽,不甚介意。等到其子被牽出廟時,兩個泥塑皂隸 (城隍神的吏卒)忽然向前移動,兩根木棒擋住門,使人不能通過。觀者嘩然,兩知府亦驚然,趕快重新審理,判決“其子冤”,王監生依法處之。[10]175
上述四個案例中,有的是城隍為民伸冤而阻止官吏濫施誅罰,有的是城隍參與刑訊懲治惡人,有的是城隍神在陰間誅殺陽間惡人,有的是城隍督促司法官吏理冤申案的。這都說明了城隍司法審判職能的加強,更說明了鬼神迷信等觀念在古代司法活動中占有很大市場。以城隍神監察官吏、在城隍廟里審理案件,這在表面上與早期的神判有著很大的不同,但它仍是試圖利用人們畏懼鬼神的心理,從精神上摧垮不法之徒的防線,使其自行招供或露出異常,再按照世俗的法律加以制裁。因此,實質上還是天道鬼神觀念在司法審判制度上的貫徹與滲透。
二、司法審判理念層面
關于宗教文化對司法審判理念的影響,學界存在著不同的觀點。有學者認為,僅是普通民眾相信鬼神的存在,而中國傳統的士大夫階層是“敬鬼神而遠之”;即使司法官吏在具體的司法活動中運用了,那也僅是利用人們的迷信心理,為自己的需要服務。[2]P248筆者認為,這些觀點有以偏概全之嫌。實際上,絕大多數人還是相信鬼神的,很多司法官吏并不是裝神弄鬼,而是內心里真相信鬼神的存在。因此,在古代很多司法官吏的具體司法活動中,鬼神仍舊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對鬼神的敬畏態度始終貫穿在整個司法活動中,如斷案如神的北宋包拯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就利用人們對鬼神的敬畏裝神弄鬼地把犯罪嫌疑人的膽給下破了而盡吐實話,從而獲得斷案的證據;清代著名縣令藍鼎元在城隍廟中利用城隍的威嚴而破大案。長期以來,天道鬼神觀念潛在地左右著司法官的心理,影響著普通民眾的司法理念,這成為古代司法審判活動的文化根基。在中國,對傳統司法審判制度影響較大的兩個宗教是道教與佛教。
(一)道教的“善惡承負”觀
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對中華民族心理特質的形成、影響是其他宗教所不可及的。“道教是我國古代社會鬼神崇拜的延續和發展,……。”[11]道教把傳統的福孽報應觀念進一步發揚光大,把“天道承負、現世因果報應”理論定為其教義。“天道循環,善惡承負”②這一教義,原始道教已加載《太平經》。如《太平經》卷九十二中說:承負之責最劇,故使人死善惡不復分別也,大咎在此。又說:如此言,為善復何益邪?為惡何傷乎哉?力行善,復何功邪?豈不是抹煞善惡,不能勸善規過.揚善止惡了嗎?因而認為承負之說是反亂天道之辭,為天地所不喜悅,提出應以現世之善惡報應為教義。認為吉兇福禍乃是個人行為善惡的必然報應。《太平經》卷一百中說:善者自興,惡者自病,吉兇之事,皆出于身,以類相呼,不失其身。天道無私,但行之所致。卷一百一中說:善者自興,惡者自敗。觀此二象,思其利害。凡天下之事,各從其類,毛發之間,無有過差。認為上有日月照察,身中有心神與天音聲相聞,有諸神疏記人的善惡,過無大小,天皆知之,到了一定的時候,天便校其善惡,予以賞罰。《太平經》卷一百十二說:得善應善,善自相稱舉,得惡應惡,惡自相從。……務道求善,增年益壽,亦可長生。……天責人過,鬼神為使……罰惡賞善人所知,何不自改。天報有功,不與無德。《老子想爾注》中也說:道設生以賞善,設死以威惡,行善,道隨之。行惡,害隨之也。不能積善行,精氣自然與天不親,生死之際,天不知也,死便真死,屬地官去也。如能積善功,則精神與天通,設欲侵害者,天即救之。可以復生而長生仙壽。天上之神對善者則賜福、增壽,對惡者則降災、減壽,還要把他的鬼魂下入黃泉,打入地獄。
道教對中國民族心理的影響,可謂無所不至,無處不在,上至帝王將相,中至文人士大夫,下至庶民百姓,都受到了道教濡染,滲透入中國人思想的每一個角落,滲透入中華民族心理的巖層,成為中國民族心理的一種特質。道教影響大致分為三個方面:一是為上層統治集團提供精神支柱。③二是成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棲息地。④三是道教對于民間信仰有直接而深廣的影響。許多中國人雖然沒有加入道教,但對道教系統整理過的鬼神譜系卻是虔誠信奉的,而且不管是哪種神仙,都可以和諧地并存在一起信奉。在許多地方,釋迦牟尼、老子、孔子甚至其他各種天王、羅漢、牛頭馬面、關公財神都可以并排放在一起祭拜,甚至各行各業都有其保護神,對著神靈不能做虧心之事,這個傳統演化到司法文化中就叫“神道設教”。正是因道教具有這種廣泛的上層和下層社會基礎,鬼神信仰就成為中華法系習慣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報應觀念滲透到中國傳統的司法審判活動中也就不足為怪了。如在民間流傳極廣的《功過格》,本是道士發明、使用的,用以推進鬼神精神在民間的傳播。但當它不斷地與民眾生活相交匯的時候,其性質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濃厚的宗教色彩變淡,而適應民眾心理需要的倫理道德性增強。
(二)佛教的“因果輪回”說與地獄說
佛教傳入中國后,佛教的“業”、“業報”等抽象教義,中國普通百姓并不懂,但經過中國化改造后,佛教的“因果輪回說”與中國古代本土宗教文化中的這種“天道承負、善惡報應觀”的觀念結合起來,更是深入人心。人們認為死后有鬼神存在,除作惡多端者下十八層地獄之外,一般人都會重新轉世為人。但是如果那人是死于非命,并且其冤仇又未獲得昭雪,則會成為孤魂野鬼,冤仇未報之前無法投生,只會在大地上游蕩,有時會引起天地失衡,出現一些異常現象。“善惡報應”觀進一步融入到人們的思想觀念中,民間俗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就是這種觀念的典型寫照。人們在這一宗教觀念的影響下,形成了若被冤死,死者將會冤魂不散,不得超生,進而會對審理案件的官員進行尋仇的法律理念。⑤
(三)善惡報應觀潛在地左右著司法審判理念
道教“善惡承負觀”、“佛教的因果輪回說”與儒家的“天道福善淫禍”交融在一起而形成的善惡報應觀念深入到民俗信仰和士大夫的精神生活當中,并產生了廣泛的作用和深遠的影響。善惡報應的宗教信仰成為傳統法律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之一。在這種觀念影響下,司法官吏相信如果因其審判工作失誤,而誤殺無辜,會破壞和諧秩序,引起天譴。司法官吏為有善報、福延子孫,避免禍及后世,往往以救生為陰德,在司法審判上,往往對罪犯寬肴開脫,并以懷有陰德自許。北魏時的高允就常對人說:我在中書做官時曾積有陰德,濟救民命,如果陰報不差,我便可以長命百歲。[2]P167司法官吏因存在這種懼怕福孽相報的心理,一般都能謹慎辦案,尤其在辦理死刑案件時要比其他案件付出更多的謹慎,主張多做善事。所謂的善事是一個模糊概念,不殺生、不害人是最基本的要求,司法官吏判人刑罰,打人殺人,在傳統觀念上就是損陰德,不是現世折壽,就是來世報應,或者于仕途有累,或者對子孫不利。司法官吏認為寬恕罪犯是一種“善行”,多存活人命,就是為自己積累陰德,會有福報;而執法嚴苛、濫殺無辜是造孽行為,必有惡報。不僅司法官吏會得到報應,就是幫助司法官起草判詞的幕友也同樣得到報應。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里講:幕友雖沒有官的身份,卻暗中有官的權力,報應更為明顯。清代著名的幕友汪輝祖在他的《佐治藥言》中列舉了很多的事例來說明因果報應的必然性,反復強調說“求生”是“千古法家要訣”。這樣的文化傳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中國古代每個官吏在案件審理中的態度。這點可以從古代官員對于出任刑名相關職務時的態度上得以驗證。此方面最典行的代表就是清代著名的刑名幕友汪輝祖父子,他父親當年在作紹興師爺時猶豫萬分,最后還是怕“損德”而不敢作刑名幕友。汪輝祖年輕時立志作幕,其母親以家族三世單傳加以勸阻。后來汪輝祖得中進士,三個兒子都有功名,自以為就是佐官裁判時的積德報應。這種文化上的制約對于講求“實用理性”的中國古人來說,尤其在死刑適用上是具有相當約束力的。[12]汪輝祖在長達二十六年、歷經十六個州縣的作幕經歷中,只處理過六個死刑案件,自己認為積下陰德不少。
這種因果福報的觀念,雖然對促使司法官吏認真辦理案件、限制枉法濫刑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同時又成為封建司法官吏為罪犯開脫罪責、放縱罪犯的托詞,往往造成“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以幸免”的后果,對古代司法審判制度產生不良影響。
三、法律器物層面
中國傳統司法文化中的有些符號與儀式,真實再現了宗教文化對司法審判制度的侵蝕與風化。
(一)獬豸
從神判中走來的神獸“獬豸”。⑥由于能分辨是非,決訴訟,遂成了中國古代法官的代稱,如同龍象征著皇帝、鳳象征著皇后一樣,獬豸則象征著威嚴的法官,獬豸冠更成了法官的代名詞。雖然隨著歷史的發展,獬豸的形象在不斷地發生變化,如早期的獬豸似牛、羊、豬等家畜,到了中晚期則象虎、豹、獅等猛獸,但它無論怎樣變化,其頭頂上那支突出的并用來抵觸邪惡的銳角,卻仍然是它最大的特征。《后漢書·輿服志下》載:“獬豸,神羊,能辨別曲直,楚王嘗獲之,故以為冠。”因此至少從戰國以后,“獬豸”一直就是中國法律的象征。秦滅楚國后,秦王將該冠賜給御史佩戴,遂稱為“獬豸冠”。在漢代,專門主持糾察之職的御史所戴的帽子,也被稱為“獬豸冠”。如《后漢書·輿服志下》載:“法冠,執法者服之,……或謂之獬豸冠。”唐宋時期,凡是執法官員所戴的官帽都稱“獬豸冠”,號為“法冠”,象征著明察秋毫的獬豸神獸。唐代詩人岑參曾有“聞欲朝龍闕,應須拂豸冠”的描寫。至明代,以獬豸圖案飾執法官公服已十分多見。到了清代,御史及按察使的官服前后都繡有獬豸圖案。直到現代社會,習慣上仍然以獬豸的形象作為法律的象征。
(二)州縣衙門的布置及設施——折射出宗教文化的魅影
人類文化發展的歷史表明,任何試圖反作用于人的精神或意識,都必須有其物化的形式作為載體,如宗教的廟宇。衙門是司法文化最重要的符號之一,司法權正是在衙門中得到運行的。法庭及其設施的配置無不反映司法精神的必要的外化效果,反映了一種意識形態痕跡,使司法審判制度的內涵能為人所感知。雖然司法活動的神圣性沒像宗教那么純粹,然而司法活動場所及空間布置卻表露出“神明裁判”隱喻下的世俗遺留,衙門的建筑結構、衙門中的設施彰顯一定的文化氣息與內涵。
曾在清朝州縣衙門擔任過刑名幕友的陳天錫先生以湖南麻陽縣署為例,談及衙署的主要建筑及陳設:“署坐北朝南,大門前有一道照壁,畫一只四腳獸,其名諧音如‘貪’意思是警戒做官的不可貪婪。……。由轅門進來,正中是大門。大門有三個,一個正門和兩個側門,都是長方形兩扇,畫著門神。……,儀門之內是一個大天井,正中有一個牌坊,橫額寫著‘爾體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相傳是宋太宗所制的戒石銘,命令郡縣立石堂前以資警惕。也有人說是宋代黃庭堅做太守時所說的話,天下州縣都照此立坊。……,地板上鋪著蔑席,意思是坐這暖閣的主官辦事要憑良心,否則便要‘天誅地滅’,這是何等嚴厲的警惕。[13]作為司法場域的大堂 (這是州縣衙門最為重要的辦公地點)正中懸掛“明鏡高懸”的匾額,堂前有一楹聯: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負民即負國,何忍負之。這就是說,天意和人心,國家和百姓,都是縣官必須持正平衡的東西。
古代社會衙門的設置、布局基本上大同小異,但無論是畫的四角獸、門神,還是楹聯中的“天”字以及懸掛著的“明鏡高懸”的匾額,無不滲透著宗教文化的意蘊。門神系道教和民間共同信仰的司門之神,⑦舊時人們都將其神像貼于門上,用以驅邪避鬼,衛家宅,保平安,助功利,降吉祥等,是民間最受人們歡迎的保護神之一。道教因襲這種信仰,將門神納入神系,加以祀奉。《禮記·祭法》云:王為群姓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大夫立三祀,適士立二祀,皆有“門”、“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灶。”可見自先秦以來,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崇拜門神。門神因其張貼在古時司法活動的主要場所——衙門,因而也就具有新的文化意蘊。“鏡”在儒家思想中,并不具備神秘色彩,而僅僅限于映照物象的實用器物,是后來文人賦予其“殷鑒”、“戒鑒”之意;但道家則從莊子以降,就賦予“鏡”神秘化、咒術化,乃至視為神靈的思想。⑧尤其從唐代開始,“鏡”的文化涵義更為豐富,唐代道士曾根據教理教義設計出許多道教銅鏡,最著名的是天照、地照、人照三件道教大鏡。[14]佛教的經書《佛說十王經》所說的“業鏡”的功能主要是指在冥間罪人被定罪后,經常會心里不服,于是幽冥世界的審判主、諸鬼中的大王——閻羅王就會以“業鏡”讓他們各自觀看自己所造的罪業。伯 2003《佛說十王經》:破齋毀戒煞豬雞,業鏡照然報不虛;若造此經兼畫像,閻王判放罪消除。五七閻王息諍聲,罪人心恨未甘情;策發仰頭看業鏡,始知先世事分明。佛教“業鏡”遂成為陰間判官手中彰顯罪人罪惡的工具。鏡子成為法文化中具有高度象征意涵的一個器物。古代衙門上方懸掛著的“明鏡高懸”的匾額,就是把鏡子作為彰顯罪惡的工具,期待法官判案能像“明鏡”一樣的高懸,讓善惡清楚,無所盾形。類似這樣將“名鏡”轉化為法律用語,也出現在敦煌吐魯番出土的法制文書中,如《后周顯德五年 (958)押衙安員近等牒稿五件》有“伏乞令公鴻造,高懸志鏡,鑒照貧流”語;又《宋太宗雍熙二年(985)牒稿二件》有“伏望大王高懸惠鏡,照祭 (察)貧兒”語。⑧庶民已經期待司法官員能明鏡高懸,以明是非,申理冤屈。敦煌出土的《佛說十王經》出現在唐末五代,這里的兩件文書,時間在五代宋初,恐怕“明鏡高懸”的法律用語,也受到《佛說十王經》“業鏡”觀念的影響,[6]P329,與“業鏡”思想的傳播有關系,是冥府“業鏡”的世俗化。“業鏡”以其意像對后代法文化產生深刻影響,“鏡”成為法文化中具有高度象征意涵的一個器物,“明鏡高懸”成為高掛衙門的法寶,在朗朗乾坤中,使一切罪惡無所遁行。
四、結語
宗教文化對中國傳統司法審判制度的影響與滲透,宜從歷史的視角客觀地評價。
(一)宗教淪為輔助傳統司法審判制度實施的工具
中國傳統的司法審判制度要服務于實現法律的終極目的——穩定社會統治秩序,而不是實現法律本身。為了實現這個終極目的,當然就可以采用各鐘手段,包括宗教。在民間具有深厚影響的神鬼信仰就成為首選,宗教也就被司法所利用了。在原始宗教信仰時期,那時人的理性不發達,認識能力終究有限,在科技、取證技術都不發達的情況下,當無法判斷曲直又擔心枉縱罪犯,只能通過一些唯心的辦法來加以補充,用神靈來斷案,也不失為一個無耐的卻也庶幾可行的辦法。因此可以說,早期的“神判”制度其實就是古人用神靈無限的理性認識能力來彌補人類有限的理性能力在審判實踐中的一個反映。但隨著歷史的發展,宗教信仰與法律的關系就異化了,宗教信仰與司法審判制度互為表里,中國古代的統治者按照自己的意愿給司法審判制度披上了一層神秘的外衣,使宗教淪為統治者馭民的工具,“人惟神佑,神實人依”,直接地道出了人神的相互為用。例如,古代社會司法官吏借助城隍參與司法審判就說明,隨著城隍信仰的發展,城隍神格日趨重要后,世俗權力推波助瀾,充分利用民間信仰,城隍成為常住民間的陰間司法審判官。人們的宗教信仰淪為工具后,人們對法律的神圣性產生了懷疑,法律信仰被宗教信仰邊緣化了,我們的神道設教除了灌輸給蒼生黎民一點善惡觀和“舉頭三尺有神明”的畏懼感外,終究難以培養他們對于法律與程序的神圣感,這與西方宗教教義對法律的影響不可同日而語,西方國家的宗教信仰培養了西方人對法律神圣性的信仰。
(二)宗教文化對傳統司法審判理念的侵蝕
宗教文化對中國傳統審判制度的侵蝕,不只僅停留在制度層面上,更主要的是體現在思想層面上,對司法官員及普通民眾法律意識、法律觀念的影響。
在古代,官員們很忌諱被人稱為“酷吏”,為積陰德往往對罪人減輕處罰。《名公書判清明集》就記錄了大多數案件的處刑都要輕于法律的規定,官員們在判書往往以“姑且從輕發落”、“姑寄竹篦一頓”等語句,減輕判處的刑罰。《幕學舉要》(清)就說:“古今清官子孫或多不振”就是因為處事刻薄,有損陰德而得到的報應。[2]P232宗教信仰中的報應觀念,嚴重地侵蝕了司法官吏必須依法斷案的司法理念,這雖對于緩解法律的嚴酷性具有作用,但官員們對報應的畏懼超過了對法律的畏懼,司法與執法時斤斤于自己的“福孽之報”,對于法律公正與程序正義就是一種巨大的破壞,法律的權威性大打折扣。南宋的大儒朱熹對此持強烈的批評態度,他說:“現在的司法官員都被福報之說所迷惑,喜歡出人罪以求福報,該處死的改判流配,該流配的減為徒刑,該徒刑的減為杖刑,該判刑的減為笞刑。罪人免于處罰,就不能保護好人,實際上這樣做正好是在做惡事,難道還會有什么福報嗎?”
對于普通百姓來說,由于司法制度的黑暗以及官場的腐敗,激起了社會的不滿情緒,人們又無可奈何,只好借用鬼神的力量予以抨擊現實,以化解心中的怨氣與苦悶,反映出人們對司法公正的追求,明確司法責任的美好愿望和樸素心理。但普通百姓遵守法律的動力也往往源于這個福孽報應的觀念,這種觀念摧毀了人們對法的敬畏懼,腐蝕了人們的法律意識,成為人們對一些社會不公平現象的一種很好的解脫之法,反正冥冥之中的報應終歸會替人們實現公平。法律權威何以確立?
注釋:
① 朱元璋對城陛神的封號已做了最簡潔扼要的回答:“鑒國司民”(明初各級城煌神前面都要加上這四個字),用死鬼來治活人,這是中國封建統治者的一大發明。此句話參見張勇:《中國古代司法官責任制度及其法文化分析》,第 107頁,中國政法大學 2002年博士學位論文。
② 《太平經》卷卅九說:然,承者為前,負者為后,承者,乃謂先人本承天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積久,相聚為多,今后生人反無辜蒙其過謫,連傳被其災,故前為承,后為負也。負者,乃先人負于后生者也……。意思是說,前人有過失,由后人來承受其過責;前人有負于后人,后人是無辜受過,這叩承負。換句話說,即前人惹禍,后人遭殃;如果是善的話,則是前人種樹,后人遮蔭。正是因為有這種由天道所決定的承負,所以凡人之行,或有力行善反常得惡,或有力行惡反得善,使人從是常冤,蒙受無辜的苦難。
③ 統治者在取得統治地位之后,總想鞏固自己的統治,辦法之一就是神化自己的統治,使人們覺得皇權天授,不容質疑;另一方面,統治者總想安享榮華富貴,但生命短暫,轉瞬即逝,于是他們就想方設法使生命得以延長,甚至長生不死。這兩種思想取向,在道教中都可以得到滿足。于是,道教成了上層統治集團的精神支柱。唐高宗追封老子地建玄元皇帝廟,以先祖陪祀;妃嬪公主多信道教,受金仙玉真等封號 (如楊玉環等)。這些舉措,一方面是借道教神威鞏固皇權,另一方面是借以滿足個人的精神追求。唐憲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武宗以及一大批重臣名士,都是因為想長生不死,誤吃道士丹藥中毒而早死的。但百死而不悔,悲劇照樣繼續演下去。宋真宗另設一道教尊神趙元朗,作為趙宋的始祖,給皇室涂上神圣光彩。宋徽宗自稱教主道君皇帝,奉道極虔。明代諸帝以嘉靖佞道最甚,他長年潛居深宮,日事齋醮、煉丹和服食,得寵大臣須能寫青詞(禱告表文),道教成了嘉靖皇帝的主要精神慰藉。
④ 道教與其他宗教不同,其宗旨是追求長生不死,得道不死;看重個體生命的價值,相信經過一定的修煉,世間的個人可以脫胎換骨,直接尸解成仙,不必等到死后才靈魂超度;它注重的是現世的幸福,主張人要活得適意、灑脫,超塵脫俗,高雅飄逸。道教的這些思想向度,很迎合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需求,特別是當他們在現實生活中受到壓抑失意的時候,他們的靈魂便亟需一個道教這樣的棲息地,所以,很多文人士大夫都信奉道教。如王勃便“常學仙經,博涉道記”(《游山廟序》),常常嘆息“流俗非我鄉,何當釋塵昧”,夢見自己成了仙人(《忽夢游仙》);盧照鄰則“學道于東門山精舍”,還到處乞討銀兩和藥石來煉丹(《與洛陽名流朝士乞藥值書》);李白更是“清齋三千日,裂帛寫道經”(《游泰山》六首),連做夢都想著羽化飛升:“余嘗學道窮冥筌,夢中往往游仙山”(《下途歸石門舊居》);就連白居易,也曾煉鉛燒汞,學制金丹。為什么文人士大夫會對求道煉丹如此熱衷呢?這是因為,他們對塵世充滿眷念而又深感失望,在這種進退維谷之中,道教那種既能免除生老壽夭之苦,又能安享塵世之樂,既能滿足心中情欲,又能活得高雅脫俗的生活情趣彌漫開來,使他們的靈魂能夠得一些安適,所以他們皈依了道教。
⑤ 在我國流傳甚廣《聊齋志異》中很多鬼怪故事就可以說明報應觀念已經成為中國古代的一種重要的文化傳統。
⑥ 獬豸,又名獨角獸,是中國古代傳說中的一種似羊非羊、似牛非牛的神獸,具有能分辨是非、判斷正誤的特異功能。《說文》云:“獬豸,獸也,似山羊,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者。”《后漢書》載:“獬豸,神羊,能別曲直。”相傳,在原始社會末期,堯、舜時代的法官皋陶,最早開始用獬豸參加斷案。遇到難以解決的案件時,就將獬豸牽到當事者的面前,獬豸用角抵觸的一方就是有罪者。
⑦ 門神二字最早見于《禮記·喪服大記》。鄭玄注:“釋菜,禮門神也。”就是說在唐之前已有敬門神之俗,桃符上有神像以驅邪之俗也早在唐代以前就形成了。但經過唐代,門神的內容和形式有了豐富和完善。到五代,桃符內容有了新的變化,向春聯演變,門神方獲得獨立地位。宋代,除夕之夜宮中仍有扮門神驅鬼的習俗,而在民間則懸掛門神像。百歲寓翁《楓窗小牘·下》云:“靖康以前,汴中家戶,門神多番樣,戴頭盔;而王公之門,至以渾金飾之。”《東京夢華錄》也載:“近歲節,市井皆印賣門神、鐘馗、桃板、桃符。”足見宋代春節懸掛門神之盛。
⑧ 有關道家對于“鏡”所賦予的神秘思想,參看福永光司《道教的鏡與劍》,收入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 7卷“宗教思想”,中華書局 1993年版,第 386-445頁。
[1] [漢]王充.論衡·是應篇[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2] 郭建.獬豸的投影——中國的法文化[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出版,2006.
[3] 圖 3[J].考古,1973,2.
[4] 圖 8[J].考古,1973,2.
[5] 圖 9[J].考古,1973,2.
[6] 陳登武.唐代的法制、社會與國家——從人世間到幽冥界[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7] 張勇.中國古代司法官責任制度及其法文化分析[D].中國政法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2.
[8] 大明會典卷八十二[M].北京:中華書局,1996.
[9] [清]陳其之.庸閑齋筆記卷二[M].北京:中華書局,1989.
[10] 郝鐵川.中華法系研究[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
[11] 李養正.談談道教的幾點特征,道教與傳統文化[M].北京:中華書局,1997.
[12] 胡興東,劉婷婷.中國古代死刑適用機制[J].云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06,3.
[13] 張偉仁.清朝地方司法——陳天錫先生訪問記[J].食貨月刊,6.
[14] 王育成.唐代道教鏡實物研究[J].唐研究,2000,6.
Restriction and Influence on Chinese Traditional Judicial Trial System of Religion Culture
Zhang M ing-m in
(The People’s Congress of Shandong Province of the Committee for Internal and JudicialAffairs, Jinan Shandong 250011)
Itwas unquestioned that the religion culture restricted and influenced on chinese tradtional judicial trial system.Religion had little influence on Chinese traditional trial system,but in fact it had deep issue with traditional trial system.The influence of the religion culture on judicial trial system embodied from the side of system,judicial ideology and legal tools.
the religion culture;tradition;judicial trial system
詞】DF08
A
(責任編輯:唐艷秋)
1002—6274(2010)03—100—08
張明敏(1972-),女,山東濰坊人,歷史學博士,山東省人民代表大會內務司法委員會公務員,研究方向為立法學、法律思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