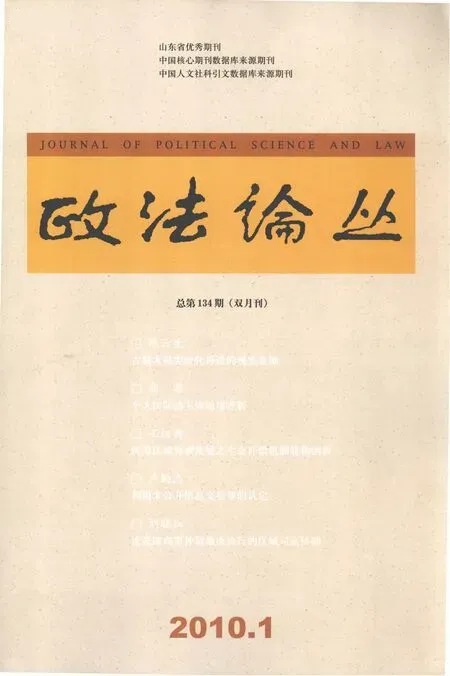國際投資仲裁中的人權保護
李鳳琴
(華東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上海200042)
國際投資仲裁已經成為解決投資者與國家之間投資爭端的最有效方式。當前越來越多的B ITs通過允許外國投資者單方面訴諸國際仲裁機制而給予外國投資者高水平的具有強制力的保護標準,[1]這就為投資者利用國際仲裁挑戰東道國更廣泛的經濟管理政策和措施提供可能,同時,這些新出現的投資者與國家間的仲裁也帶來了一些意料之外且比較敏感的問題。除了環境保護和與公共健康有關的問題外,國際人權保護是國際投資仲裁必須面對的新問題。
一、國際投資對人權的影響
國際投資法和國際人權法在其發展過程中基本上處于一種彼此獨立的狀態。然而隨著投資領域范圍的擴大,有關投資規則已經越來越多地影響到人權的享有,因此,一些學者開始認識到兩者之間的聯系。
(一)國際投資對人權的積極影響
國際投資對人權的影響是廣泛的。投資可以增加貿易規模、加快經濟增長和推動社會發展,表明投資和人權的享有存在潛在的聯系,尤其是投資與人權中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以及發展權聯系更加密切。最直接的體現是投資對就業帶來的好處。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指出,國際投資在以出口型勞動密集型產業、初級制造業和服務業方面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有證據顯示在過去的20年里國際投資的增加在推動婦女參與有償勞動方面產生了積極影響。就業機會的增多可以推動新技術的出現和帶動人力資源的培訓,同時使收入分配更趨合理。這樣通過賦予人們應有的權利和創造一個更加平等的社會,使他們更好地享有人權。特別是對于婦女來說,有機會參與有償勞動,即使收入不多,也能使她們無論在家里還是在社會上贏得更大的自主權,并且迫使社會對婦女的平等權給予更多地承認。而且,東道國為吸引外資,通過改善國內教育體制,提高教育水平,從而使更多的人享有受教育的權利。[2]P182
總之,外資的增加可以加速東道國經濟的發展,進而提高當地的人權保護水平;而當東道國居民的諸多人權,特別是受教育權、勞動權和公共健康權等受到較好保護時,企業的工作效率將會提高,利潤增加,這樣外國投資者就有可能將人權保護作為一種商業策略來對待。
(二)國際投資對人權的消極影響
然而,很多學者普遍認為,目前的國際投資已經對促進和保障人權帶來不利影響。[3]在《關于侵犯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馬斯特赫里特指南》中注意到這樣一種傾向,即世界各地往往為吸引跨國公司的投資或應對由國際國內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所引發的情況而削減政府的作用,依靠市場力量來解決人們的福利問題。這樣一來,政府負有的尊重、保護和實現人權的責任就包括確保私人企業和個人,以及由政府管理的跨國公司不剝奪公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義務。[4]然而,東道國在吸引外資過程中,通過B ITs賦予外國投資者較大的權利時卻很少要求其承擔義務,而由于外國投資者并不是國際人權法中的義務主體,因此,外國投資者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同時,往往以侵犯國際人權的方式作為實現其投資目標的手段。東道國為履行保護人權的國際義務,本應對外國投資者侵犯人權的行為加以干涉,然而由于外國投資者特別是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力量巨大,以至于東道國既無資源也無意愿進行控制,還有一些國家走得更遠,它們甚至與企業一起聯手侵犯人權。[5]P99
而當一些東道國試圖規制和管理本國經濟(其中包括對外國投資者的管理),以期實現促進或保障人權目的時,投資條約中爭端解決條款的設立卻為投資者通過國際仲裁挑戰東道國人權激勵措施打開了方便之門。在由投資者提起的投資仲裁中,東道國往往面臨投資者的巨額索賠,這就不可避免地影響東道國履行國際人權義務的能力。
那么,在投資仲裁中,仲裁庭是否享有對人權問題的管轄權,國際人權規則究竟會給投資仲裁中的實體規則和程序規則帶來哪些影響?東道國是否可以其承擔的國際人權義務來對抗投資者的訴求,對于上述問題,由于仲裁程序的保密性,目前尚無法全面了解投資仲裁庭對此類問題已經做出過的明確表述,理論界對此看法不一,因此,有必要對此類問題作進一步的探討。
二、投資仲裁庭對人權爭端的管轄權問題
在國際投資仲裁中,仲裁庭的管轄權一般來源于投資條約和投資合同的規定,投資仲裁庭是否可以對人權問題行使管轄權,關鍵在于投資條約或投資合同中爭端解決條款的規定。在很多投資條約中,只是將仲裁庭的管轄權限于“投資爭端”,或者是“侵犯本條約所規定的實體權利而引起的爭端”。比如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第1116條爭端解決條款中規定,仲裁庭的管轄范圍限于“違反第11章A節所規定的實體義務而引起的爭端”,在《能源憲章條約》(ECT)中規定只有“違反第三部分的實體義務”才具有可仲裁性。類似的規定還出現在法國、德國、英國、美國等的B ITs范本中。但問題是,這些投資條約一般并不規定人權義務條款,因此,仲裁庭對于“純粹違反人權義務的爭端”是無法取得管轄權的。[6]然而,某些違反人權的行為可能與投資有關,從而可被視為“投資爭端”而由仲裁庭取得管轄權,比如與保護投資者財產有關的侵犯人權行為可能違反了條約義務,從而列入仲裁庭的管轄權范圍。
在Biloune v.Ghana Investments Centre案中,申訴人Biloune針對被申訴人加納政府向仲裁庭提出三項請求:征收補償、為拒絕司法和違反人權承擔責任。Biloune認為加納政府對他進行逮捕并連續關押了13天后,并沒有對他提出任何指控而將他驅逐出境,已經干涉到了他的投資和其他活動從而構成征收,應當補償,同時加納政府應當對其承擔侵犯人權的責任。而被申訴人加納政府認為,Biloune的被捕和被驅逐出境并不是由投資而引起,因而仲裁庭對于違反人權之訴缺乏管轄權。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UNCITRAL)仲裁庭基于投資者與東道國間的協議第15條之二的爭端解決條款“任何由投資者與政府之間引起的投資爭端可交付仲裁”來解釋自己的管轄權。仲裁庭認為,因武斷拘押和驅逐出境而侵犯了Biloune的財產權和合同權利,Biloune因此而要求賠償的請求仲裁庭有權管轄。而仲裁庭認為,雖然國際法賦予個人以基本人權,如財產權、人身自由權等,但這并不意味著仲裁庭對每一違背最低國際待遇標準或違反人權的行為享有管轄權。仲裁庭由此得出結論:“仲裁庭的管轄權只限于由投資合同引起的商事爭議,鑒于政府只同意將與外國投資有關的爭端交付仲裁,就本案而言,雖然被指控違反國際人權義務的行為可能與仲裁中的投資爭端有關,但是,仲裁庭就純粹違反人權之訴是無管轄權的。”①
從以上案例可以看出,仲裁庭明顯繞開了純屬人權問題的爭議。應當承認的是,仲裁庭避免在此類敏感問題上發表意見也許是正確的,仲裁庭只存在有限的管轄權,不能代替其他司法機構對人權問題做出裁判。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仲裁庭并沒有完全拒絕或以某種方式貶損關于人權的主張。相反,仲裁庭明確承認東道國不應當違背最基本的人權。[3]
三、人權規則在國際投資仲裁中的適用
要了解人權規則在投資仲裁中的適用,首先必須解決人權規則是否可以作為解決投資爭端時可適用的法律。許多B ITs中的爭端解決條款明確規定了解決爭端應當適用的法律,一般包括投資協定、東道國法律和可適用的國際法。比如中國與芬蘭的B IT第9條規定:“仲裁庭可以根據本協定的規定,爭議締約一方的法律(包括其沖突法規則)和可適用于締約雙方的國際法規則做出裁決。”2004年美國B IT范本規定:“仲裁庭可以根據本協定和可適用的國際法規則進行裁決。”在NAFTA和ECT的爭端解決條款中也有類似規定。I CS ID公約第42條規定:“法庭應當依照雙方可能同意的法律規則判定一項爭議,如無此協議,法庭應當適用爭議一方締約國的法律(包括其沖突法規則),以及可能適用的國際法規則”。
應當指出的是,雖然許多B ITs和ICS ID公約等都規定了國際法可以作為解決投資爭端可適用的法律,但它們都未對國際法一詞下定義,這就留下了一個解釋問題。對此,世界銀行關于ICS ID公約的《執行董事會報告》中解釋到,“國際法”一詞應理解為《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第1款所包含的意義。②這樣,這里的國際法應當包括國際條約、國際慣例、各國所公認的一般法律原則、司法判例和權威學說等。因此,人權規則作為國際法的一部分就可以成為解決投資爭端可適用的法律。
(一)人權規則在界定“征收”時的適用
在投資者針對東道國提出的征收賠償案件中,仲裁庭經常會利用人權規則來解釋東道國的措施或行為是否造成對投資者私人財產的征收。在UNCITRAL仲裁庭關于Lauder v.Czech Republic案中提到:“B ITs沒有對征收和國有化做出明確定義,也沒有明確其他強制性剝奪財產的措施。”因此,仲裁庭援引了一些學者觀點和歐洲人權法院在Mellacher and Others v.Austria案中針對不同征收類型而對征收所作的定義:“一項‘形式’上的征收是旨在轉移財產的措施,而一項‘事實’上的征收是指一國剝奪了財產所有人對財產的使用權、租賃權或轉讓權。”仲裁庭認為,“被申訴人并沒有采取任何措施或采取其他相當于征收的措施,因為捷克共和國并沒有直接或間接干預Lauder的財產權或其財產利益。申訴人沒有提出足夠證據證明捷克共和國采取的措施或行為將影響到其財產權或剝奪其使用財產的權利,甚至是干預了其財產權。”③
另一個采用人權規則來對征收進行界定的是I CS ID仲裁庭所裁決的Tecmed,S.A.v.United Mexican States案。在該案中,投資仲裁庭首先援引美洲人權法院在Ivcher Bronstein案中關于征收的解釋:“在界定某種征收是否發生時,不能只限于從形式上判斷對財產的剝奪和限制,而應該透過形式,從實質上來判斷一項措施或行為是否已經構成對財產的征收。”④
其次,仲裁庭還借鑒了歐洲人權法院關于間接征收的相稱性判斷標準,即要求一國所采取的措施不僅符合公共利益,而且要在維護公共利益和保護個人基本權利之間維持一種公正的平衡。[7]P98仲裁庭認為,墨西哥政府的決定雖然是合法的,但其造成的后果與政府目標并不相稱,不合理地剝奪了投資者的經濟權利與合理預期,構成間接的事實上的征收。⑤
值得注意的是,歐洲人權法院關于間接征收的理論和實踐已經成為國際投資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的許多理念和方法對其他的國際投資法制(如NAFTA、B ITs等)已經或將會產生重要影響,[7]P102而且,越來越多的投資仲裁庭也已開始援引歐洲人權法院的間接征收理論來做出裁決。
(二)人權規則在確定征收補償額時的適用
從現行的國際投資法律與實踐來看,對于間接征收的補償,普遍采取的是一種“要么全有,要么全無”的做法。具言之,如果沒有將東道國政府的管理措施認定為間接征收,就無需向外國投資者承擔任何補償責任;反之,一旦將東道國政府的管理措施認定為間接征收,則無論情形如何,均需按照“充分、及時、有效”標準,向外國投資者支付全部或充分的損害賠償,從而置東道國于不利的地位。[8]P38有些學者擔憂,對東道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課以繁重的賠償責任可能使這些國家無法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國內人權的實現。[9]
因此,如果一國為保障國內人權而采取的措施或行為構成對外資的征收時,仲裁庭在確定征收補償標準時就應當考慮東道國的國際人權義務。因為,既然投資條約沒有規定強制性的全部賠償義務,那么就為仲裁庭在確定征收補償標準時適當考慮東道國的人權義務留有余地。而且既然在間接征收的認定上,仲裁庭可以運用歐洲人權法院的“比例原則”來平衡東道國與外國投資者之間的利益,另外,《歐洲人權公約》第一議定書第1條第2款也不是保證被間接征收者在所有的情形下都能得到全部補償,那么,仲裁庭就同樣可將“比例原則”用以確定間接征收之補償額的大小。具言之,在外國投資財產遭受同等損失的前提下,東道國政府行為的“適當性”和“必要性”如何、外國投資者合理期待受損的程度、東道國所要實現的社會公共利益有多大等因素,均將影響補償額的確定。[9]
雖然目前尚無案例明確表明投資仲裁庭在確定一國征收補償標準時考慮到了東道國所應承擔的人權義務,但是,至少在I CS ID的一個供水私有化爭端案中,非當事方提請仲裁庭注意賠償標準將會給玻利維亞所造成的經濟影響,他們認為幾百萬美元的索賠要求也可能破壞政府在保障公民享有最基本權利上的努力。⑥事實上,非當事方已經明確采用“權利”字眼來表達自己的主張,然而卻沒有援引國內或國際人權標準來進一步強調他們的主張。
(三)人權規則與投資仲裁中的法庭之友
法庭之友通常指非案件當事方對法院或仲裁庭存有疑問的事實或法律問題通過提交書面報告或參加庭審的方式善意地提請法院或仲裁庭注意的人。[10]在國際投資仲裁中,如果投資者與東道國都避開人權保護問題,那么非當事方可能援引人權規則要求參與仲裁程序,此時,仲裁庭在決定是否接受“法庭之友”摘要(Amicus Curiae briefs)時就可能需要考慮相應的人權規則。[9]
非當事方要求參與仲裁程序,既可能援引程序性人權,也可能援引實體性人權。援引程序性人權可以基于《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或者《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中第14條規定的“公平審判權”。
在Aguas del Tunari v.Bolivia案中,非當事方根據國際人權規則主張其有權參與仲裁,并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第14條的規定要求向仲裁庭提交“法庭之友”摘要。⑦但是,仲裁庭拒絕了他們的請求,認為“非當事方的請求超出了仲裁庭的權力。”仲裁庭強調,“仲裁庭的權力來源于當事雙方的授權,既然投資條約沒有規定,而且雙方當事人也沒有同意非當事方參與仲裁,因此,仲裁庭沒有權力允許非當事方參與仲裁,也不能為其提供聽審的機會。”[11]
在United Parcel Service ofAmerica Inc.v.Canada案(UPS案)中,加拿大郵政工人聯盟和加拿大人聯合會援引《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第14條規定的“公平審判權”、第26條規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世界人權宣言》的相關規定,向ICS ID仲裁庭申請作為當事方或作為法庭之友加入仲裁程序。仲裁庭認為:“我們并不認為一般國際法規則可以支持申請者的主張。我們必須承認,國際法律與實踐和相關國內法律與實踐要么忽視第三方的權利,要么只給予其極低的待遇。申請者所援引的,最接近本案可以適用的人權規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第14條,它涉及的是正在接受審判的人的權利和義務。本案并非如此,申請方的權利和義務與本案無關”,最終仲裁庭拒絕了法庭之友的申請。⑧
其實,公正審判權能否有助于非當事方參與仲裁程序是存在疑問的。正如上述UPS案仲裁庭所認定的那樣,人權法設立公平審判權的目的在于保障接受審判的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其只關注作為當事人一方的人權,而并不涉及非當事方是否也可以公平地參與訴訟或仲裁程序。[6]因此,在涉及“法庭之友”的更多仲裁案件中,非當事方還是援引實體性人權來支持自己的主張。
在ICS ID仲裁庭審理的供水私有化爭端Aguas Argentinas v.Argentine Republic案(Aguas案)中,五個非政府組織共同向仲裁庭提出請求要求參與仲裁程序,它們認為,仲裁裁決關系到公眾是否可以獲得足夠和平等的水資源問題,它關系著人的基本權利。⑨仲裁庭認為,以往接受法庭之友摘要的案件一般都涉及公共利益問題,這些案件的裁決對個人所產生的潛在、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甚至超過對案件當事人的即刻影響。仲裁庭援引以往的案件并做出結論:“本案爭端涉及布宜諾斯艾利斯及周邊地區大范圍的供水和污水處理問題,涉及公共利益,供水和污水處理系統為百萬居民提供最基礎的公共服務,可能會引起復雜的國際法問題,甚至包括人權問題。”因此,仲裁庭允許接受由五個非政府組織共同提交的法庭之友摘要,因為他們被視為受人尊敬的,在人權事務和公共服務方面具有充分的專業水平和經驗。⑩
在另一個涉及供水私有化爭端的案件,Biwater Guaff v.Tanzania中,仲裁庭認可了上述Aguas案仲裁庭關于接受法庭之友摘要的觀點,并且強調“仲裁程序并不只限于解決商事糾紛或私人沖突,而是可以對人們享受基本人權的能力帶來實質性影響。”?最終仲裁庭接受了法庭之友的請求。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非當事方可能援引人權規則要求參與仲裁程序,但是仲裁庭允許接受法庭之友摘要的理由一般是基于增加仲裁程序的透明度和對公共利益的考慮,而較少是出于對人權問題的考慮。而且隨著2006年《ICS ID仲裁規則》的修訂,至少已經消除了ICS ID仲裁庭對于能否接受法庭之友摘要方面的疑慮,該規則允許仲裁庭在與當事方協商后,可以接受非當事方向其提交的與爭端有關的書面建議。[6]
四、仲裁庭如何處理東道國人權義務與投資條約義務之間的沖突
根據國際人權法的要求,一國負有尊重、保護和實現人權的義務。承擔國際人權義務要求國家不僅僅只是避免干涉公民的人權,還要求國家采取措施確保私人企業和個人,以及由政府管理的跨國公司不剝奪公民的人權。這就要求國家有積極義務去規制和管理本國經濟,其中包括對外國投資者投資的管理,以實現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承諾。
然而,當東道國通過簽訂B ITs的方式從而對外國投資者承擔投資條約義務時,就為外國投資者通過投資仲裁挑戰東道國的經濟管理措施提供了可能,同時東道國可能會援引國際人權義務來抗辯投資者的主張。但問題是,不論一項條約涉及的是人權義務還是投資義務,“約定必須遵守”原則同樣適用,[12]那么,仲裁庭在裁決投資爭端過程中,是否應當優先考慮東道國所應承擔的國際人權義務?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
在國際法領域,《維也納條約法》應當是為人權的優先性提供支持的主要法律依據。《維也納條約法》第53條規定,“條約在締結時與一般國際強制規律抵觸者無效。”因此,當國際法作為投資爭端解決可適用法律的一部分時,如果存在強制性的國際人權規則,那么仲裁庭無疑應當優先適用。
目前,關于強制性的國際人權規則究竟包括哪些內容在學界尚無統一說法,根據《維也納條約法》的規定,國際法強制規則必須滿足國際社會全體接受的前提。一般認為,構成國際強行法一部分的人權規則主要存在于國際習慣法中,包括:1、生命權(包括免受任意屠殺的權利和免受種族滅絕的權利);2、免受種族隔離的權利;3、免受酷刑和其他有辱人格待遇的權利;4、免為奴隸的權利;5、免受奴役或強迫勞動的權利;6、婦女和兒童免受販運的權利。[13]因此,當投資者違反這些受強行法保護的人權時,其所依據國際投資條約而獲得的投資權利將無法得到仲裁庭的支持。即使投資仲裁庭無視這些強制性人權規則的存在而做出裁決,國內法院在承認和執行仲裁裁決過程中,也會考慮這部分強制性人權規則,最終可能以違反公共政策為由拒絕予以承認和執行。
然而,與投資有關的人權主要是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人權,鑒于國家在履行和促進經濟、社會權利方面的廣泛分歧,證明這些人權規則的國際接受性并不容易,《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二條之一只是要求“成員國承允盡其資源能力所及,各自并借國際協助與合作,采取種種步驟,務期以適當方法,尤其包括通過立法措施,逐漸使公約所確認之各項權利完全實現。”因此,經濟、社會和文化權一般屬于非強制性人權規則中的人權。投資仲裁中東道國一般也是援引這部分非強制性人權規則來對抗投資者的主張。
在Azurix Corp.v.Argentine Republic案(Azurix案)中,阿根廷政府提出其與美國簽訂的B IT和保護消費者權利的人權條約相沖突,并且在一份由阿根廷Solomoni博士提交的專家意見中指出,當B IT與人權條約相沖突時,應當優先適用人權條約的規定,因為消費者的公共利益必須優先于服務提供商的私人利益。而申訴人主張,用戶(消費者)的權利得到了特許協議的充分保護,阿根廷政府并沒有證明在特許協議終止后用戶權利所受到的影響。?仲裁庭認為,“阿根廷并沒有對其提出的問題進行充分的爭辯,仲裁庭無法了解B IT的規定究竟與消費者的人權存在哪些具體沖突,而且在發出終止特許協議通知后的5個月,申訴人Azurix還是不間斷地向用戶提供了服務。”?
在另一個CMS Gas Transmission Co.v.Argentine Republic案中,阿根廷提出了與Azurix案相同的主張。阿根廷認為,雖然國際條約的效力要高于一般法律,但是條約卻不能凌駕于阿根廷憲法之上,它必須與憲法規定一致。只有那些已經被阿根廷1994年憲法修正案承認的基礎性人權條約才取得與憲法同等的地位,因而,這些條約效力也就高于一般性條約,比如投資條約等。阿根廷進一步主張,當國內的經濟和社會危機已經影響到該國所保護的人權時,投資條約將不能優先適用,因為這將違反憲法所承認的人權。?
但是仲裁庭最終還是要求阿根廷承擔其B IT義務,仲裁庭認為,“在本案中,仲裁庭并沒有發現條約義務與人權義務存在沖突。因為,第一,憲法保護財產權,正如人權條約規定的那樣,第二,就雙方所涉及的爭議并沒有影響到基本人權。”?
從以上兩個案件我們可以看出,雖然東道國試圖援引人權義務來對抗投資者的主張,但是仲裁庭其實避開了人權義務與投資條約義務存在的沖突,因此,也就無法為我們提供一個如何解決投資仲裁中兩種條約義務相沖突的具體實踐。然而,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仲裁庭通常適用國際法解釋投資條約中的權利,那么仲裁庭也就應當考慮適用東道國已經加入的國際條約中的人權義務,以調和東道國相互沖突的國際義務,而不只是允許投資規則去任意踐踏人權規則。
五、余論
近些年來,雙邊投資協定數量迅猛增長,東道國特別是一些發展中國家希望通過簽訂B ITs的方式,給予外國投資者以高標準保護,從而達到吸引更多外資,促進本國經濟發展的目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2003年全球經濟展望》中,世界銀行根據客觀事實指出:“即使B ITs中相對強有力的保護措施,看來也沒有增加向簽署協定的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流動。”[14]由此看來,給予外資高標準待遇的基本理由沒能經受住實踐的考驗,因此,發展中國家在今后簽訂B ITs的談判中,應當重新考慮自己的談判立場,不能盲目地提高投資者待遇,應當為自己保留足夠的政策空間。
以往的B ITs一般只是單方面地給予投資者以權利,而往往忽視投資者對東道國承擔的義務,導致東道國無法有效援引自己更廣泛的國際義務來抗辯投資者的主張,而投資者卻有時威脅采用B ITs來挑戰東道國的人權保障措施。因此,有必要在B ITs中重新考慮投資者的責任,至少要求投資者尊重國內和國際基本人權作為其享受投資權利的前提。這對于當前國際社會還沒有有效機制追究跨國公司人權責任的情況下顯得尤為重要。這種規定也可以確保仲裁庭在面對投資者針對東道國的訴求時,去適當考慮投資者的人權責任。
然而,必須強調的是,本文中的任何建議并不意味著投資仲裁庭將取代已經建立的國際司法體制在裁決人權問題方面的職能。投資仲裁庭本身沒有實施國際人權標準的能力,它只能裁決投資爭端,只是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使投資者權利與最低限度的人權責任保持一致。
注釋:
① Antoine Biloune(Syria)andMarine Drive ComplexLtd.v.Ghana Investments Centre and the Government of Ghana,95 I.L.R.183(UNCITRAL 1989).p.203.
② Report of theWorld Bank Executive Directors on the Convention,ICS ID/2,p.13.
③ Lauder v.the Czech Republic,2001 WL 34786000,UNCITRAL FinalAward,Sept.3,2001,para.200-201.
④ TécnicasMedioambientales Tecmed,S.A.v.UnitedMexican States,I CS ID Case No.ARB(AF)/00/2,29 May 2003,para.116.
⑤ Id.,para.122.
⑥ Aguas del Tunari,S.A.v.Republic ofBolivia,ICS ID Case No.ARB/02/3,NGO Petition to Participate asAmicus Curiae,29 August 2002.
⑦ Id.,para.47-48.
⑧ United Parcel Service ofAmerica Inc.v.Canada,Decision of the Tribunalon Petitions for Intervention and Participation asAmiciCuriae,17 October 2001.at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6033.pdf,Mar.21,2009.
⑨ AguasArgentinas,S.A.v.Argentine Republic,ICS ID Case No.ARB/03/19,Order in Response to a Petition for Transparency and Participation asAmicus Curiae,19 May 2005,para.18.
⑩ Id.,para.25,27.
? Biwater GuaffLtd V.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ICS ID Case No.ARB/05/22,Petition forAmicus Curiae Status,27 November 2006,p.8.
? Azurix Corp.v.Argentine Republic,ICS ID Case No.ARB/01/12,June 23,2006,para.254.
? Id.,para.261.
? CMS Gas Transmission Co.v.Argentine Republic,ICS ID Case No.ARB/01/8,Apr.25,2005,para.114.
? Id.,para.121.
[1] 曾華群.變革期雙邊投資條約實踐述評[A].國際經濟法學刊(第14卷)[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2] 李先波等.主權、人權、國際組織[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3] JamesD.Fry.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Law in InvestmentArbitration:Evidence of InternationalLaw’sUnity[J].Duke Journal of Comparative&InternationalLaw,Vol.18,2007.
[4]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國際人權機構手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J].專業培訓叢刊,2004,12.
[5] 宋永新,夏桂英.跨國公司的國際人權責任[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6.
[6] Clara Reiner,Christoph Schreuer.Human Right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EB/OL],at http://www.univie.ac.at/intlaw/h_rights_int_invest_arbitr.pdf,Mar.14,2009.
[7] 李尊然.〈歐洲人權公約〉體制下的“管轄權征收”述評[A].國際經濟法學刊(第14卷)[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8] 徐崇利.利益與平衡與對外資間接征收的認定及補償[J].環球法律評論,2008,6.
[9] Luke Eric Peterson and Kevin R.Gray.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in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and in Investment TreatyArbitration[EB/OL].http://www.univie.ac.at/intlaw/h_rights_int_invest_arbitr.pdf.Mar.4,2009.
[10] 趙海峰,高立忠.論國際司法程序中的法庭之友制度[J].比較法研究,2007,3.
[11] Aguas del Tunari.S.A.v.Republic ofBolivia,ICS ID Case No.ARB/02/3,Letter From President Of Tribunal Responding To Petition,29 January 2003[EB/OL],http://ita.law.uvic.ca/documents/Aguas-BoliviaResponse.pdf.,lMar.19,2009.
[12] W illiam Schreiber.Realizing the Right toWater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Law:An interdisciplinaryApproach to BitObligations[J].Natural Resources Journal,Vol.48,2008.
[13] 白桂梅.國際強行法保護的人權[J].政法論壇,2004,2.
[14] 陳安.中外雙邊投資協定中的四大“安全閥”不宜貿然拆除[A].國際經濟法學刊(第13卷)[C].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