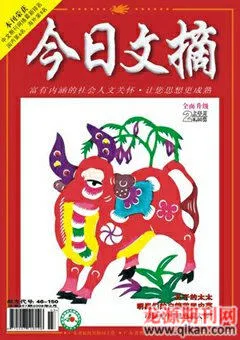歐洲最大精子庫生意興隆
她們等啊等,但仍沒有懷孕的消息。或者對她們來說,有個孩子比丈夫更重要。因此,她們找到Cryos,位于丹麥奧胡斯的世界最大的精子庫之一,并在網上預定年輕男性留在小瓶內的精子。
一個夢
這里是歐洲最大的精子庫,它由20人的團隊組成。他們負責搖晃、冷凍精子并把它們從奧胡斯送往世界各地。他們有250名定期捐獻者。自從1991年精子庫成立以來成功懷孕的已有1.2萬人次,精子送住的國家超過60個。負責人奧勒·紹說:“我們很有可能是世界三大精子庫之一。”另外兩家大規模精子庫位于美國,但他們的捐獻者并不是很樂意捐獻,而且在身高和發色上也不是很可靠。
一切都源自24年前還是經濟系大學生的紹的一個夢想。Cryos源自希臘文,是冰的意思。眼下除了奧胡斯的總部之外它在歐登塞、哥本哈根都有分部,奧爾堡的分部很快也將開張。此外,Cryos在紐約和孟買還有辦事處,生意很好。營業額在200萬歐元左右,盈利增長每年在10%到20%之間。診所、患者和懷孕人數都在增多。
精子越濃縮價格越高。根據濃度的不同,價格從30歐元到1000歐元不等。同時,捐贈者越容易接受新事物,價格也越高。因此女顧客可以在“坦率的”和匿名的捐贈者之間選擇。“坦率的”捐贈者會把名字留給孩子,匿名的則不會。而某些捐贈者人們只知道他的種族、體重、身高、教育程度、血型、頭發和眼睛的顏色,另外一些則還會了解他偏好的食物或者是喜歡的動物、休假地點和興趣愛好等等。多付15歐元,女顧客可以得到候選人嬰兒時期的照片和他的手寫字跡。花5萬歐元她就可以“獨享”他——再也沒有其他人能獲得他的精子。
顧客群
雖然官方機構試圖為基因買賣設定界限——但規定存在國與國的差別。例如,希臘、比利時和挪威允許匿名捐贈。瑞典、奧地利和瑞士則只允許“坦率的”捐贈。某些國家只允許異性夫婦使用精子庫,而另外一些國家則允許單身者使用。奧勒·紹說:“精子就像水,它尋找著自己的道路。沒有什么法律條款能阻止它。法律中一再出現漏洞。例如在我們這里,醫生不允許給病人使用‘坦率的’捐獻精子,但助產士有權這么做。”夫婦們大多只想要一樣:精子。捐獻者應當在外觀上與養父相似(花38歐元Cryos就提供照片比對服務)。對此單身女性希望了解的興趣更大一些。花17歐元她就可以從網站上下載使用了假名的候選人特征描述。候選人在其中對100個問題進行了回答:喜歡聽什么音樂?對科學或藝術的興趣如何?優缺點都有哪些?等等。
Cryos主要向已婚婦女提供匿名精子,精子由醫生在診所內人工授精。在美國,單身女性已占了Cryos顧客群的1/3,很多人讓公司將氮氣罐和注射用具送上門,私密的事情再次變得私人化。
全世界每年大約有10萬名人工受精嬰兒。而且人工受精的嬰兒數量越多,下面的問題就越迫切:孩子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還是一種生活方式?生孩子是自我實現還是人權?捐贈精子是醫學還是美容?奧勒·紹給出了答案。他使用的詞是患者,而不是顧客。“女性天生就是要懷孕的。她們必須繁衍后代。”大約15%的夫妻并非出于本意而沒有子女,很多因此而要接受心理治療。
捐獻者
那么那些孩子呢?如果存在繁衍后代的權利,那么是否也有了解自己身世的權利呢?奧勒·紹的論據正好相反。如果說沒有孩子是造化弄人,那么沒有父親則是可以接受的命運。“捐贈精子生產的孩子可以給我打電話。我會對他們說:你們是帶著某種殘缺出生的——那就是沒有父親。我會問這些孩子:‘其他的選擇是什么:你們情愿自己根本不到這個世上?’”他會對他們說:你們不是孤身一人。每10個孩子中就有一個是所謂來歷不明的孩子。而且他說,如果不采取匿名政策,那就不會有捐贈者了。家庭也會出現反叛和分裂,“捐贈精子生產的孩子會指著養父的鼻子罵,你不是我爸爸,憑什么規定我做這做那?”那樣就不會有全球最大的精子庫了。有些捐獻者是希望為別人提供幫助,而有些人只是要來發泄掉必須發泄的東西。有的是想在世上留下點痕跡。而對其他人來說這就像是獻血,沒有人會問,自己的血獻給了誰。
在他們進入精子庫之前,候選人必須進行健康檢查并通過好感測試。該測試由Cryos的工作人員進行。工作人員會自問:我會讓自己的女兒跟他交往嗎?例如,一個翻著白眼、聲音忽高忽低、一會兒英語一會兒丹麥語的人就沒有過關。但像8888號捐贈者這樣的人就是可以信賴的。8888號捐贈者自己也說:“我的基因不是很差。我女朋友也不反對我這么做。她認為,有更多的人像我這樣是好事。”
根據他的自我描述,他“樂于接受新事物、快樂并具有創造力”。他最喜歡的汽車是福特格拉納達。他曾在科索沃服役,以后也想做發展援助方面的工作。在應征表中他給孩子未來的父母留下了這樣一句話:“我知道,有一天孩子可能會敲我的門,但這對我來說沒有什么。相反,我會很高興有人從國外來拜訪我。”■
(楊軒薦自《參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