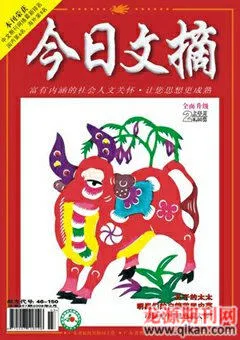雪山哨卡老班長
那年春天,新兵下連我被分到海拔4000多米的青藏高原雪山上的3號哨卡,那里距中隊80多公里,周圍荒無人煙,常年積雪,空氣中的氧氣含量不到內地的三分之一,一年大雪封山的時間有八個月。
已經記不清是哪一天,排長帶著我走了四個小時的山路,翻了三座雪山,才到達我要生活工作的3號哨卡,把我交給了哨卡唯一的戰友——老兵班長薛亮。
第二天,我早早地起床,按照新兵連的習慣,打掃了營區的衛生,站在空曠的高原,望著遠山和天上飄逸的白云,心里涌動著一絲寂寥和惆悵。望著排長漸去漸遠的身影,我的心像雪山上的冰凌,眼里浸滿了淚水,模糊的視線中,我看到了哨位上班長挺拔的身姿。
班長也是新兵下連后來到哨卡的,堅守的7年中,戰友換了一茬又一茬,而他始終把哨卡當作自己的家。
有一天,我問班長是什么力量使他呆在這里,他對我說起一段往事:他到哨卡的第二個冬天的一天,他突然覺得肚子鉆心地疼,吃了藥還是不管用,他的班長非常著急。由于大雪封山,中隊衛生員上不了山,老班長只好獨自下山尋藥,沒想到剛出去不久就遇到了雪崩。久等老班長不回,他把消息報告了中隊,中隊官兵緊急救援,老班長卻始終沒有醒來,永遠留在了雪域高原。
在整理老班長的衣物時,發現老班長一年前寫好的遺書——為了哨所隨時做好犧牲準備。
他在哨卡旁的山坡上用石頭壘起了一座衣冠冢,刻上老班長的名字,讓老班長永遠守衛著3號哨卡。從那以后,他就堅定了在哨卡呆下來的信心。
一天傍晚,班長接到中隊的電話,說未婚妻已到了中隊要上山來看他。放下電話,班長看著未婚妻的照片發呆,茫然又興奮。那是他談了近9年戀愛、入伍后只見過兩面的心上人,他不想讓未婚妻知道自己呆的地方多么艱苦,一直在信里、電話中向戀人描繪這里的風景多么優美、氣候多么宜人。這可怎么辦?整個晚上班長翻來覆去都沒睡好,我卻沉浸在與未來嫂子見面的興奮中。
第二天,我倆起床很早,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凈凈,可一打開房門,我們傻眼了,昨天還是晴空萬里,今天卻鵝毛大雪瘋狂地飄。班長出了哨卡,抖了抖身上的棉大衣,沿著山路走下去。一個多小時后,他遠遠看到指導員帶著自己日夜思念的戀人出現在對面的山脊上。然而,眼前的道路被雪崩堵死,直線不過300米的距離,一對戀人被阻隔。他倆大聲喊著對方的名字,大山里回蕩著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嘶啞的呼喚。
我未來的嫂子走了,已等不到道路疏通的時候了。班長和未婚妻通了電話,嫂子說:雖然僅300米的距離卻沒能相聚,但聽到了聲音,看見了人影,已經很幸福了。
那天晚上,我和班長談心。他對我講起了他倆中學時幸福的初戀、七年間的相思。他說,作為一個兵,選擇了軍營,就要把青春獻給崗位,不能因為兒女情長而辜負忠誠的誓言,崗位雖小但要自覺踐行武警官兵的職責使命。
從他的眼神里,我讀到了一位老兵的堅毅。后來,我們在營房門口修了個假山,用大紅油漆在上面書寫了“高原風雪冷,心中爐火紅,苦樂有取舍,志在寫忠誠”的詩句,激勵自己在艱苦的環境中鍛煉成長。
第二年,我考上了軍校。離開雪山哨卡的那天早晨,班長坐在山腰等我出來,他微笑著從衣袋里取出一個用報紙包好的東西,囑咐我到學校后再打開。我小心地把它裝進了背包,告別了班長。
一晃十多年過去了,我一直把他送我的那本《黨章》珍藏著,每當我遇到困難都會拿出來看一看、讀一讀,便會有一股暖流在心中流淌。
我上軍校的第二年,班長在配合公安民警抓捕射獵藏羚羊犯罪團伙與犯罪嫌疑人搏斗時英勇犧牲了。在他的遺物里發現了一份他到3號哨卡后給黨組織寫的遺書和未婚妻給他的120封情書……■
(趙濤薦自《中國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