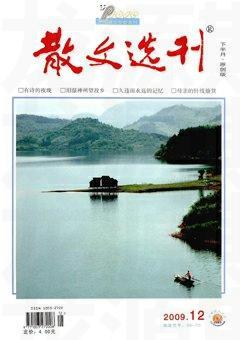大樹和我們的生活
2009-12-25 10:18:26楊獻平
散文選刊·下半月 2009年12期
楊獻平
桐樹栽下沒多久,忽然間,就長大了,我肯定親眼看見了,但沒確切的印象。我好像一直有意忽略著,反過來,它也忽略我——我就在它的身邊,日日看著,甚至還在它身上用刀子刻下自己的名字……而今,它已將我的名字掩蓋了,用并不堅硬的皮膚,將一個人的名字收縮到了時間里面。
父親說,這桐樹的心已經空了,再長下去,啥材料都做不成,鋸了,還能鋸幾塊板子,做家具用!說完,就開始鋸,鋒利的鋸齒不斷深入樹木。第一個回合,它就流出了一些青色的樹汁,亮亮的,像人的眼淚或者口水,“噗嗒噗嗒”滾在泥土上。鋸了一會兒,我和父親滿頭大汗,鋸齒還沒完全穿透桐樹的身體,它就倒了,轟然一聲,落在還沒撒種子的田地里,粗壯的枝干斷成了幾截,裂痕白得耀眼。
父親起身,抓了一把濕土,撒在桐樹茬上說,來年春天,它還能長出一些新枝條出來,幾年后,又是一棵大樹。母親說,桐樹木質軟,只能做桌子面,不如栽一棵椿樹,能當梁,還能做門板。
椿樹木質硬,長勢極慢,樹苗也不怎么好找。父親扛了镢頭,到后山轉悠了大半晌,帶回來一棵椿樹苗,雖還沒有我高,但很直順,新發的葉子已經露出了嫩黃色的小腦袋。父親在桐樹樁一邊又挖了一個坑,提了清水,先潤了底下的干土,把眨巴著根須的椿樹苗兒放在里面,我一锨一锨往里填土,父親不時用腳踩踩。
第二年春天,椿樹代替了老桐樹。再一年的春天,父親請了木匠,叮叮當當做起家具,那棵老桐樹鋸成的木板也干得可以用手指敲出響聲了——不到10天,就變成了嶄新的寫字臺和櫥柜——它留在院子里的根,盡管又滋生了幾次嫩枝,但都被我踩掉了。
插圖:吳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