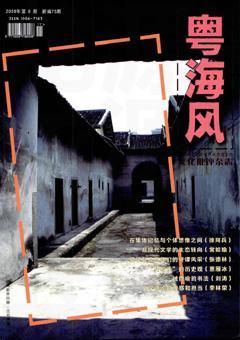“反智論”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中的表現(xiàn)
曹學聰
“反智論”(anti-intellectualism),也可譯為“反智主義”,該名詞因美國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Hofstadter)的《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1962)一書而走紅,此書出版后影響甚大,兩年后即獲新聞大獎——普利策獎,繼而在美國掀起了霍夫斯塔特熱。按余英時的解釋,“反智論”并非一種學說、一套理論,而是一種態(tài)度。余氏認為“反智論”有兩種情況:一是“反智性論者”(anti-intellectualist),即對于“智性”(intellect)本身的憎恨和懷疑,認為“智性”及由“智性”而來的知識學問對人生皆有害而無益;另一種則是“反知識分子”(anti-intellectuals),即對代表“智性”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表現(xiàn)一種輕鄙以至敵視。如余英時所言,兩者實則無本質區(qū)別。[1]無論是霍夫斯塔特還是余英時所談及的“反智主義”,都是將之納入到復雜的文化范疇里,從而涉及政治、歷史、思想、社會等各個層面。本文旨從文學的角度對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中的反智主義的表現(xiàn)作一梳理,并簡單分析其產生的緣由。
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敘述中,都或隱或顯地存在著“反智論”的書寫。具體來說在純文學、嚴肅文學、通俗文學等各個形態(tài)上有不同的表現(xiàn)。
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鄉(xiāng)土”無疑是一個不能遺忘的母題。從20年代肇始于魯迅的“鄉(xiāng)土文學”,到沈從文那一系列悠長而又雋永的“田園牧歌”,再到80年代贏得廣大讀者的汪曾祺那獨特且極富“民間性”的寫作,盡管他們書寫的角度各異,但不可否認,“鄉(xiāng)村”在現(xiàn)當代文學史上作為題材和表現(xiàn)對象的重要性,幾乎要超過城市。如果說魯迅的“鄉(xiāng)土文學”是在于批判國民性,那沈從文的“田園牧歌”則著力于遠離現(xiàn)代城市文明的喧囂,建造不曾被現(xiàn)代文明污染的希臘小廟,這廟里供奉著“人性”。沈從文對現(xiàn)代性的反思、質疑是通過在鄉(xiāng)村與城市、自然與文明的二元比照中顯現(xiàn)的。正如他所說:“請你從我的作品里找出兩個短篇對照看看,從《柏子》同《八駿圖》看看,就可明白對于道德的態(tài)度,城市與鄉(xiāng)村的好惡,知識分子與抹布階段的愛憎,一個鄉(xiāng)下人之所以為鄉(xiāng)下人,如何顯明具體反應在作品里。”[2]在這種城鄉(xiāng)的對比中不難看出沈從文對現(xiàn)代文明的質疑、對啟蒙運動的反思甚至對歷史進化論也不信任。這是審美現(xiàn)代性層面上的“反智主義”,從《紳士的太太》中對上流社會墮落的鄙視,到《薄寒》里對都市文明的否定,再到《有學問的人》、《八駿圖》中對知識分子虛偽、卑瑣心理的揶揄,都明顯表露出這種反智論調。
汪曾祺曾坦言受到過魯迅、廢名的影響。[3]但在表現(xiàn)鄉(xiāng)土民俗方面,其創(chuàng)作風格主要得益于沈從文,作為沈的學生,無論是在為人抑或為文等方面都受其師很大影響。汪曾祺在創(chuàng)作中,重點將鄉(xiāng)土風情納入到審美創(chuàng)造中,從而遠離政治背景,淡化時代環(huán)境,沈從文的語言、意境、心態(tài)等等無不在汪曾祺身上再現(xiàn)。但更重要的是,沈從文遠離城市文明、回歸鄉(xiāng)土民間的“反智”傾向也流淌在汪曾祺的筆尖,“我的小說多寫故人往事,所反映的是一個已經消逝或正在消逝的時代。……隨著經濟的發(fā)展,改革開放,人的倫理道德觀念自然會發(fā)生變化,這是不可逆轉的,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但是在商品經濟社會中保持一些傳統(tǒng)品德,對于建設精神文明,是有好處的”。[4]雖然汪曾祺沒有明確指出反對精英文化,也沒有像沈從文那樣明確地批判現(xiàn)代文明,但其對民間文化的肯定與褒揚,并用對“鄉(xiāng)土”寫作的執(zhí)著追求在實踐上與“反智”論調有契合之處。在現(xiàn)代生活中,“人”已被工具理性異化,不再自由。汪曾祺在創(chuàng)作中把追求生命自由的筆端伸向了民間,在那里他看到了現(xiàn)代都市中難覓的“和諧”,這里“人的一切生活方式都順乎人的自然本性,自由自在,原始純樸,不受任何的清規(guī)戒律的束縛,正所謂‘饑來便食,困來便眠”。就像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桃花源,“這個桃花源中諸多的人物不受清規(guī)戒律的約束,其情感表露非常直接而且質樸,他們雖然都是凡夫俗子,卻沒有任何奸猾、惡意,眾多的人物之間的樸素自然的愛意組成了洋溢著生之快樂的生存空間”。[5]
分析汪曾祺的回歸民間寫作的原因,可以看出汪曾祺一直都意識到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對自己創(chuàng)作的影響及“再使風俗淳”的重要性,汪曾祺對民俗文學有著特殊的偏愛,甚至說過“不讀民歌,是不能成為一個好作家的”[6]這樣不無偏激的話。在喧囂異質的現(xiàn)代都市文明里,在日益緊張的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在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專制控制下,汪曾祺在前現(xiàn)代的淳樸鄉(xiāng)村找到了渴求已久的自由生命、完美和諧的人際關系、健康真實的人性;在自己魂系的鄉(xiāng)土中構建著理想的世外桃源。
在現(xiàn)代中國,“民間”、“大眾”,作為特定的能指概念,其政治意義遠甚于社會學內涵,與今天在商業(yè)運作下的“大眾文化”也有著不同的含義。早在“五四”時期,受俄國民粹主義的影響,“勞工神圣”、“到民間去”的口號就已喊遍中國,知識分子已有明顯的反智論跡象,陳獨秀就認為“只有做工的最有用最貴重。這是因為什么呢?我們吃的糧食,是那種田的人做的……我們穿的衣服,是裁縫做的,我們住的房屋,是木匠瓦匠小工做的……這都不是皇帝總統(tǒng)做官的讀書的人底功勞”。[7]1919年在《平民教育》上有一篇文章《教育的錯誤》談及:“念書人是什么東西,還不是‘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無用而又不安生的一種社會的蠹民嗎?這一種無用的人縱然受了教育,在社會上依然無用……再翻回頭來,看看那些大睜著眼不識字的可憐的平民,卻實實在在我們的衣食生命都在他們掌握之中。他們才是真正的中國人,真正的社會的分子。”[8]30年代,受政治意識形態(tài)影響并控制的左翼作家們,號召到底層去、到民間去、與大眾結合,認為應該用大眾口語作為創(chuàng)作的語言,并且認為真正的道德與智慧來自底層民眾。當時的文藝大眾化使得文藝走向了宣傳、鼓吹,從而帶有極強的意識形態(tài)的功利色彩。40年代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上,毛澤東認為,“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干凈了,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 腳上有牛屎, 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9]文藝作為政治文化語境下的產物,“知識分子”與“智性”本身已經全然遭到否定。這個層面上的“反智”,究其根源在于中國知識分子潛意識當中浸染的儒家民本思想在俄國“民粹”思想的影響下,再加上本身缺乏獨立的主體意識,從而在強硬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面前容易喪失自己,逐漸從精英滑向底層,由批判轉為頌揚。
同以審美現(xiàn)代性批判啟蒙現(xiàn)代性的純文學和在政治意識形態(tài)下書寫的嚴肅文學一樣,通俗文學也有著“反智論”的傾向,主要表現(xiàn)在注重德性,回歸純樸自然的本性。這一點在金庸的武俠小說中有突出表現(xiàn)。不少論者都曾提及,金庸凡十五部作品有一個明顯的特征就是小說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來越低。從早期的陳家洛、袁承志,到郭靖、楊過,再到狄云、石破天,可以看出金庸認為“知識”有礙真正的“俠”的塑造,所以金庸讓他的主人公們一個個在遠離正統(tǒng)教育的地方成長,蒙古大漠之郭靖、流浪市井之楊過、海外極地之張無忌,閉塞鄉(xiāng)村之狄云、石破天……正因為他們是沒有受到“正統(tǒng)知識”污染的璞玉,故而他們的人格較之那些所謂的中原“俠義之士”才更健全更理想。
倪匡評價《連城訣》是一部“壞書”,“寫盡了天下各色人等的‘壞”。[10]的確,金庸對世俗文化中的虛偽、貪婪、卑鄙、陰謀、殘忍作了徹底的暴露,這一切對剛從鄉(xiāng)下走出來的不諳世事、無知無識的狄云來說是不可思議的。還有一個無知勝有知的極端例子,《俠客行》中的狗雜種不僅沒有知識、毫無欲求,甚至連自己的姓名家世都沒有,但金庸偏偏就讓目不識丁的他破解了幾十年來兩位島主和中原無數(shù)“武學專家”都不能參透的至上武學。看似意外,實在情理之中,金庸在“后記”中解釋到:“大乘般若經以及龍樹的中觀之學,都極力破斥煩瑣的民相戲論,認為各種知識見解,徒然令修學者心中產生虛妄念頭,有礙見道,因此強調‘無著、‘無住、‘無作、‘無愿。邪見固然不可有,正見亦不可有。”[11]金庸對“智性”及“知識分子”的價值的否定,來自于對禪宗和道家精神的領會。禪機所謂“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要真正悟會要義,須不為“所知障”才行。道家也認為“圣人不死,大盜不止”,所以唯有“絕巧棄利”,“絕圣棄智”,道德方能臻于理想完美。
通俗文學由于其通俗性與大眾化,受市場取向的影響,適應大眾的消遣娛樂需要,從而在內容上多淺顯明白,反精英立場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了,當然易于在大眾中流行。本雅明在《技術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肯定大眾藝術具有民主性的一面,并認為大眾文化可以增進人們的民主意識,進而能影響社會變革。本雅明是站在大眾的立場上,反對精英文化,肯定大眾藝術的。“反智”傾向顯而易見。
縱觀20世紀中國文學,從“五四”伊始直到新時期,在文學的三種形態(tài)上均有不同程度及性質的“反智主義”表現(xiàn)。中國的“反智主義”作為話語資源直接來源是霍氏的《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而深層根源是來自中國本土固有的傳統(tǒng)文化資源,其中以禪宗及道家尤為明顯。如果對“反智主義”稍加追究,即會發(fā)現(xiàn),對“知識”或“知識分子”的反對并非來自其對面平民或大眾,而是精英知識分子自身制造的一種質疑、批判現(xiàn)代性的意識形態(tài),換言之,是知識分子站在民眾的立場代之言說的一種態(tài)度。作為審美現(xiàn)代性層面上表現(xiàn)出來的反智論,對在人與人及人與自然關系日益緊張異化的今天,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當知識分子獨立人格漸失,迎合主流政治意識形態(tài),屈身仰視底層民眾來貶斥自身及自身擁有的“智性”,這種帶民粹思想的“反智論”破壞性很強。由此看來,對“反智論”在不同文學形態(tài)上的表現(xiàn)作具體分析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1] 余英時《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tǒng)》,選自《歷史與思想》,臺北:聯(lián)經出版社,1976年,第2頁。
[2] 沈從文《沈從文選集》(第五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0頁。
[3] 汪曾祺 《談風格》,選自《晚翠文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8年,第102—103頁。
[4] 汪曾祺《菰蒲深處》,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3年,第3頁。
[5] 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48頁。
[6] 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論卷》,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3年,第4頁。
[7] 陳獨秀《勞動者底覺悟》,見《獨秀文存》,蕪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0頁。
[8] 張允侯等編《五四時期的社團》(三),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79年,第20頁。
[9]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851頁。
[10] 倪匡《我看金庸小說》,收入《金庸其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21頁。
[11] 金庸《俠客行·后記》,廣州:廣州出版社,2002年,第56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