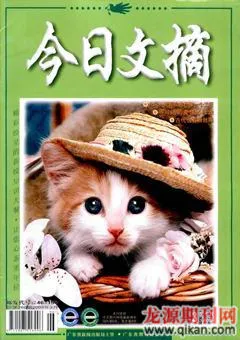幾米:我喜歡自己像一個(gè)工匠
午后的香港時(shí)代廣場(chǎng),總是熙熙攘攘,川流不息。就在這幾天,原本一成不變的廣場(chǎng)上,居然放置了好幾個(gè)碩大的玩偶人像,它們都有著俏皮而天真的表情,還有著小如豆大的瞇眼,更有著圓圓的可愛(ài)臉蛋……這些,不正是幾米繪本中的人物嗎?原來(lái),在寸土寸金的時(shí)代廣場(chǎng),正在舉辦臺(tái)灣著名繪本畫家?guī)酌椎摹癗everEndingStory—?jiǎng)?chuàng)作十年回顧展”。
二樓中庭,展覽門口,并不高大的幾米始終保持著不變的親和微笑,被眾多“粉絲”簇?fù)碇淇斓貫榇蠹液灻裟睢!懊襟w常常說(shuō)我害羞、淡泊,其實(shí),我不太確定自己是否符合這樣的形容。在正式的場(chǎng)合,我常會(huì)退卻,不自在。不過(guò),真的要我上臺(tái),我還是可以侃侃而談的,比如像今天。哈哈哈……”幾米站在自己的畫作前,說(shuō)到這里,俏皮地笑了起來(lái),“與其說(shuō)我害羞,不如說(shuō)我一直都不太習(xí)慣‘幾米’所帶來(lái)的名氣吧!”站在幾米面前,聽著他率真自然的言談,很難想像眼前這個(gè)長(zhǎng)著“娃娃臉”的著名畫家已經(jīng)有50歲了。
繪本捕捉美麗
1958年,幾米出生于臺(tái)灣,從小喜歡繪畫的他,自文化大學(xué)美術(shù)系畢業(yè)后,曾在廣告公司工作了整整12年,練就了他所謂的“在創(chuàng)作時(shí)能夠很快抓住瞬間靈感”的特殊本領(lǐng)。1994年,他辭職在家,一門心思為報(bào)刊畫起了插圖。也就在這個(gè)時(shí)候,原名廖福彬的他,開始用“幾米”(自己的英文名“Jimmy”)作為自己的筆名。“因?yàn)檫@個(gè)名字,很多讀者以為我是外國(guó)人,還有人以為我就姓‘幾’,把我稱為‘幾先生’!”
10年前,他以“幾米”這個(gè)名字創(chuàng)作的第一本“成人繪本”—《森林里的秘密》出版了。通過(guò)筆下那只可愛(ài)的大兔子,幾米開始成為臺(tái)灣書市的一道“流行旋風(fēng)”,沒(méi)過(guò)多久,這道“旋風(fēng)”又席卷到了香港、大陸地區(qū),一時(shí)間,全中國(guó)都知道了“成人繪本”,知道了幾米這個(gè)“大器晚成”的畫家。甚至連德高望重的老一輩漫畫家丁聰,都坦言自己“不僅看,而且很喜歡幾米的作品,因?yàn)槠渲杏兄鴱?qiáng)烈的時(shí)代感,相當(dāng)好看”。
自《森林里的秘密》之后,10年來(lái),幾米每年都會(huì)創(chuàng)作2到3種繪本新作,尤其是隨著描寫都市人情感生活、生存狀態(tài)的《地下鐵》、《向左走,向右走》等諸多作品的廣泛傳播,加之同名電影的熱映,幾米的讀者群一下子從中國(guó)擴(kuò)大到了日本,從英國(guó)流行到了美國(guó)。如今,法國(guó)、西班牙,甚至愛(ài)沙尼亞等國(guó)家,都有幾米繪本的不同翻譯版本,世界各地都能看到幾米漫畫的衍生產(chǎn)品:玩偶、抱枕、馬克杯、餐巾紙……幾米儼然成了具有國(guó)際影響力的中國(guó)畫家。
“繪本和漫畫其實(shí)是不太一樣的繪畫表現(xiàn)形式。”常常有人對(duì)幾米冠以“著名漫畫家”的稱謂,但他始終覺(jué)得自己不能算作一個(gè)地道的漫畫家,“如果你把漫畫的對(duì)白文字遮住了,那就會(huì)無(wú)法了解作者要說(shuō)什么;而繪本的圖片則是可以單獨(dú)存在的,甚至可以一看再看。而且,繪本的文字部分有情節(jié),有故事,甚至具備了某些小說(shuō)的特質(zhì)。”因此,幾米特別喜歡“繪本作家”這個(gè)全新的稱呼。“我與朱德庸、蔡志忠這樣的漫畫家有很大的不同,他們愛(ài)用線條去表現(xiàn)想說(shuō)的東西,可以做成長(zhǎng)篇的小說(shuō)。而我,只是畫一張簡(jiǎn)單的圖像,但在這張圖像里,我要說(shuō)的東西卻有很多很多。”
在幾米的作品中,出現(xiàn)得最多的,往往是有關(guān)人和人之間關(guān)系的探討,尤其是兩個(gè)不太熟悉的人之間,在同一個(gè)空間下,會(huì)否發(fā)生一些微妙的關(guān)系?對(duì)此,幾米有著自己的解釋:“我畫現(xiàn)實(shí)世界,畫寂寞城市里的對(duì)話。我生活在城市里,放眼望去,大部分都是我不熟悉的人們,于是我們大家一起入了畫。”而這些“探討關(guān)系”的作品,往往還會(huì)以一個(gè)美麗愛(ài)情故事的形式出現(xiàn),但事實(shí)上,幾米卻覺(jué)得“愛(ài)情其實(shí)很微不足道”,“我常覺(jué)得人們都喜歡夸大自己的不幸,或者夸大自己的快樂(lè),超脫一點(diǎn)來(lái)看,這些東西其實(shí)不存在。人生無(wú)常,愛(ài)情美麗,我只能用畫筆捕捉被遺忘的無(wú)常與美麗”。
繪本作為一種圖書題材,最早的源頭便是幾米。在他的影響下,如今有許多年輕作者都在嘗試迎合所謂的“讀圖時(shí)代”,試圖用繪畫結(jié)合文字的辦法,來(lái)講述一個(gè)個(gè)奇妙的故事。但無(wú)論如何模仿,總是很難超越幾米。“我注重我的作品,注重畫出來(lái)的東西,故事、顏色、線條……是否都做到最好?如果做到了,我會(huì)很高興,如果沒(méi)做到,我會(huì)反復(fù)去做,做到滿意為止。”幾米正是以如此敬業(yè)的精神與態(tài)度,走著自己的創(chuàng)作道路。
對(duì)于幾米繪本的不斷升溫,也有不少評(píng)論家認(rèn)為:這些作品僅僅體現(xiàn)了“中產(chǎn)階層的文化趣味”,讀幾米只能是一種時(shí)髦,一種小資情調(diào)的標(biāo)榜。更有甚者,認(rèn)為繪本是“讀圖時(shí)代”的快餐文化。對(duì)此,幾米的回答頗為幽默:“小資?那可能是讀者跟我都是同一類型的人,當(dāng)我用圖像去感受一個(gè)東西,讀者也能感受得到。一個(gè)作者不可能超越他的生活,我不可能去畫農(nóng)民,畫其他我不熟悉的東西。”說(shuō)到此,他聳聳肩,做出一副無(wú)可奈何的表情,“當(dāng)然會(huì)有繪本作家去做快餐文化,但繪本絕不是快餐文化。其實(shí)在國(guó)外,好的繪本是可以代代相傳的。如果一幅圖畫有足夠的美感,那它就不僅僅是一張圖像。你可以從中看到許多要表達(dá)的東西。我始終覺(jué)得,我的畫被怎樣歸類不是我的問(wèn)題,這是讀者和評(píng)論者的權(quán)利。我僅僅是做我認(rèn)為開心的事情。”
幾米的幸與不幸
幾米的童年曾經(jīng)有一度在鄉(xiāng)村度過(guò)。當(dāng)時(shí),他只有4歲,與老祖母在一起生活,遠(yuǎn)離城市里的父母和兄弟,常常會(huì)讓他有種被遺棄的感覺(jué)。“這件事以前沒(méi)有想起,現(xiàn)在覺(jué)得那是造成我性格內(nèi)向、敏感、多疑的部分原因,也因此慢慢形成了我作品中的某些孤單、清冷的元素。”幾米總覺(jué)得近年來(lái)媒體夸大了他在鄉(xiāng)間的童年歲月,但他卻從不否認(rèn)“孤獨(dú)”在其作品中的重要地位。
1995年,幾米查出得了血癌,經(jīng)歷了生命中最為黯淡的歲月,但這段飽受折磨的傷痛時(shí)光,卻讓他變得感性而敏銳,“許多平凡的小事變得重要,而許多平凡的大事又變得無(wú)足輕重”。逐漸復(fù)原之后,他的作品開始呈現(xiàn)出另一種味道,在歡樂(lè)畫面外,有淡淡的哀傷、疏離的情感和些許的無(wú)奈。
好在家人常常會(huì)給幾米許多鼓勵(lì)與安慰。幾米擁有一個(gè)幸福的家庭,生性低調(diào)的夫人從事翻譯工作,常常是幾米創(chuàng)作的“第一讀者”與“把關(guān)者”。偶爾,她也會(huì)為自己丈夫的作品修改文字,夫妻倆還經(jīng)常在一起討論下一步創(chuàng)作的故事大綱。更有意思的則是幾米的小女兒。這個(gè)只有幾歲大的孩子從來(lái)不覺(jué)得自己的老爸畫得有多好。“她根本不理我,還時(shí)常嘲笑我,說(shuō)我畫的人眼睛都只有一個(gè)小黑點(diǎn),連眼白都沒(méi)有,特別奇怪。”說(shuō)到這里,幾米露出無(wú)奈的一笑,“她覺(jué)得還是她畫得比較好!”
如今,幾米保持著極為規(guī)律的生活狀態(tài):早上7點(diǎn)起床,隨后送女兒上學(xué),8點(diǎn)左右來(lái)到自己的工作室,開始享受獨(dú)自創(chuàng)作的樂(lè)趣。“我一直都是一個(gè)人工作,有時(shí)候太安靜了,就會(huì)聽聽音樂(lè),盡量不出門,生活得很‘宅’。”幾米往往會(huì)在自己的工作室靜靜地畫上一整天。天黑之后,再慢慢地回到家中,享受家庭的樂(lè)趣。“我從沒(méi)感到這樣的生活很單調(diào)。對(duì)我來(lái)說(shuō),創(chuàng)作是工作,也是娛樂(lè)。可以一整天都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我覺(jué)得很棒,我非常喜歡這樣的狀態(tài)。”幾米常說(shuō),“我喜歡自己像一個(gè)工匠。”在他看來(lái),自己就好像每天在一個(gè)固定的空間里,默默地雕琢著一件器皿。完成之后,又繼續(xù)下一件,在不斷的創(chuàng)作中,再生出新的創(chuàng)作。
有時(shí)候,幾米也會(huì)考慮讀者和市場(chǎng)的因素,但一旦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就根本無(wú)法顧及這些了:“在我之前,從來(lái)就沒(méi)有‘成人繪本’這個(gè)概念,何來(lái)‘市場(chǎng)’?但出版后,出現(xiàn)了一群喜歡這類作品的讀者,市場(chǎng)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創(chuàng)作很甜美,市場(chǎng)很殘酷,幾米覺(jué)得自己一直是個(gè)幸運(yùn)兒,“找到了一個(gè)市場(chǎng),找到了一種成功的出版類型”。因此,他自己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努力做個(gè)專職的創(chuàng)作者”。■
(陳婉婷薦自《時(shí)代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