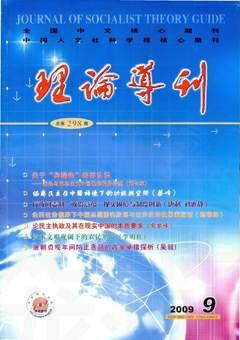侵犯商業秘密罪之人格考量
權明麗
摘 要: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侵犯商業秘密犯罪日益突出。我國《刑法》第219條的侵犯商業秘密罪對構成該罪的行為方式和處罰做了比較明確的規定。該規定側重于構成犯罪的客觀行為,沒有因人而異、區分情況,對人身危險性不同的人處以相同的刑罰,這既不符合人格刑法學的理論要求,也不利于對犯罪人員進行教育改造。為此,我們認為有必要以人格刑法為視角來考量我國的侵犯商業秘密罪,以期對該罪進行重新審視和完善,使該罪名的法律規定更趨于科學合理。
關鍵詞:人格刑法;商業秘密;完善
中圖分類號:D922.294.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09)09-0091-03
一、 人格刑法的基本內涵
從詞源學的角度來看,“人格”最早出現于希臘語中,表示“移近”、“置換”,在拉丁語中是Persona,表示“面具”、“偽裝”,同戲劇角色有關。[1]在中國古代典籍當中,“人格”一詞未曾出現過。新版《辭源》也沒有收入“人格”這一詞條。《漢語大辭典》第一卷、《辭海》及臺灣版《中文大辭典》雖收有“人格”辭目,但義項的證據均取自近代,前者列蔡元培、梁啟超等人之文,后兩者舉章太炎《諸子略說》。
人格刑法學是指將行為人的人格作為定罪和量刑的考量因素,使犯罪本質由單純的以行為為一元過渡到行為與行為人并重的二元結構。定罪既要考慮行為,也要考慮行為人,即“應當以作為相對自由主體的行為人人格的表現的行為為核心來理解犯罪。”[2]55同時,量刑與行刑也應考慮行為人的人格。這一理論淵源于人格行為論[2]99和人格責任論[2]366。最早提出人格刑法這一理論的是日本學者大塚仁。1900年,他在《人格刑法學的構建》一文中,明確提出了“人格刑法學”的概念和設想,將行為者人格引入犯罪論和刑罰論。大塚仁認為,構成要件之中的行為要件,不是單純的、孤立的與行為人無關的僵硬行為,而是作為行為者人格體現的行為,構成要件中的違法性是客觀違法要素(行為)和主觀違法要素(主觀罪過)的有機結合,有責性是以具有相對自由意志的行為人的行為的譴責為核心(第一位),同時也考慮對行為背后的行為人的犯罪人格的譴責。刑罰的量刑應以行為對法益之危害程度和行為人的犯罪人格為基礎。總之,對行為人定罪量刑,既重視客觀行為,也考慮行為人的人格,以此二者為核心,對整個刑法理論進行重新思考,是人格刑法學之精義。[3]8在大塚仁發表了這篇論文之后,其在《人格刑法導論》(總論)中,從理論上進一步深化、完善、整合了人格刑法理論,將人格這一因素引入到了犯罪論和刑罰論當中,將他所構想的“人格的犯罪理論”和“人格的刑罰理論”相結合,稱之為“人格刑法學”。人格刑法學理論的提出,給刑法這種“惡”的學科注入了溫情的人性關懷,注重發揮刑罰對犯罪人的矯正改善功能。但是,它也有不完美之處,正如學者所言:“大塚仁博士未明確說明犯罪人格的概念和類型,以及行為人的人格怎樣測量,及其在頂罪中如何發揮作用。”我國學者以“善”的沖動對人格刑法學加以完善,提出了徹底的“犯罪行為與犯罪危險性人格的二元定罪機制”,并對我國的犯罪構成理論進行改造,將行為人犯罪危險性人格與行為并重[3]228,并對如何具體操作,即對犯罪危險性人格的鑒定作了完善的制度設計。至此,貫穿于犯罪論與刑罰論的人格刑法學理論形成。
二、 侵犯商業秘密罪中的人格因素
根據我國刑法第219條的規定,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的主要表現方式為:(1)以盜竊、利誘、脅迫或其他不正當手段獲取權利的商業秘密;(2)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以前項手段獲取的權利人的商業秘密;(3)違反約定或違反權利人有關保守商業秘密的要求,使用或允許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業秘密;(4)明知或應知前述三種違法行為,獲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商業秘密和行為。有的學者將其分別概括為:(1)非法獲取商業秘密;(2)濫用非法獲取的商業秘密的行為;(3)濫用合法獲取的商業秘密的行為;(4)以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4]也有學者將第219條所列的行為方式概括為以下四種行為類型:一是采用非法手段獲取商業秘密,既可能是采取不正當手段直接從權利人手中獲取,也可能是從侵權行為人那里獲取;二是非法披露商業秘密,既可能是采用不正當手段或從非法途徑獲取或者披露,也可能是合法知悉者違反保密義務而披露;三是非法使用商業秘密,既可能是采用不正當手段獲取或者直接使用,也可能是合法知悉者不經權利人許可而使用;四是非法允許他人使用商業秘密。無論學者們將法律條文所規定的四種行為方式如何概括,各種行為所蘊含的犯罪危險性人格則是不同的。
從以上四種行為方式來看,第一種方式是通過盜竊、利誘、脅迫等手段來獲取商業秘密,這已顯示了行為人的犯罪危險性人格。第二種方式不但通過盜竊、利誘、脅迫等手段獲取了商業秘密,而且還更進一步,即通過積極的作為方式將非法獲取的商業秘密進行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從犯罪危險性人格即人身危險性的角度來說,此種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顯然大于前者。第三種行為方式所表現出來的人身危險性要小于第一種行為所表現的人身危險性,此種行為人只是違反了約定或權利人有關保守商業秘密的要求,不涉及盜竊、利誘、脅迫等惡劣的手段,有學者甚至認為這可理解為一種民事上的違約行為。違約行為所表現出來的主觀惡性顯然小于盜竊、脅迫等犯罪手段所表現出來的人身危險性。第四種方式中行為人在“明知或應知”的心理支配下,獲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商業秘密,這一行為所表現出來的人身危險性與第一種所表現出來的人身危險性相當。
刑事實證學派將刑事法學的視角傾向犯罪人后,在刑事法學領域引起巨大的震動。盡管早期的人身危險性理論過于偏激,并且因為被法西斯所利用而受到批判,但不可否認的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是客觀存在的,它準確地揭示了犯罪人的特征,因而是科學的。”[5]而行為人的人格即犯罪危險性人格往往通過行為表現出來。雖然我們反對僵化的征表主義學說,但“人之行為,系主觀與客觀的綜合體。犯罪行為,則為行為人人格之現實表露。因此,無視行為,僅視行為人為對象,或與行為人分離,僅就行為而評價的犯罪理論,均有欠妥切” [6]。刑法第219條所規定的同種行為所征表出來的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是客觀存在的,而且人身危險性的大小是不同的,即犯罪危險性人格存在,但不相同。
三、人格刑法對侵犯商業秘密罪的考量
人格刑法當中充滿了對人性的關懷,在吸取舊派和新派理論的基礎上將人格的考量貫穿于整個刑法學當中。不但在量刑、行刑中關注行為人的犯罪危險人格,而且在定罪時同樣予以充分考慮。以人格刑法學為視角來考量我國刑法所規定的侵犯商業秘密罪,要從罪與刑兩個方面來進行。
1.罪之方面。我國刑法第219條規定:有下列侵犯商業秘密行為之一,給商業秘密的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造成特別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在定罪上,列舉了四種行為方式,而且在以上四種行為造成“重大損失”的時候才予以定罪。通說認為此罪是結果犯,即只有出現重大損失或特別嚴重后果的結果時才成立犯罪。在法條表面的文字用語和字里行間的含義中以及眾多的理論書籍當中找不到行為人的犯罪危險性人格的身影,其給我們展現的只有“行為”的濫觴而沒有“行為人”的蹤跡。雖然刑法總論當中在有關犯罪主體的規定涉及到了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的問題,但是人格這一重要因素在對該罪的規定中并沒有受到應有的、足夠的重視。人格刑法學強調的是定罪與量刑要考慮人格因素,并把人格因素提高到了與犯罪構成要件同級并重的地位。[3]228而從我國刑法對該罪條文規定和學術上的理論分析來看,偏向于以行為為標尺而忽略行為人。客觀主義的刑法理論在刑罰的制定與執行上側重于報應,主張“因為有犯罪再科處刑罰,”即有罪必有罰。過分強調報應必然忽視預防和教育。正因為如此,累犯與再犯急劇上升,教育改造罪犯的效能低下。不考慮人格而行刑,不對癥下藥,只能是治標不治本,興一時而不能興長遠。
2.刑之方面。在量刑上將危害性不同的犯罪行為的法定刑混雜在一起而不做區別,沒有形成一個與罪行相適應的刑罰階梯。在刑的規定上不考慮人格的異殊,與刑罰的個別化理念不符,違背了法理的一般正義與個別正義兼顧的正義觀念,片面的追求形式正義而犧牲了實質的正義。我國刑法第219條將侵犯商業秘密罪的四種行為進行了列舉式的敘述,然而在量刑上卻劃一而論,“給商業秘密的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造成特別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前三種行為方式主觀方面均為故意,但故意的內容不同,行為方式不同、行為主體所承擔的義務不同,因而社會危害性也不同。但《刑法》第219條在法學的規定上并沒有體現出不同的故意行為及過失行為在量刑上的區別。”而人格刑法學則是關懷人、以人為本、充滿人性的理論,強調“犯罪人是刑事科學的出發點和歸宿。”[3]71所以,以人格刑法學為視角來審視此罪有關刑的規定來看,我國刑法對侵犯商業秘密罪的規定仍存在諸多不合理之處。
四、以人格刑法為導向對侵犯商業秘密罪的完善
在堅持以人為本,人權得以彰顯,人越來越得到重視的背景之下,我們更應以一種善的沖動來關注人這一智慧而復雜的實體。人格刑法作為順應時代思潮,與時代脈搏相合拍的人性化理論理應成為我們的指向標,成為指導我們進行理論研究與實務操作的指南,指導我們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針對侵犯商業秘密罪之人格考量,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完善:
1.正確理解和界定“應知”。由于“應知”一詞的存在,使得學界對這一詞語的解釋出現紛爭,有的認為是過失的主觀心態,而有的學者則認為是故意。導致出現“故意”和“過失”紛爭的罪魁禍首當然是我國刑法的規定,從我國《刑法》第219條的規定和學界的詮釋來看,此罪是結果犯、法定犯。在結果犯、法定犯這樣一類的犯罪行為當中,將“應知”這一許多學者認為是過失的犯罪來加以處罰,使我國刑法過于膨脹、犯罪圈過于擴大。基于人權保障的需求和人格刑法對人格的要求,我們認為應當取消對“應知”這一過失犯罪的刑罰處罰,對其做出非罪化的處理。在刑法中取消這一規定,來消除學界的紛爭,為刑事立法的明確性來保駕護航。雖然,“法律不是被嘲笑的對象”,刑法的條文也不可能規定的全是完全明白無誤的普通的用語,但是我們應當有這樣的一種理念,即“立法者應該像哲學家一樣思考,但像農夫般說話”[7],這樣既符合時代的要求,也縮小犯罪圈,體現了刑法的謙抑性。
2.區分危險性,分格量刑。我國《刑法》第219條的規定:有下列侵犯商業秘密行為之一,給商業秘密的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造成特別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我們認為,對行為方式和人身危險性不同的行為人不加區別的規定同一幅度的刑罰方法是不妥的。合理的做法是將法定刑分格,對犯罪危險性人格不同的行為人處以不同的刑罰,因人而異,實施刑罰個別化原則,進而實現實質正義。也許有人認為法官可以充分發揮自由裁量權來予以處理,但殊不知西方大多數國家的立法與司法運作是:立法定性,司法定量;而我國則是立法既定性又定量。這與人們對法律的信仰和對法官的信任度有關,更重要的是司法者的素質問題。在法治國家尚未完全確立的我國現階段,人們對法律的信仰不夠,更有許多人對法官不信任,而且,司法者的素質也是一個我們無法回避的問題。因此,在法律中明文規定針對不同的行為所展示出來的不同的社會危害性和不同的犯罪危險性人格進行不同的處罰是比較科學的。這樣針對人身危險性不同的人,適用不同的刑罰,更能夠與刑法的正義理念相適應。“正義是法律,是刑法的靈魂”“盡管刑法的正義體現在許多方面,但是,罪有應得,惡有惡報是刑法正義的基本表現。”[8]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罪行的輕重相適應,與行為人的犯罪危險性人格相匹配。脫離犯罪危險性人格而實施的盲目的刑罰是不明智的,是達不到刑罰的報應與預防的目的的。況且,近代刑法中興起了責任主義的原則,針對行為人的人格而實施不同的刑罰是與責任主義相適應的。
3.區分情況,兼采民事行政制裁方式。我國《刑法》第219條所規定的構成該罪的第一種行為方式是指以盜竊、利誘、脅迫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獲取權利人的商業秘密的。單獨實施這些行為而不進一步實施其他行為能造成商業秘密的權利人的重大損失嗎?答案雖然不是否定的,但至少也不那么肯定,“因為獲取行為不會給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造成重大損失的是披露、使用行為。”[9]在實施了上述行為后,對權利人能否造成重大損失這一結果則是不確定的,而且一般情況下僅有盜竊的行為并不會給商業秘密的權利人造成損失,所以,“對非法獲取商業秘密的行為單獨做出規定并沒有多大實際意義。”[9]為此,我們認為應當將有限的司法資源用到對社會有害的行為上,充分發揮刑法的社會保護和人權保障的機能。將不可能發生現實危害的行為做出罪化處理,做到刑事法網恢而不漏。但是,對這一行為不動用刑法制裁并不代表對其放任自流,而等到發生結果時再去處罰,這種亡羊補牢的思想應當摒棄。筆者意見,可以對這種行為進行民事或行政制裁而不必動用刑法,這樣符合刑法的謙抑性思想。
4.將第三種行為方式作為非犯罪化處理。我國《刑法》第219條所規定的構成該罪的第三種行為方式是:違反約定或者違反權利人有關保守商業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業秘密的。這種行為方式利用民事法律規范去調整即可,因為其從本質上來說是民事上的違約行為,刑法卻加以干涉,有熱心過度之嫌,與“法律不理會瑣碎之事”的法諺不符。處罰人身危險性不夠嚴重的行為人一方面擴大了犯罪圈,另一方面使行為人留下污名劣跡,而且也起不到刑罰應當起到的教育作用。正如有的學者所言:“…….對普通民事違約行為過于嚴厲,處罰了不當罰的行為……”,“這是一種因合同而產生的約定義務,泄露商業秘密本質上是一種違約行為,是對債的違反。”“從刑法存在的特殊性和刑法與市場經濟的關系的角度來看,刑法在這里雖然是熱心過度了”。[10]民事上違約行為尚顯現不出其人身的不受刑罰的處罰性。因為“罪責越重,刑罰越重,”用英語國家的法律格言來表述就是“罪行越大,絞刑越高”,推而廣之則是沒有應受刑罰處罰的人格,也就不能被用以刑罰。
人格刑法學是對新派和舊派理論的揚棄的結果,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理念,也符合時代的潮流和刑法的機能的要求,能夠將行為人的危險性人格貫穿到刑法學的始終。用這一充滿人性的理論來審視我國的侵犯商業秘密罪的不足并對其進行完善是科學的,合理的。
參考文獻:
[1][俄]尼古拉·別爾嘉耶夫.人的奴役與自由[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16.
[2][蘇]大塚仁.刑法概論[M].馮軍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3]劉艷紅,甘怡群.人格刑法導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4]趙秉志.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研究[M].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1999:299.
[5]陳興良.走向哲學的刑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93.
[6]甘添貴.刑法之重要觀念[M].臺灣瑞星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6:50.
[7][德]亞圖·考夫曼.法律哲學[M].劉幸義,譯.臺灣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0:110.
[8]翟中東.刑法中的人格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3:91.
[9]李希慧,劉斯凡.侵犯商業秘密罪的立法缺陷及其彌補—以商業秘密的概念與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共同為視角[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3,(3).
[10]唐稷克.罪刑法定視野下的侵犯商業秘密罪[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3).
[責任編輯:陳合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