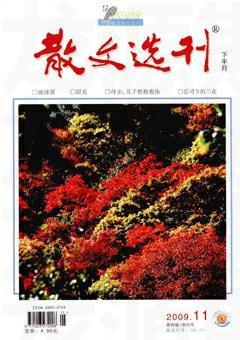陽光中的老年斑
高維生
不知為什么,我所有的精力集中在手上。手掌豎起對著陽光,我一點點地看。一個斑點,攀伏在手背上,離凸起的淡藍色的血管那么近,想走進血脈中。順著血水,它可以走遍各個部位,在身體里流浪,它會發現我內心的世界。
看見老年斑的一瞬間,我并沒有情緒波動,驚恐地抵抗,只是注視,而且是久久地注視。其實我早就發覺,激情消失了很多。對待事情上,我沒過去容易沖動了,更多的是順其自然,不想爭個高低。我回到家中,不想下樓,戴一張假面具去應酬人與事。坐在窗前,泡一杯清茶,在繚繞的茶香中,向窗外眺望。有時拿著數碼相機,對著窗外的云絮拍個不停。我想拍很多的云,陰天的,晴天的,冬天的,夏天的,秋天的,舒卷的,濃重的。這些云記錄著日子,記錄著情感,將來翻閱一本云的圖片日記,回味一天天的情景,這是老年的事情了。我的一個書櫥,一層層地排滿傳記,我每天都站在那里,透過玻璃門向里面觀望。
書櫥里有一對泥塑的“老夫妻”,笑瞇瞇地望著我,這是我到樂山時買的工藝品。
第二次到樂山是在雨夜,白色的海棠花開滿了城市,春天很多的樹開花了,不大的雨絲,細細的,不急不躁。我住的女神賓館,是半圓形的建筑,坐落在半山間,賓館的名字取于郭沫若的詩,他的家鄉就在樂山的沙灣。賓館下面的街叫海棠街,這條街通往大渡河邊。樂山師院坐落在江邊,與大佛隔江相望。晴天的時候,大佛顯得格外莊重。一千多年過去了,樂山大佛閱盡了人間的風雨,經歷了戰亂和朝代的更迭。我喜歡一個人,趴在學校門前的護江墻上,看著大渡河水靜靜地流走,聽船上的汽笛在江面嘹亮,一只渡船來來往往地接送客人。一上午,我沒離開校門前,就這樣過去了。后來,我問當地的人,這個渡口的名字。他說:“叫李家渡口。”我記住了李家渡口的上午,想了很多的事情。早晨是在一家“毛記面館”,我來樂山,早餐是在這兒吃一碗“抄手”,上面放幾片綠色的菜葉,浮著紅油,吃一口麻辣的,心情特別好。小面館不大,幾只條凳,幾張方桌,每天的客人卻不少。這是一家人開的小店,丈夫、妻子、女兒,他們說著一口樂山話,我一句也聽不懂。早餐后,我沿著馬路向西走,在陌生的城市,我分不清東南西北。樂山是旅游城市,每天有大量的游客,街道上的人力三輪車是一大特點,花五塊錢,跑遍半個城市。三輪車夫靈活機動,只要看到外地人,他就跟在后邊不斷地吆喝。樂山人的生活節奏緩慢,街頭很多的店前都擺著折疊椅,人躺在上面,旁邊放一杯茶水。樂山多陰天,曬著難得一見的陽光,消磨一天的時間。樂山的書店比較大氣,這和人文環境有很大的關系。走在安靜的店里,在書架前慢行,尋找自己喜愛的書,這是一種享受。在書店旁的一家小店,我買下了這對“老夫妻”,回來后,擺在書櫥中顯眼的位置。
坐在藤椅中,手搭在扶手上,一縷陽光落在右手背上。老年斑像一粒種子,在陽光中孕育,多年后,繁生出更多的斑點。電視中很多的故事情節,需要年輕的演員化妝,去體驗老年的情景。有一天,他們真的老了,頭發花白,手上爬滿了老年斑的時候,只能用記憶去尋找年輕時的影子。我把手翻過來,手心盛滿陽光,一條條紋絡被陽光塞滿。很多人拿手紋預測自己的未來,而我用力地一攥,不知攥住了幾縷陽光。
我倚在藤椅的后背上,閉著眼睛在聽。陽光在掌中燃燒,發出灼熱的尖叫。
插圖:愛瑪·哈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