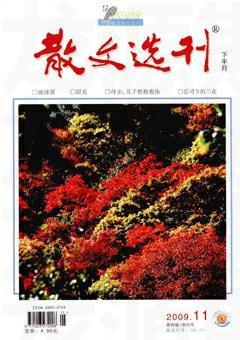春天,別為我哭泣
沈冬果
二姐夫出殯那天,父親還在醫院里接受心臟監控治療。我們兄妹幾個強壓悲痛扮出笑臉,輪流去醫院,想把二姐夫出車禍的噩耗對年邁的父母瞞天過海。
或許是一種親情感應,父親坐臥不安,本來已經有所好轉的心絞痛卻忽然頻繁發作。一向敏感的母親,總是盯著我眼睛問:松怎么沒來?松,是二姐的乳名,母親只有在情急時候才會喊我們姐妹的乳名。無論我怎樣搪塞,母親的眼睛里總是充溢著疑惑和不安。
老父老母做夢都不會想到,在過去的幾天里,他們一向愛如親子的二女婿正全身插滿著管子躺在他們所住的病房大樓頂層搶救室,要依賴于呼吸機強行拉動他本是強健的心肺,才能夠維持那一點可憐的生命跡象。大姐召開了家庭會議,特意叮囑我們兄妹,無論如何都不能讓父母知道這件事,否則父親的心臟將不堪重負,后果可想而知。
幾天來,我們兄妹幾個在痛苦、焦慮與惶恐中煎熬著。外地上大學的外甥和外甥女兒日夜兼程地趕回來,看著病床上躺著的面部已浮腫變形了的他們親愛的老爸,外甥女一下子昏死過去,外甥兒雙手抱頭跪拜在床前……本該享受陽光般快樂生活的孩子們怎么能承受得了?這洶涌而至的悲傷會沖垮他們的。
無論醫生和親人們做出怎樣的努力,死神最終還是把忠厚善良的二姐夫給帶走了。
我詛咒著惡魔般的車禍。
一個人的死,從物種自然交替必然規律上來說,或許并不意味著是悲哀,但悲哀分配給了自己的親人,它足以把許多顆心刺痛。親人的消失,我們的世界的某一重要的部分也跟著消失了,感覺那一部分空蕩蕩的。
暮春的雨淚水般地灑落在家鄉大平原滾動的麥浪上,那流動的綠色像無邊的時光,正向遙遠的天邊漫延,時隱時現的墳塋在溽熱的光陰中讓人鼻子發酸。
我緊緊地擁抱著外甥女顫栗著的瘦弱身體,用我的臉撫愛著她的臉,竭盡全力不讓她再次昏厥。送葬的隊伍緩緩前行,女賓們按規矩被截留在離開家園的第一個岔路口處。雨下得很細很密,它在把人間的離別愁緒浸透在這個春天的盡頭。二姐夫同族的姐妹們在雨水里哭天蹌地,善良的圍觀人都在憐惜地抹眼淚。
只有我擁著外甥女呆呆地站著。外甥女一直沒有眼淚,她年輕的臉毫無表情,眼睛緊盯著緩緩遠去的棺木,所有哭聲匯成的洪流都沒有使她動容,她出奇地平靜讓我感到害怕。
或許外甥女真正地第一次看懂了死亡,明白了生存的意義?不然在送葬隊伍最終消失在紙片漫天飛舞的那一刻,她怎么會突然堅定地轉過身來,挽著我的胳膊說:“小姨,我沒事了,咱們回去勸勸我媽媽吧!”
在料理完二姐夫的后事,賓客們都散盡了的時候,二姐忽然無所顧及地大哭起來,哭得很凄慘、很無助,誰也勸止不了。哭完之后,她就開始變得目光呆滯,神情恍惚,高聲大笑。
我明白二姐心中的悲涼,她在愛人忽然消失的世界里感到了孤立無援,知道了從今以后獨自看護自己是多么地困難。我們沒有打擾二姐,哥哥說,都別擔心,她壓抑這么多天了,想怎么釋放就讓她怎么釋放吧。
二姐很堅強,她終于把沉重卸載在對生活的責任和信念之上了。在孩子們面前,她收斂了自己。在給醫院里的父母親打電話時,她流著淚笑著說話。
這是怎樣的一種讓人倍受折磨的欺騙啊。
在二姐夫死后的一個禮拜,父母親終于知道了這件事情,是同鄉的大伯去醫院看望父親時不經意間說出來的,當時我們兄妹幾個都不在旁邊。大伯走后,母親就偷偷地哭著,挨個給我們打電話。在第一時間里,我們兄妹六個很快聚到了醫院里,聚在父母親的身邊。接下來,卻是父親的可怕沉默。他躺在病床上,面向墻壁,蜷縮著蒼老身軀,一句話都不跟我們說。母親在旁邊無聲地流著眼淚。二姐緊緊抱著母親的肩膀,輕輕撫著母親的白發,替她擦著臉頰上的淚水……
一縷陽光穿過窗外那棵香樟樹茂盛的枝葉,透過窗玻璃直射到父親的病床上,本來陰冷的病房內豁然明朗溫暖起來。這時父親慢慢坐起身,平靜而慈愛地看著我們說:“把窗戶打開吧!”
窗外,那棵春天的橡樟樹綠葉青枝,陽光稀釋了它昨夜風雨落葉時的痛楚,新葉間一簇簇細碎的花朵彼此支撐著,在陽光下努力地開出燦然,開出生機,虔誠地開出對生命的尊重和對健康平安的渴望,溫柔而繁盛。
春天,別為我哭泣,這一切都比想象中的要好。
責任編輯:黃艷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