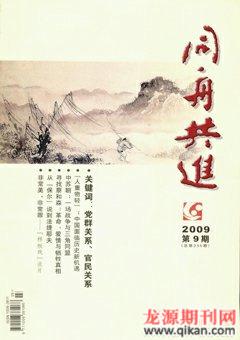如何對“錢”和“官”形成有效制約
鄭永年
很多跡象表明,當今社會沖突已深入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這些年來,無論官方還是民間,人們關注的大都是群體性事件,且把目光聚集在主要沖突者即“官”和“民”身上。但與此同時絕不能忽視引發沖突的導火索——“錢”。所以,本文想把“官民沖突”拓深一層,從權、錢、民也就是權力、資本和老百姓之間的對立來理解當前的社會沖突。
官民沖突的背后是什么
首先應當認識到,當下權、錢、民的對立狀態已相當突出。民和“錢”的對立已有很多年了。最近杭州富家子弟飆車撞死大學畢業生引起民憤,非常形象地說明了這一點。類似的案例可說是多年前“寶馬事件”的延續。在民與“錢”的對立中,“錢”成了社會非正義的代名詞。
民與官對立的例子更多。湖北省巴東縣一名鄉鎮官員在娛樂場所被女服務員刺死,社會情緒普遍表現為對女服務員的支持。早些時候上海的楊佳案也有類似情形。無論民與“錢”的對立還是民與官的對立,在這些案例中都表現出強烈的民憤,這是一種積累很久、濃縮了的集體憤怒。 很顯然,這種民憤如果不能及時化解,就可能演變為集體行動的動力。很多群體性事件的背后就是這種集體憤怒。
如何理解這種現象?筆者已在《基層社會的政治生態令人憂慮》(載《同舟共進》2009年第7期)一文中討論過官與民的對立是如何形成的。簡單地說,當政府不能履行政府職能,不能為民眾提供安全和社會正義時,民和官的緊張關系就會出現。尤其當政府本身成為社會不安全和非正義的根源時,民與官的沖突隨時可能爆發。
民與“錢”的緊張和沖突同樣不能忽視。人們往往簡單地以社會的“仇富”或“絕對平均主義”心態解釋兩者的沖突。但很顯然,這種解釋抱有太多偏見,過分站在“錢”的立場上說話。
中國人并不一定是“仇富”的、“平均主義”的。民和“錢”的沖突是兩者間失去平衡的產物。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提倡“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中國社會普遍接受這一政策導向。在這一政策的指引下,相當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但這并沒有導致人們的“仇富”心理,因為當時大多數人的經濟狀況也在不斷好轉。
現在的情形則完全不同,收入差異越來越大。經濟的高速發展不僅沒有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而且相當部分人陷入貧困狀態,絕對貧困的人數也在增多。 一些農村居民貧困,一些城市居民也已淪為貧困一族。更為嚴重的是,當先富者占據了制度的制高點后,就成了既得利益者,開始變得保守,排斥后來者。這樣一來,受“錢”操縱的市場(如股票和房地產市場等)便成為轉移社會財富的機制。
權(公共權力)的存在本來就是為了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和社會正義。但當權成為錢的俘虜時,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公共秩序、安全和社會正義就蕩然無存了。這樣,民必然起來為自己的生存和發展而抗爭。
知識階層的角色及其力量的削弱
那么,如何化解官、民、“錢”的不正常關系?不同國家、不同制度形態有不同的辦法。
從中國本身的歷史經驗和現狀看,最主要的是要處理好官與民的關系。在傳統中國,“官”的范疇又可分為“帝”和“官”,即皇權和官僚階層。在今天,這種分類表現在作為決策者的上層領導和作為政策執行者的官員及其官方機構。
歷史上也有“大戶”的概念,相當于現在的“富人”、“資本”或本文所說的“錢”。這樣中國社會就至少有四個群體,即作為決策者的領導者、作為決策執行者的官員、作為資本擁有者的富人和作為社會大多數的民眾。
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官僚和資本也就是權和錢的結合。這種結合不僅產生了上述官與民、“錢”與民之間的沖突,而且也在促使官僚、資本和決策者之間產生矛盾和沖突。
很顯然,整個政權的基礎并非“錢”和“官”,而在于“民”。從本質上說,“官員”和“錢”實際上只是領導者治理國家的工具和手段。這些不可或缺,因為社會的治理并非領導者和民之間面對面的關系。但現在的問題是,無論“官”還是“錢”,都異化了自身的本質,各自根據自身的需要和“民”發生關系,“民”成了被主宰的對象。 或者說,決策者的權力實際上為“錢”和“官”所攫取,執行政策的工具成了實際上的決策者和實施者。這同時也說明了,決策者本身和“民”失去了直接聯系。
在中國的傳統中,文人或知識階層在解決官民矛盾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文人居于社會和皇權之間,既非完全屬于社會力量,也不完全是皇權的代言人。在儒家的傳統里,當文人作為皇權的一部分時,就要為社會著想;作為社會的一部分時,就要為皇權著想。這樣就在皇權和社會之間產生了一個中間地帶,很多問題就是在中間地帶消化掉的。在基層社會,文人甚至完全代替政府治理地方,為皇權效力。這就是傳統紳士階層的作用。天高皇帝遠,紳士階層的存在使得傳統中國社會的自治成為可能。
但同時,這也意味著文人和皇權之間存在一定的張力或矛盾。歷史上,如果文人被視為挑戰皇權或公開站到對立面,皇權就會用強力壓制文人階層。但也有很多時候,文人和皇帝共享權力。如果兩者之間能夠保持一種均衡,那么社會和政權就處于穩定狀態。當皇權把文人徹底邊緣化的時候,社會穩定甚至政權的穩定就成為大問題。
經過“文革”等政治運動,中國傳統文人階層幾乎消失殆盡。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文人階層再度活躍。但1990年代以來,通過政治或經濟手段,文人階層很快被容納進政權體系,傳統文人和政權之間的“張力”或者“反對”成分被有效地消化掉了。
決策者如何對“錢”和“官”形成有效制約
在知識階層力量消減的情況下,想依靠它們形成有效的緩沖地帶已不太可能。辦法只能重新從社會上找。就是說,決策者必須通過依靠“民”的力量重新獲得群體關系的均衡。這就是筆者多次討論過的從國家向社會分權。在過去30年間,國家向官員分權、向資本分權,但如今在官僚坐大、資本坐大的情況下,要節制資本、節制官僚,就要向社會分權。如果不向社會分權,決策者很難控制官僚和資本。
如何賦權于社會?不外乎兩種方法。一是給予社會更大的空間,主要是利益表達和利益聚集的空間。 二是確立社會參與決策過程的制度機制。(應當指出的是,在這兩方面,目前的趨勢是向“錢”傾斜的)
換句話說,決策者和“民”的聯盟是政治改革的關鍵。沒有“民”的支持,決策者本身很難對“錢”和“官”形成有效制約,尤其是在后兩者已經結盟的情況下。
目前的官民沖突如果繼續下去,最終受害的不僅是民,而且將是整個政權。決策者若不能與民結成聯盟,那么民本身可能成為變革的唯一主體——尤其當民處于非組織狀態時,會表現出暴力性。這在中外歷史上屢見不鮮。
在任何社會,各社會群體間都會存在著一定的張力,就是說它們之間處于一種非均衡狀態。一定的張力屬于必然,也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但如果不能通過改革達到新的均衡,社會就會失去和諧,穩定將受到嚴峻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