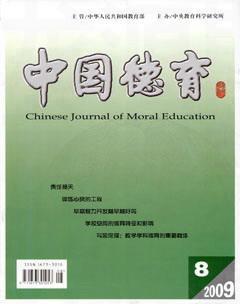道德是幽靈
畢世響
道德是幽靈
作為一個人,你覺得高尚嗎?作為一個人,你覺得光榮嗎?作為一個人,你感受到尊嚴沒有?德育在“做人”這個意義上,應該理解為“做一個高尚的人,做一個光榮的人,做一個有尊嚴的人”。或者,使每個人都感受到人的高尚、光榮與尊嚴。我們這個世界使人喪失尊嚴的遭遇太多了,不使人感到高尚和光榮的境遇太多了,也許會覺得個人和整個人類,是和我們一起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一切生物之中最殘忍的、最卑鄙的、最下流無恥的,我們簡直就生活在一個最不道德的世界之中。似乎人類沒有任何希望,沒有任何可以值得驕傲的。然而,我們無法否認個人和人類所創造的文明,否則,人類社會早已毀滅。是什么把人類社會支撐到現在以至將來?無疑,那就是人類的尊嚴,人類在罪惡面前永遠不會倒下,永遠不會喪失靈魂的圣潔;人類會迷失,卻永遠不能否認道德對個人和人類的守望,道德既像白晝的太陽,又像夜晚的星空,照耀著我們,使我們處于光明的智慧之中:人類社會的冷漠,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扭曲了,我們卻不能否認人身上的脈脈情愫,人會為自己流淚。更會為他人流淚,也會為花草樹木、泥土石頭流淚。個人生活在人類的情愫之中,沒有整個人類情愫的支撐,個人不能生存;人性有極其陰暗的內涵,卻不能否認個人和人類的尊嚴,不能否認人性的燦爛,人性的偉岸。人之為人就在于人的倫理與道德,人類的墮落,最終是道德的墮落;人類的消亡,也最終因為道德原因而消亡。唯有道德才能夠挽救人類,個人亦復如是。理性的冷凝與感性的激蕩,化為道德的性情,唯有道德才能協調理性與感性。人類的一切思想都來自道德,人類的一切思想本身也都是道德思想,一切教育在歸根結底的意義上是道德教育。
道德實在是一個幽靈,一個具有溫暖與冷酷、高尚與卑下二重性的幽靈,它既被人頂在頭上膜拜,又被人踩在腳下作踐,還被人吞吐于口舌之間,需要它的時候說它的好話,不需要它的時候說它的壞話。人類的歷史到底是見證人類高尚的歷史,還是見證人類卑下的歷史?似乎既是見證人類高尚的歷史,也是見證人類卑下的歷史。
人類的一切言行都是矛盾,譬如,人類現在擁有的核武器,可以把地球毀滅幾十次,也就是把人類毀滅于一瞬間。可是,人類還在拼命地活著——人類的一切作為都是為了能夠活著。現實就是這樣:人類這邊要毀滅人類,踐踏人類的尊嚴,那邊要活著,而且要活出人類的尊嚴。正是由于人類在自己的不道德行為中,更加感受到人類道德的尊嚴。
德育的吊詭
道德是介于“活著”與“死亡”之間的幽靈,道德教育實際上是教人知道你到底是庸人還是哲人,或者,你到底愿意做庸人還是做哲人,你到底是“做他人”還是“做自己”。實際上,庸人和哲人之間沒有鴻溝,孔子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孟子·告子下》成為庸人還是成為哲人,既取決于人先天的稟賦,更取決于后天的教化,人要有向善之心,才有向善之人。那么,道德的先驗與個人的道德自覺,是德育的根本基礎所在。
“德育”的倫理學基礎正是這樣的吊詭。——最終使德育也吊詭起來了。德育尷尬的根源在于道德本身的二重性,又在于人們對道德既敬畏又輕蔑的吊詭——一個人具有高尚的德行,不能保證他具有崇高的社會地位,也不能保證他能夠過上優裕的物質生活,相反,歷史上多少道德高人都是清貧之士。“德育”評價為優秀的中學生,不能保證他(她)考上大學,“德育”評價為優秀的大學生(包括研究生),不能保證他(她)能夠獲得社會地位。實在的,無論對人進行什么樣的道德教育,一個人一般也不會去違反道德,實際上,一個人一般也不刻意地去做一個道德君子。在道德上,一般的人只求做一個既不被社會表揚的人,也不去做一個被社會批評的人。這也說明,一般的人頭腦中有某種道德的先驗觀念,這個先驗觀念保證人不會無緣無故地行惡;這個世界上絕大多數人都死了,因為他們的活著除了具有“活著”的社會意義以外——社會是由人群組成的,沒有其它任何文明意義。他們只是重復前人的“活著”,沒有“自己的活著”,像咀嚼被前人咀嚼了幾萬遍的甘蔗渣一樣。在這個意義上說,這個世界是庸人的世界,他們把持著世俗的活著。庸人有沒有道德素養,他們都翻不了天,對庸人進行道德教育,說不定還是對道德的褻瀆呢;真正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是鳳毛麟角,他們的“活著”,是“自己的活著”,是“做自己”,他們的“做人”是“做自己”。盡管他們的思想也是來自前人,但他們是活得有思想、有境界的人。在這個意義上說,這個世界是哲人的世界,因為世界的思想就是那么幾個人的思想,他們引領著人類,他們是人類的道德老師。
德育的意義并不被社會所完全了解,即使道德學者自_己也對“道德”和“德育”懷抱琵琶,另有別談。“道德”或者“德育”似乎是一個不能隨便說話的危險領域。在去年四川大地震中“涌現”出來的新聞人物范美忠老師的作為,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一個刺撓話題。范老師卻使道德專家們(包括我自己)在輿論權和道德責任面前“集體投降”“集體不作為”或者“集體失語”了。雖然“沉默”也是一種話語權,也是一種態度,專家們都知道范老師是因言獲罪,如果他不把自己的話說出來,他哪里可能成為眾矢之的呢?專家們不愿意成為眾矢之的,沉默是最好的道德保守主義。那么多的倫理學專家和德育學專家,沒有公開出來評價范老師的,盡管大家在私下里對范老師都有自己的道德理論——專家們自然知道道德不僅僅是私下之事,更是光天化日之事。我在課堂上也對范老師有我的說法,我卻沒有在我的文章中公開評價范老師,我也沒有在網絡上公開評價范老師,我很希望有范老師這樣一個“人”做我的朋友,我把他作為和我一樣的人、一樣的同行來尊敬。以我的看法,范老師成為一個使學者無法“下手”,或者說無法“置喙”的道德人物。學者們并不是沒有看法,他們,或者說“我們”,都是謹小慎微的人兒,“我們”懼怕的是道德本身,更懼怕的是民眾和社會對“我們”道德觀的批評——這個批評可不是“我們”的學生對老師的委婉的批評,而是毫無情面的批評,甚至是人身攻擊,更甚者,是政府對“我們”言論的批評。
德育的遭遇
德育往往受到許多批評,批評德育的人卻未必知道德育受批評的根本原因在于道德的幽靈氣質。也許正因為道德和德育本身都是一個吊詭領域,又使得道德學者自覺或者不自覺地在是非問題面前,采取了保守主義的立場——保守主義
本身就是一種道德立場。
十年前,我剛念博士,我的專業是教育學原理,方向是德育學或叫德育原理。寒假和幾個朋友(他們都是大學畢業生)在一起吃飯,其中一個朋友(也是我的學生)問我博士研究什么方向,當他聽說我研究“德育”的時候,脫口而出:“德育也有博士啊?”他把這句話就著一口菜吞到肚子里去了,沒有再說下去,飯桌上的其他幾位朋友都不再和我“研究德育”,只“研究飯菜”了。我知道,實際上,他們還有更迷惑或者難聽的話要說,對著我這個老師,他的道德意識——對老師的尊重——使他不能或者不敢再說下去。還有一種可能,他不懂得“德育”是什么意思,因為他所想象的“德育”是另外一個意思。人家總認為“德育”非常難研究,或者認為,“德育”不屬于“正經的學術”,而是某種政治玩意兒。前一段時間和一位同事的老鄉,也是幾位大學教授,在一起吃飯,我又遭遇到這樣的“尷尬”。初次見面,相互除了請教“尊姓大名”以外,也要請教“研究什么”,他們一聽說我是研究“德育”的,總有一種異樣的詫異;實際上,我在念博士的時候,外學院給我上課的一位教授(也是博士研究生導師),聽說我們是“德育”博士生時,居然驚詫得花容失色;即使教育理論專家,也覺得“德育”是一個相當難伺候的領域:“迄今為止,我一直想‘搞德育卻又不敢‘搞德育。”
現在,我的一些大學生“老同年”偶爾還會拿我的專業開玩笑,說,“畢教授是專門給人洗腦的”。德育等于洗腦?我倒是從來沒有這么研究過德育,也從來沒有想到把德育抬舉到這么高的地位;其實,我的教育學同事也多不懂得“德育”。要么覺得德育太高深了,要么覺得德育古怪,要么覺得德育玄奧,要么覺得德育嚴肅。似乎“德育”領域以外的人根本就不會把德育看成一門生動的、活潑的、燦爛的、親切的、深刻的學問,更不知道德育和整個人類文明相表里。一般的人不能理解“德育所涉及的是人的靈魂、精神中最深沉的部分”(魯潔語)的含義;中小學老師在我們學院念教育碩士,我給他們上德育學課程,他們說“第一次接觸德育課,簡直不可思議,德育居然是這樣的!中小學德育不是這樣的”。他們從來就沒有想到德育和倫理學有什么關系,德育和哲學、文化學、社會學有什么關系,也許是第一次聽說“倫理學”這樣的學科。他們很難把“德育”和當下中國社會歷史上最大的文明轉型——從農耕文明到工業文明的轉型——聯系在一起。因為“一提起學校德育往往就是對學生和老師的某種意義的管束,學校德育到頭來往往是把德性給閹割了,至少是把德性縮小了。本來德性是人類博大精深的文化,本來就應該用這樣的文化來養育學生的德性,但在學校德育之中,只是用一些‘守則‘規則之類的‘yes‘no來塑造學生,使德育變成一個否定過程:不許這樣,不許那樣,如:‘不遲到,不早退,不曠課,不說謊話,不隨地吐痰,不欺弱小,不喝酒,不隨地吐痰,不罵人,不打架……”。
德育確實有幾個層次,大學教育理論界的德育老師所伺候的德育,以理論為研究,更多的是在形而上的意義上說話。教育學領域“德育”的國家學會全稱是“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學分會德育(理)論專業委員會”;中小學德育是以教育教學中的“問題”為實踐的,更多的是在形而下的意義上說話。如中學“德育處”幾乎成為一個“處理問題”的機構,學生上課搗亂會被科任教師送到“德育處”去處理,學生和老師鬧出矛盾也由“德育處”處理。難怪“德育”在中小學成為一個“問題”。
德育與道德精神
在這個網絡民主時代,網絡言論以“民間社會正義”身份,對社會事件說話。那種說話多是熱情仗義立場,會使人想到“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示君,誰有不平事?”那樣的古道俠義心腸,也會感到積淀在民間的燕趙慷慨悲歌精神,似乎荊軻重生,聶政再世,這種極其寶貴的仁義高風,代表的是民間的道德精神。仔細分析一下,古代俠義之士多是“酬恩知遇”和“士為知己者死”的動機使然,被后世史家贊為“天壤間第一種激烈人”。當代網絡義士,不為名,不為利,乃社會正義使然,使人感動,使人肅然起敬,使人感到社會正義的激昂。
然而,如果仔細分析一下,當代網絡義士的說話,往往缺乏某種哲學的理性立場。譬如,網友對范美忠老師的行為以“罵”為說,這就喪失了正義。另外,網友對事件說話,多是一哄而上,像一陣旋風旋過來,勢頭很快就過去,又把興趣旋到另外的事件上去了,當時無論多么嚴重的事情,過不了多久,就被網友們忘記了。這種“打游擊”式的正義,為網友們掙得一個惡名:“網絡暴民”。
道德需要熱情,更需要理性。我們的生活中往往會出現這樣的吊詭:以獨裁的民主壓制民主的獨裁,和以民主的獨裁壓制獨裁的民主。在“文化大革命”中,人們往往不許“反動派”說話,“反動派”只能老老實實地低頭認罪,那就是獨裁的民主壓制民主的獨裁。在這個網絡時代,我們的思維仍然是這樣。最近文藝界有人揭露出“文化大革命”中某些知識分子被另外一些知識分子告密的事實。有人發表文章,認為不應該揭露這樣的事實,因為怕被后人把那些知識分子說成“沒有好人”“沒一個是干凈的”。后人為什么沒有權力知道那段歷史?知識分子為什么不能“現形”?今天,某些具有崇高社會地位的人,如國家官員和高級知識分子,往往以自己的地位來為自己的某種利益發表在大眾看來是“荒謬”的言論。一些民眾不希望媒體把他們的言論發表出來,更不希望媒體叫他們出來說話,這就是以民主的獨裁壓制獨裁的民主。因為民主社會是人人都能夠說話的社會,即使他的言論是錯誤的、荒謬的,也不能剝奪他說話的權力。這就是民主時代的道德精神。
知識分子應該是社會的良心,是天與人之間的使者,是代天立言的人,什么時候能夠正視自己的靈魂?當我們把社會的不道德歸為某種社會責任的時候,有沒有想到自己在社會不道德中的責任?一個不反思自己靈魂的民族,一個害怕自己靈魂的知識分子,還配講道德嗎?還能夠教育人嗎?人類在自己的罪惡面前不會倒下,面對過去的罪惡、當下的罪惡和未來的罪惡,我們的靈魂應該更加堅強,我們過去、現在和將來都處于傷心之中,但我們永遠不能傷了我們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