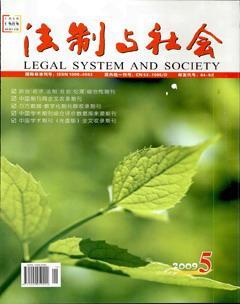淺析發現權的客體
陳榮飛
摘要陜西省西安市臨潼區下和村的楊新滿、楊培炎、楊全義三位農民,為贏得兵馬俑發現人的“名分”,代表9名發現人將“關于‘秦兵馬俑發現人資格認定的申請報告”交給了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要求該館頒發證書、確認他們的“發現權”。對文物主張確認發現權的案例在全國尚屬首次,并直擊我國法律“盲點”,其申請確認兵馬俑“發現權”的意義,無疑超出了“確認”本身。對于是否應該向楊新滿等九人頒發證書、確認他們的“發現權”,各方說法不一,本文認為要正確處理好以上問題,歸根結底,就是要確定發現權的客體。
關鍵詞國家自然科學獎發現權法律關系
中圖分類號:D923.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0592(2009)05-013-02
法律關系的客體又稱權利客體,是權利主體的權利與義務所指向的對象。而發現權,通說認為,是指自然科學發現人依法對其自然科學發現成果所享有的權利,包括領取榮譽證書、獎章和獎金的權利。認為發現權的客體應該是自然科學發現,而不包括社會科學發現。這也得到我國有關立法的認可,如1999年5月23日國務院發布的《國家科學技術獎勵條例》第九條第一款:“國家自然科學獎授予在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中闡明自然現象、特征和規律,做出重大科學發現的公民。”
關于發現權,我國《民法通則》雖然有所規定,然而其規定的比較籠統,并沒有具體規定哪些發現才能授予發現權,也不能確定發現是否僅指自然科學發現,而不包括礦藏的發現,古生物化石、古文物發掘,地理、動植物的發現等。發現權,作為一項獨立的民事法律制度,最早見于前蘇聯,其于1947年確立了科學發現登記制,并于1961年的《蘇聯和各加盟共和國民事立法綱要》以及各加盟共和國后來的民法典都專章規定了“發現權”。在國際立法方面,1967年簽訂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所劃分的知識產權則包括科學發現權等,該公約明確規定了發現權的客體為科學發現。由此,多數學者認為,我國發現權的客體應該是科學發現,而不包括古文物等發現。支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另有一個理由:如果將文物發現權授予個人,那么發現權之后必然聯系到所有權,這樣就必然侵犯國家在文物上的處分權,造成對國家權利的侵犯。
筆者認為,發現權作為一種民事權利,只要法律沒有明確禁止,而其實施又不會損害國家、集體和他人的利益,權利人就可以而且應該享有這種權利,甚至在合理范圍內的擴大化。因為法律權利不過是對事實上的權利和應然的權利的一種認可,法律本身的不確定性和模糊性同樣也表明其不可能對權利作出周延的規定。因而,在司法實踐中,權利保護的范圍實際上要比法律的明確規定更為寬范。如果說,從社會發展的總態勢看,法律必然擴大權利保護的范圍,因為生生不息的權利涌流是法律權利擴張的重要條件和前提,那么,將應受保護的權利局限于法律的明確規定,就顯得過于機械,缺乏法治所必須的靈活性。另外,1999年5月23日國務院頒發的《國家科學技術獎勵條例》也只是確定自然科學發現是發現權的客體,但并沒有規定它是唯一客體。因此,從法理上和邏輯上來講,我國發現權的客體應作廣義的理解,不僅包括自然科學發現,而且包括古文物等發掘。所以,發生在陜西西安申請確認發現權的事件中,有關部門應該授予楊新滿等9位農民發現權,這主要有以下幾個理由:
第一、授予發現人的文物發現權不會損害文物所有權。對于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所有權,理論上主要有兩種觀點:1.無主的或所有人不明的具有學術、藝術、考古價值的自然物或文物歸國家所有。我國大陸、臺灣地區,瑞士等國家的立法持這種觀點,如《民法通則》第七十九條第一款規定:“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隱藏物歸國家所有,接受單位應當對上繳的單位和個人給予表揚和獎勵。”《文物保護法》第四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地下、內水和領海中遺存的一切文物,屬于國家所有。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石窟等屬于國家所有。……”《瑞士民法典》第七百二十四條第一款規定:“學術價值極高的無主的自然物或文物,一經發現,歸發現地所在州所有。”持此觀點立法的國家或地區,對無主的或所有人不明的文物享有占有、使用、收益、處分的權利,而占有“指對于物的事實上的控制與支配”,在物權中極為重要,具有推定與公示物權的效力。然而,發現權作為知識產權的一種權利,不能具有所有權的全部權能,尤其權利人不能對權利標的實施“占有”。另外,物權作為對物進行支配的權力,其排他性直接指向物本身及對物的控制,因而對物權的侵害就表現為對客體物的侵奪或損壞。但發現權,是直接對客體物利益進行配置的法律工具,其本身并不涉及對載體物的配置。因此,授予文物發現人的發現權,對國家享有文物所有權并不會產生侵害的事實。另一方面,國家享有文物的所有權,還要依靠發現人的發現,如果沒有發現人的發現文物的事實,國家也不可能存在對文物的占有,更不用談所有權。所以,授予發現權,能鼓勵發現人發現文物并及時上交的積極性,以致國家能實際占有更多的文物。2.無主的或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歸發現人所有。德國、日本等國的立法持這種觀點,如《德國民法典》第九百五十八條第一款規定:“自主占有無主的動產的人,取得此物的所有權。”《日本民法典》第二百四十一條規定:“關于埋藏物,依特別法規定進行公告后六個月內,其所有人不明時,發現者取得其所有權。……”按照此種觀點,如果授予文物發現人的發現權,則發現權與所有權的權利主體合二為一,根本不可能產生誰侵害誰的問題。另外,發現權與所有權保護權利人的側重點又有所不同,發現權保護的重點是精神方面的權利,而所有權保護的重點是財產方面的權利,因此,發現權的設立對維護權利主體各方面的權益是必要的,在司法理論和司法實踐中是不可缺少的。總之,不管發現權與所有權的權利主體是否同一,授予文物發現人的發現權是不會損害所有權的。
第二、授予發現人的文物發現權,是權利、義務相一致原則的需要。從法理上來說,一方面,在任何一種法律關系中,權利人享受權利依賴于義務人承擔義務,義務人如果不承擔義務,權利人不可能享受權利,權利與義務表現的是同一行為,對一方當事人來講是權利,對另一方來講是義務。因此,就權利與義務的實質內容——行為來講,二者是統一的。權利與義務所指向的對象——客體,也是同一的。另一方面,不能一方只享受權利不承擔義務,另一方只承擔義務不享受權利。具體地說,任何權利都意味著權利人在法律所允許的范圍內能做一定的行為,使自己的行為不超出這個范圍是權利人的義務;而任何義務也都意味著義務人在法律要求的范圍內應做(下轉第15頁)(上接第13頁)一定的行為,超出這個范圍則屬于義務人的自由,即義務人的權利。因此,權利人在行使自己權利的時候必須承擔一定的義務,而義務人在履行自己義務時也同時享受一定的權利。我國《文物保護法》規定,一切機關、組織和個人都有保護國家文物的義務,發現文物應當及時上報或上交。發現人有上述的義務,就應當有相應的權利來維護自己的權益,否則即違反了法理上的權利義務一致性原則。因而,要維護文物發現人的利益,在法律表現形式上就應該授予發現人的發現權,這不僅維護發現人精神方面的權益,而且維護了物質方面的利益。
第三、授予發現人的文物發現權,是我國制訂一部開放型民法典的需要。我國民法典已經正式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審議,這樣,民法典的草案就正式登上立法舞臺,引起全社會的普遍關注,而制訂一部開放型的還是封閉型的民法典,也成為學者討論的重點。筆者認為,我國應當制訂一部開放型的民法典,因為社會經濟生活是非常活躍的,它不應當受法律的束縛和阻礙,法律應當給它更大的未來空間和余地。同時,一部開放型民法典的靈魂就是民事權利的開放,不宜封閉,否則就充滿著危險,而權利的開放,不僅包括權利類型的開放,還包括權利內容的開放,對于權利主體民事活動中的行為,法律沒有禁止的都是許可的。因為權利作為社會主體自主性地反映,除了有適當的理由,則不得加以限定。從現代法治的原則看,法無明文禁止的行為,就應該是人們自由活動的領域。換言之,法律所確定的權利界限應該是法律所禁止的行為。雖然,法律明確規定的權利屬于國家所鼓勵的,但并不意味著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就不予以保護和提倡。因此,授予發現人的文物發現權,是與我國制訂開放型的民法典相適應的。
第四、授予發現人的文物發現權,是時代發展的需要。現在的社會是以個人為本的社會,它以保護個人利益為主要任務,當然,這并不是不對社會利益進行保護,更不能說是放縱個人對社會利益進行損害,只是說在私法主體沒有損害社會利益及他人利益的場合,法律應對私法主體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進行鼓勵和保護。換言之,個人利益是第一位的,社會利益是第二位的,“個人(正當)利益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應沒有任何附加條件,即使在所謂的社會利益面前也應該是個人正當利益優先”。因此,任何法律制度的制訂、修改、解釋都應以個人為出發點,反映社會生活的實際需要,那些能夠滿足主體利益并得到國家法律確認和保護的客觀現象,都應成為法律關系的客體,成為主體的權利和義務所指向的對象。關于文物發現人的權益,《文物保護法》第二十九條規定:“有下列事跡的單位和個人,由國家給予適當的精神鼓勵或者物資獎勵:…(四)發現文物及時上報或者上交,使文物得到保護的;…”雖然立法中并沒有標明“發現權”的字樣,但發現人的精神和物資方面的利益在法學理論上就化成一種權利,而這種權利主要是針對發現文物并及時上報或上交的行為,由此,從法律術語上講應該稱之為發現權。而且,我國也逐漸把發現權的目光慢慢移到自然科學發現以外的東西,如北京公證了首例自然景觀發現權,這也從另一方面反映了隨著社會文明的不斷進步,人們法律意識日益增強,用法律維護自己權益的觀念日益深入。因此,社會生活的現狀以及時代發展的需要,也要求我們的立法、司法、執法觀念不斷更新,以致于能更好地維護人們的權益,這迫使我們應該授予發現人的文物發現權。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我國發現權的客體不僅包括自然科學發現,而且應該包括有重大意義和價值的非科學發現,如文物的發掘,這不僅是以人為本的社會需要,而且是新世紀對我們提出的要求。我國的民法典正在制訂,而在為建設一個豐富和令人滿意的文明的努力奮斗過程中,法律制度發揮著重要而不可缺少的作用,它在某些基本的生活條件方面為個人創制并維續了一個安全領域,并促進潛存于社會體中的極具創造力和生命力的力量流入建設性的渠道。我們期望民法典的出臺,對發現權有明確、具體的規定,以完善相關的法律,并增強其操作性,把包含有重大意義和價值的非科學發現,如古文物發掘等,納入其范圍,這不僅有利于保護發現人的權益,更有利于文物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