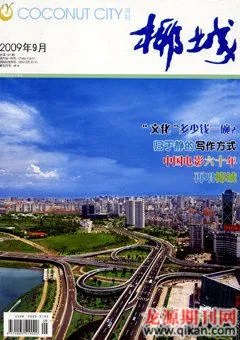歸于靜的寫作方式
2009-06-04 10:32:04葛水平
椰城
2009年9期
關鍵詞:生活
葛水平
我無法對當下眾多的寫作方式去思考,我只是我,熱眼冷心。
我的情感的那一根結一直系在鄉村。
在鄉村,大片小片的樹林依然保持著季節特有的蒼黃;在鄉村,空氣就像濾出林間的泉水,透徹明亮;在鄉村,人的身體披滿了干細的黃土,幽曠出一種自在的潔凈;在鄉村,一顆焦慮煩躁之心會歸于平復。當我回到城市的時候,我旅途中的情感常常無從放置,我知道,當我有一天“弄不出東西來”的時候,我一定得置身于鄉村。
這是我歸于靜的一種寫作方式。
我在鄉村見到第一個移民到太行山的山東人,他說:“我的爺爺是大清國年間給人當挑夫走上太行山的,看到這地方好,有白饃吃,第二年回來,一頭挑著鍋碗家什,一頭挑著我的奶奶,出門的時候是大清國,走到邯鄲成了民國。我爺爺說,這塊裸露的土地啊,變化快!”
越是變化快的日子,越需要耐性的去琢磨。
鄉村給我田園牧歌的情調和安謐寧靜的氣息。
天下事原本就是大地由之的,大地上裸露的可謂儀態萬千,因天象地貌演變而生息衍進的鄉村和她的人和事,便有了趣事,有了趣聞,有了進步的和諧的社會。鄉村是整個社會的縮影,整個社會得益于鄉村的人和事,而繁榮,而興盛。鄉村也是整個歷史苦難最為深重的體現,社會的疲勞和營養不良,體現在鄉村,是勞苦大眾的虛脫。鄉村活起來了,城市也就活了。鄉村和城市是多種藝術技法,她可以與城市比喻、聯想、對比、夸張,一個奇崛偉岸的社會,只有鄉村才能具象、多視角地、有聲有色地展現在世界面前,并告訴世界這個國家的生機勃勃!鄉村的人和事和物,可以縱觀歷史,因此,對于鄉村,我是不敢敷衍的。……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風流一代·經典文摘(2018年1期)2018-02-22 09:00:43
黨的生活(黑龍江)(2017年12期)2017-12-23 17:01:20
求學·文科版(2017年10期)2017-12-21 11:55:48
求學·理科版(2017年10期)2017-12-19 13:42:05
民生周刊(2017年19期)2017-10-25 07:16:27
特別文摘(2016年19期)2016-10-24 18:38:15
爆笑show(2016年3期)2016-06-17 18:33:39
37°女人(2016年5期)2016-05-06 19:44:06
爆笑show(2016年1期)2016-03-04 18:30:28
爆笑show(2015年6期)2015-08-13 01:4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