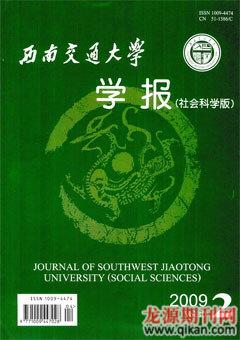魏晉南北朝人才思想中的雜家色彩分析
楊 民
關鍵詞:魏晉南北朝;《人物志》;《顏氏家訓》;雜家;名家;道家;儒家;法家
摘要:魏晉南北朝時期,兩漢定儒學為一尊的思想禁錮被突破,思想界儒、道、名、法諸種學說互相滲透,形成彼此會通的復雜面貌。《人物志》與《顏氏家訓》“不專為一家之言”,是魏晉南北朝思想領域中涉及人才問題的兩部極有特色的著作,其人才思想中均具有較濃的雜家色彩。但總體而言,《人物志》兼儒、名、法、道,儒為其道德指導原則,至于思想方法及內(nèi)容上則以名、法、道居多。《顏氏家訓》兼儒、名、道、佛,其中儒家是主流,其余則為女流。二書“兼綜駁雜”的雜家風格的形成,源于三個方面的因素,即其作者劉劭與顏之推的廣綜博學和對前人豐富思想遺產(chǎn)的繼承以及當時較為寬松的社會現(xiàn)實環(huán)境。《四庫全書總目》將二書列入雜家,確有其理由。
中圖分類號:G40-0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9-4474(2009)02-0044-06
《人物志》與《顏氏家訓》是魏晉南北朝思想領域中涉及人才問題的兩部極有特色的著作,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豐富的思想內(nèi)容。三國魏劉邵(約172~250)所著的《人物志》,是我國第一部人才研究專著,它由外及內(nèi)探討了人內(nèi)在品德、才智以及適宜任職的問題;南北朝后期顏之推(530~約591)所著的《顏氏家訓》一書,廣泛而深刻地論述了家庭教育中關于子女成才的問題,是一部對中國古代家庭教育有著較大影響的經(jīng)典著作。魏晉南北朝時期,兩漢定儒學為一尊的思想禁銅被突破,思想界儒、道、名、法諸種學說互相滲透,并形成彼此會通的復雜面貌。我們僅以《人物志》與《顏氏家訓》二書“不專為一家之言”的雜家思想內(nèi)容作為分析案例,借此觀察魏晉南北朝前后期人才思想觀念的大致變化情況。
一
《人物志》與《顏氏家訓》問世以來,歷代不少文獻在對二書進行收錄時,曾有過如下的區(qū)分和定位,見表1。
由表1可見,唐宋以來,學界對二書類別的認識并不是完全統(tǒng)一的,最后,我們看到清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將《人物志》和《顏氏家訓》均收列人雜家類書籍。《四庫全書》作為清代官方權威學術成果,它作此分類,理由何在?在此,我們有必要首先將《四庫全書總目》對二書所作的評語摘錄于下。
《四庫全書總目》評《人物志》云:
其書主于論辯人才,以外見之符,驗內(nèi)藏之器,分別流品,研析疑似,故《隋志》以下皆錄于名家。然所言究悉物情,而精核近理,視尹文之說兼陳黃、老、中、韓,公孫龍之說惟析堅白同異者,迥乎不同。蓋其學雖近乎名家,其理則弗乖于儒者也。
《四庫全書總目》評《顏氏家訓》云:
其書大抵于世故人情,深明利害,而能文之以經(jīng)訓。故唐志、宋志俱列之儒家。然其中《歸心》等篇,深明因果,不出當時好佛之習;又兼論字畫音訓,并考正典故,品第文藝,曼衍旁涉,不專為一家之言。今特退之雜家,從其類焉。
以上兩段評語將《人物志》與《顏氏家訓》的思想風格闡述得較為清楚,同時我們也能看出,清代學者仍承接了班固《漢書·藝文志》中關于雜家“兼儒、墨,合名、法”的界定,他們以“不專為一家之言”為標準,來衡量《人物志》與《顏氏家訓》的性質(zhì),應該說,這種衡量是有一定道理的。那么二書究竟有怎樣的雜家特色呢?下面便試將二書人才思想中帶有雜家“兼綜”色彩的具體內(nèi)容予以進一步辨正剝析。
(一)《人物志》與《顏氏家訓》中的儒家色彩
先秦諸子中孔子所創(chuàng)立的儒家,以注重血親人倫、道德修養(yǎng)的醇厚之風獨樹一幟并深刻影響后世。孔子一生,無論對自己還是對學生,都在努力培養(yǎng)仁與智(知)的人才必備素質(zhì),后來儒家便以“仁且智”來稱道孔子的人格理想。例如,孟子引子貢的話說:“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荀子亦言:“孔子仁知且不蔽。”在《人物志》與《顏氏家訓》人才思想中,同樣體現(xiàn)了儒家仁、智統(tǒng)一的內(nèi)容。
第一,二書均以仁為人才道德的核心。孔子貴“仁”,《論語》載樊遲問“仁”的內(nèi)涵,孔子曰:“愛人。”儒家強調(diào)仁愛是人本性的最高表現(xiàn),是人美德的最高概括。據(jù)此,劉邵提出“蓋人道之極,莫過愛敬”,將“愛敬”推舉到極高的地位。其次,劉邵以仁、義、禮、信作為道德的主要規(guī)范,強調(diào):“仁者,德之基也。義者,德之節(jié)也。禮者,德之文也。信者,德之固也。”顏之推則推崇“謙恭、禮讓、慎交、厚重”的道德原則,提出了“圣人之書,教人誠孝”的觀點。總之,劉邵、顏之推二人在其人才思想中,均力圖塑造仁為己任的完美人才道德素質(zhì)。
第二,二書均將智作為人才的重要素質(zhì)。孔子重視對人性的了解,他曾說:“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論語》載樊遲問“仁”,孔子曰:“愛人”。問“知”。孔子曰:“知人。”由此可知,孔子所強調(diào)的智,其主要功能之一便是認知人性的能力。在《人物志·序》中,劉邵聲稱自己遵循孔子對智的理解,他說:“訓六蔽,以戒偏材之失,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倥倥而無信,以明為似之難保。”另外,他又強調(diào):“智者,德之帥也。”這些都表明《人物志》在認知手段上所持有的儒家立場。
孔子認為認知的主體有先天素質(zhì)的差異,他說:“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顏之推據(jù)此發(fā)揮說:“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以此來說明其對先天智力素質(zhì)及后天努力的重視。
第三,針對“仁且知”(智)的理想人格培養(yǎng),孔子總結出“修己”的道德修養(yǎng)理論,這在二書中也有反映。劉邵在《人物志》中提出了“三優(yōu)三劣”的個人修養(yǎng)標準,并且提出切實可行的個人修養(yǎng)方法,即:“舉不敢越儀準,志不敢凌軌等,內(nèi)勤己以自濟,外謙讓以敬懼。”顏之推提倡的個人修養(yǎng)標準是:“君子處世,貴能克己復禮,濟時益物”;并且他主張通過學習古人“行道以利世”的方式來提高自己的道德水準,達到“修身利行”的效果。此外,二人都樹立了一些道德學習典范,提倡向古代圣賢如孔孟等人學習,希望以此將道德理想具體化,從而發(fā)揮儒家學說在社會道德意識和道德行為中的巨大教育和激勵作用。以上三個方面都表明儒家思想對劉邵、顏之推的熏染和二人對儒家理論肯定的一面。
(二)《人物志》與《顏氏家訓》中體現(xiàn)的其他色彩
1名家色彩
后人屢將《人物志》歸人名家,是因為它表現(xiàn)出濃厚的名家思想內(nèi)容及風格。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shù)。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考名家源流時認為名家出于禮官,其中心理論是提倡“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由于名學主要通過檢形定名來研討尊卑秩序、設官分職、任人以才等問題,因此同選才任官的關系極其密切。東漢以降名學的發(fā)展,一直圍繞著改革吏制及如何選擇吏
才這一中心問題來進行。
《人物志》作為人物品鑒方面的專著,體現(xiàn)出的名家色彩相當厚重,總結起來主要有如下幾方面。第一為觀人,劉邵主張根據(jù)骨相等生理特征觀人,故書中先有“九征”之說;其次注重觀察人的行為舉止,故書中又有“八觀”之論;他還主張更進一步觀察人之行事風格,書中稱為“五視”。第二為論才性。名家不同于儒家,他們不大講性情而多言才性,其關注的是才性同異、才性大小等辯題。《人物志》亦然,例如其《材理》篇說:“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猶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愚以為此非名也。”這是涉及人才能大小及其功用的討論。第三為重談論。名學強調(diào)觀人應察其言論,欲做官者必須注重言談之修飾。而劉邵亦相應提出了“三談”之法。總而言之,名家名實相符的思想,形成了《人物志》人才理論的重要特征。正如劉邵所說:“名非實,用之不效。故日:名猶口進,而實從事退。中情之人,名不副實,用之有效。故名由眾退,而實從事章。”另外,《人物志》在行文方面也體現(xiàn)了細致謹嚴的名家論證風格。
至于一些書目將《人物志》歸入法家,是因為名學與法學在思想內(nèi)容方面頗有相連之處。孔子曾言:“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先秦法家“貴刑名”,就是要按照名與實兩者相符的程度或情況進行賞罰。韓非子說:“人主將欲禁奸,則審合刑名。”韓非子又說:“據(jù)法直言,名刑相當。”賞罰功罪必須名實或言事相當,所以古人言刑名往往將二者并舉。《古今圖書集成》將《人物志》歸人法家著作,也有自己的道理。

“循名責實”的名家思想特色在《顏氏家訓》中亦有反映,其《名實》一篇集中代表了顏之推在人才思想上的名實觀。顏之推說:“名之與實,猶形之與影也。德藝周厚,則名必善焉;容色姝麗,則影必美焉。”他主張名實二者的高度統(tǒng)一,嚴厲批判了當時社會在人才教育中的虛偽浮華態(tài)度。第一,他反對高談闊論、不切實際的學風。例如他說:“吾見世中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有試用,多無所堪。”顏之推提倡人才培養(yǎng)應遵循學以致用的原則,反對玄學之士所標榜的清談習氣。他批評了王弼、何晏等十余名清談型人物,對他們“迂誕浮華、不涉世務”的行事態(tài)度表示反對。第二,他反對在人才識別中的某些先驗方法。例如,針對江南“抓周”的習俗,他認為人才先天決定論不可信,相反,二親的“無教”才有可能導致兒女無能。另外,他指出當時社會在人才識別中帶有“貴耳賤目,重遙輕近”的缺陷,這一點與劉邵主張“以目正耳”而不要“以耳敗目”的提法是完全一致的。顏之推頗為強調(diào)個人才能與地位之間的關系,認為過分看重個人的出身與門第,不利于識別和重用具有真才實學的人物。他在《名實》篇中將人分為上士、中士、下士三個等級,并且評議:“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他分析道:“忘名者,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福佑,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懼榮觀之不顯,非所以讓名也;竊名者,厚貌深奸,干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較為細致地表達了他對名實關系的看法。通過以上的總結和概括,可以看出《顏氏家訓》書中的一些觀點與名家理論有緊密聯(lián)系。
2道家色彩
《人物志》和《顏氏家訓》在人才思想方面還表現(xiàn)出對道家思想的吸收。歷史上的道家以超然和陰柔的態(tài)度來對待塵世的紛爭,二書中提倡的個人立身之道,即多向道家人生哲學學習而來。例如在《人物志·釋爭》篇中,劉邵認為一個人在處理人際關系時要持有不伐、不爭的處世原則,但這種態(tài)度并不是讓人一味地謙讓,相反,劉邵認為“不爭”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最終是要達到“大爭”的目的。因此劉邵引《老子》“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之語來論證自己的觀點,他進而引申道:“是故君子之求勝也,以推讓為利銳,以自修為棚櫓,靜則閉嘿泯之玄門,動則由恭順之通路。是以戰(zhàn)勝而爭不形,敵服而怨不構。”劉邵又言:“不伐者,伐之也。不爭者,爭之也。讓敵者,勝之也。下眾者,上之也。”《人物志》是一本鑒人之書,我們看到劉邵對老子道家之說相當欣賞。在劉邵眼中,謙虛禮讓,卑弱自持,不僅是人才自我完善的立身之道,更是人才立功的重要手段。
道家立身之道也體現(xiàn)在《顏氏家訓》中。古人關注的人生問題之一,是人生在世,受到無數(shù)外在束縛,如肌體之累、聲色之樂、利祿之欲、死生之懼。怎樣才能超越這些外在的束縛呢?對此,顏之推強調(diào):一是對物質(zhì)享受要適度,不可過于放縱。他說:“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唯在少欲知足,為立涯限爾。”二是在待人處世特別是涉足仕宦時,仍要堅持謙退守亨、持盈保泰的立身之道。例如:顏之推認為,作為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一個人只要“謙虛沖損”,自然“可以免害”。
《人物志》沒有涉及到宗教,《顏氏家訓》中則融合了宗教思想的某些成分。在《歸心》篇中,顏之推認為在人才道德培養(yǎng)上,佛學與儒學均有其教化功能,他嘗試將儒學的人才五常——仁、義、禮、智、信與佛學的五種禁限相比配。他說:“內(nèi)典初門,設五種禁;外典仁義禮智信,皆與之符。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可見顏之推試圖推動儒、釋二家合流,促使佛教內(nèi)容適合于儒家的倫理道德規(guī)范。
通過以上對《人物志》與《顏氏家訓》二書思想內(nèi)容的梳理和歸納,我們可以看出,二書在人才思想方面確實具有“兼綜駁雜”的雜家色彩。《四庫全書總目》將二書列入雜家,看來也確有其理由。總體而言,《人物志》兼儒、名、法、道,儒為其道德指導原則,至于思想方法及內(nèi)容上則以名、法、道居多。《顏氏家訓》兼儒、名、道、佛,其中儒家是主流,其余則為支流。至此,二書的性質(zhì)便容易清晰判定了。
二
下面的一個問題,是要進一步探討《人物志》與《顏氏家訓》二書這種“兼綜駁雜”雜家風格的形成原因。通過對二書及其作者的分析,我們大致認為:二書豐富駁雜的人才思想之所以產(chǎn)生,大致有以下三方面因素:作者廣綜博學的個人認知和對前人豐富的思想遺產(chǎn)的繼承拓展以及當時較為寬松的社會現(xiàn)實環(huán)境的影響。
(一)廣綜博學的個人認知
劉邵字孔才,廣平郡邯鄲縣(今河北邯鄲)人,是曹魏政權中有名的政治家、三國時期杰出的思想家。劉邵初為廣平郡計吏,后屢遷太子舍人、秘書郎、散騎侍郎、散騎常侍,歷仕武、文、明諸帝。他學問通博,凡文學、名理、法律、禮樂諸科無所不究。其生平著述甚多,除《人物志》外,獨立或參與編撰的著作尚有《皇覽》、《新律》、《律略論》、《樂論》、《法論》、《都官考課》等多種,此外,又撰有《趙都賦》、《許都賦》、《洛都賦》等文學作品。《三國志》作者陳壽除專門為劉邵寫傳外,還在評論文帝曹丕、陳思王曹植等人時,特意評論了劉邵:“劉邵該
覽學籍,文質(zhì)周洽。”認為他學識廣博,修養(yǎng)和品質(zhì)達到了完美的統(tǒng)一。
再觀顏之推。顏之推字介,瑯邪郡臨沂縣(今山東臨沂)人。《北齊書》卷四十五、《北史》卷八十五均有傳。他生于公元530年,卒年約為公元591年。顏之推一生仕宦頗多坎坷,歷仕梁、齊、周、隋四朝,三為亡國之人。顏氏家族“世善《周官》、《左氏》”,素有儒學傳統(tǒng)。博學多才的顏之雄繼承了家族的文化傳統(tǒng),在經(jīng)學上有著深厚的造詣。不過,顏之推并不認為“經(jīng)外無學”,他“博覽群書,無不該洽,詞情典麗,甚為西府所稱”。顏之推一生著述頗豐,留下《顏氏家訓》等大量記載自己學術觀點和研究成果的著作,被后人稱為“當時南北兩朝最博通最有思想的學者”。
從劉邵、顏之推一生的學術成就以及后人的評價中可以看出,二人都是當時著名的學者、思想家,他們勤奮好學,自覺地進行各類知識的吸收、融合和重組。他們博學多通的認知態(tài)度,是造成二人思想多元取向的主觀原因。
(二)對前人豐富的思想遺產(chǎn)的繼承開拓
《人物志》與《顏氏家訓》人才思想方面雜家色彩的形成,除了二人的主觀因素外,繼承前人留下的豐厚文化遺產(chǎn)無疑是又一重要因素。前人積淀下來的思想資料,為二人擴大寫作視野和進行深一步的探討論述提供了極其有利的客觀條件。例如,二書對“中庸”一詞的理解和闡述,即是對孔子文化遺產(chǎn)的繼承和發(fā)展。眾所周知,孔子將“中庸”確定為一種理想的道德標準。劉邵也使用了“中庸”一詞,但是他把“中庸”這一相對抽象的概念具體化了。他認為:“中庸”是一種人才的理想個性,它中和金、木、水、火、士五質(zhì)構成,以平淡純一的元素為基礎,平均、協(xié)和,可塑性很強,而且無明顯缺陷。具有“中庸”個性之人適合于任何職業(yè),也即是說,“中庸”是人才生成的最佳個性。
顏之推同樣使用了“中庸”一詞,也同樣把這個相對抽象的概念具體化了。他認為,“中庸”是與“上智”、“下愚”相區(qū)別的另一類人才。秦漢以來,世人多以“中庸”為中材之稱號,顏之推即是此意。他所說的“中庸”不再是一種道德標準或個性,而是一類人才的名稱了。同一個“中庸”概念,劉邵、顏之推的說法均與前說有同有異,表現(xiàn)出了二人在思想上對前人的繼承和超越。總之,《人物志》與《顏氏家訓》的人才思想,是在前代著述的基礎上汰粗存精、博采眾長而成,有著自己的風格與特色。
(三)當時較為寬松的社會現(xiàn)實環(huán)境的影響
劉邵、顏之推都能在各自的論著中兼收并蓄多家思想成分,這也是當時社會現(xiàn)實環(huán)境相對寬松的結果。單就意識形態(tài)而言,魏晉南北朝長期分裂的政治局面使政治對學術的干預和控制弱化,這便為學術思想的自由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契機。漢代受到推崇的儒術,此時已難以保持其控御眾生的地位。儒學“天人感應”的理論在今文經(jīng)學家手中被推衍為讖緯神學,古文經(jīng)學派則在“名物訓詁”中走向繁瑣破碎,這些都致使儒學危機四伏,權威性急劇下降。儒學的衰落使其他的本土學說(如名、法)或非本土學說(如佛教)得到重視,形成學術上的多元發(fā)展。為了解決理論上或政治實踐中的問題,魏晉南北朝的思想家們大多采取了實用主義的態(tài)度。雜糅諸家思想而不專為一家之言,這是導致《人物志》與《顏氏家訓》這類著作形成雜家思想色彩的又一重要客觀因素。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雖然二書被《四庫全書總目》列入雜家類文獻,但是我們也不能高估二陪所具有的雜家色彩。由于兩漢儒學對學界的巨大影響力,我們觀察到二書中的道德指導原則仍是儒家的,因此從儒學變遷的角度上看,《人物志》與《顏氏家訓》二書亦可視為儒家思想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升降興衰的標志。《人物志》中的儒學色彩逐漸淡化,表明漢魏之際儒學權威的動搖和下降,其書中多采用《老子》等道家者言,則對于玄學的興起形成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顏氏家訓》重視禮儀以及道德教化在人才培養(yǎng)中的作用,反映出經(jīng)過400年戰(zhàn)亂以后,儒家禮教之學在南北朝后期有了某種復興的趨勢。
五四時期,胡適曾說:“我們要知道,凡是一種主義、一種學說,里面有一部分是當日時勢的產(chǎn)兒,一部分是論主個人的特別性情家世的自然表現(xiàn),一部分是論主所受古代或同時的學說影響的結果。”他將思想學說的產(chǎn)生歸為時勢、個人性情、歷史及現(xiàn)實思潮影響等幾層原因,應該說這是較為全面的分析。以胡適所論觀《人物志》與《顏氏家訓》雜家色彩的形成,同樣也是適合的。需要補充說明的是,諸子百家大都與中國西周王官之學有歷史淵源。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論諸子之學時,曾引《周易》中“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一語,用以說明諸子各家學說在判然多途的同時,也具有溝通其間的共同文化基礎。如以此論觀之,那些在不同方向上發(fā)揮作用的中國古代文化傳統(tǒng),在儒學權威下降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彼此激蕩和溝通,呈現(xiàn)出一種開放的文化態(tài)勢,最終形成《人物志》與《顏氏家訓》的雜家風格,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責任編輯武麗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