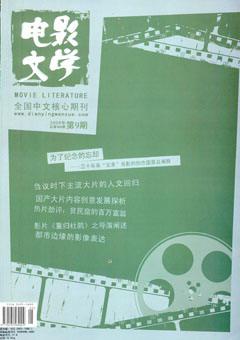后殖民時代的殖民狂歡
鄧文河
第81屆奧斯卡最佳影片等八個獎項、第33屆多倫多國際電影節“人民選擇獎”、英國獨立電影獎、2008-2009年度英國電影學院獎最佳影片等七個獎項……2008年末2009年初,世界影壇最耀眼的光芒無疑來源于英國導演丹尼·鮑爾的《貧民富翁》。該影片甫一出現即引起影評人的一片叫好。《貧民富翁》的劇情與主題完全符合了好萊塢的一貫精神,即窮小子咸魚翻身與愛情。如果從更深層次上講,從影片中可以看到好萊塢的“美國精神”。但是影片的故事背景與表現手法以及丹尼·鮑爾的英國導演身份和印度長達190年被英國殖民統治的歷史不得不引起我們在影片輝煌背后的一系列思考。薩義德曾經在他的《文化與帝國主義》中寫道:“西方人可能離開了亞非拉殖民地,但他們不僅把它當作市場,而且當作意識形態的領地保留起來,繼續他們在精神與思想上的統治。”英國人從印度徹底撤離已經有50年,不過從這部影片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英國人的殖民統治在印度留下的陰影以及從影片中反映出來的那種“居高臨下”的審視目光。因此,我們不妨從歷史與文化和“奇觀化”的展示這兩個角度分析一下該影片反映出來的后殖民時代西方人的文化優越感與審視東方人的“以偏概全”。
一、歷史與文化
在歷史上,從1757年的普拉西戰役開始淪為英國的殖民地,一直到1947年《蒙巴頓方案》的出臺,印度才從形式上擺脫了英國的殖民統治。在近兩百年的殖民歷史中,英國的文化,即西方文化的象征以其強大的、無以抗拒的力量將印度沖得七零八落。經歷了啟蒙運動以及技術革命以后,在西方人看來,東方是充滿神秘與野蠻的土地,而且為自己的侵略找到了振振有詞的借口:“種族與文化的等級是存在的,我們屬于高等民族和文化,還要承認,優越性給人以權力,但反之也附有嚴格的義務……物質力量不過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20在《貧民富翁》中,這種帶有強勢權力的、赤裸裸的文化侵略所帶來的影響暴露的一覽無遺。語言是文化得以存在的基礎,任何一種文化如果離開了其本身的語言,它的內核與魅力無疑將大打折扣。語言在一個種族中對于文化傳承的巨大作用毋庸置疑。而在影片《貧民富翁》中我們聽到的是由一群印度人說的蹩腳英語,即使杰瑪這樣一個從貧民窟出身、沒有文化、沒有教養的人,他所說的仍是英語。相對于他的母語——印度語來說,英語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滲透到血液中的語言,由此可見英國對印度殖民統治所帶來的影響,即印度曾經光輝燦爛的文明將依附的是英語而不是印度語傳承下去。在獨立之初,印度將印度語和英語共同定為官方語言,雖然從表面看,《貧民富翁》在這里為英語找到了一個合理的解釋,但從深層角度來說,正是驗證了薩義德的話:“比過去本身更重要的,是它對現在的文化態度的影響。”在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除了少數的幾句印度語之外,其余皆為英語,這說明了雖然英國人已經從印度撤離,但其留下的影響仍存在,并且會一直延續下去。
《貧民富翁》的敘事技巧在于將“誰想成為百萬富翁”的演播現場與杰瑪對過去生活的回憶交替出現。影片敘事的明線是“誰想成為百萬富翁”的游戲過程,暗線是杰瑪與拉提卡的愛情。從敘事的意義上講,后者的價值要遠遠大于前者。在影片中前者不過起到一種穿針引線的作用。同時,作為一種營銷策略,影片采用“誰想成為百萬富翁”作為明線,是因為在印度確實有一檔這樣的益智類游戲節目。極具宿命感的是“誰想成為百萬富翁”這檔游戲節目最早于1998年出現在英國,在2000年被引進印度后掀起了一股收視狂潮。從這個角度看,英國從印度的撤離僅僅是軍事的撤離,來自英國或日西方文化層面上的意識形態仍在滲透印度社會。在《貧民富翁》中。杰瑪,一個來自貧民窟、目不識丁的窮小子最終獲得了2000萬盧比的巨額獎金,丹尼·鮑爾將好萊塢搬到了寶萊塢,將“美國夢”置換成了“印度夢”。作為一種文化,“美國精神”強調的是公平與努力,即在公平的原則下,個人通過努力便可獲得成功。《貧民富翁》不僅僅是劇情上的移植,更是文化上的移植。現實中,獲得印度版“誰想成為百萬富翁”巨額獎金的無一不是接受過良好教育、有著較好家庭背景的中產階級。在印度這樣一個貧富嚴重分化、等級秩序森嚴的國度,一個出身卑微的人要想獲得成功進入上流社會,其難度不啻于鯉魚躍龍門。但是影片中一切都是“it is written(命中注定)”,杰瑪需要做的就是抓住了一次機會,便實現了其飛躍。在影片中,當“誰想成為百萬富翁”最后懸念即將揭曉時,從高檔的娛樂場所到破敗的貧民窟,大家都在翹首企盼那個瘋狂結局的到來。電視,這個20世紀西方人的科技發明在占領了西方人的文化陣地后,又向東方露出了它那充滿魅惑的、難以抗拒的神秘微笑。影片的結局絲毫不令人意外,杰瑪獲得了百萬大獎的同時也贏得了愛情。電影在這時也顯示除了其強大的“造夢”威力,不僅帶領西方觀眾又經歷了一次“夢幻”,而且想當然的將印度觀眾作為“夢幻”的經歷者一起囊括進來。這種不顧文化背景、不顧現實的生拉硬扯的“造夢”無疑是《貧民富翁》的一大硬傷。丹尼·鮑爾在接受采訪時曾說,這是他第一次到印度拍電影,他將努力尊重印度文化,很顯然在這一點上他沒有做到。
在后殖民時代,西方之于東方不再是赤裸裸的武力侵略,而巧妙的置換成了溫情脈脈的文化霸權。物質與文化上的先進使得西方在看待東方時具有權威感和居高臨下式的俯瞰。相對于西方,東方是野蠻、落后的代名詞。野蠻被文明馴化是天經地義之事。因而當“文明”面對“野蠻”時,它具有的是至高無上的權力。在《貧民富翁》中,“誰想成為百萬富翁”的主持人即是西方文化的代表:高尚的職業、令人艷羨的社會地位,更重要的他是來自西方文化——電視的代表者。當杰瑪答對一道題時,他所作的宣判看起來更像是一種施舍,就如西方文化面對東方文化時一樣。影片中有一處情節我們應當注意:杰瑪沖擊1000萬盧比大獎時,主持人在節目的間隙上廁所,他對杰瑪說了這樣的話:“貧民窟的小混混一夜之間成為百萬富翁,你知道這一切都是誰主宰的?我!”寥寥數語,將他對杰瑪命運的表現說的淋漓盡致。而這時的鏡頭也說明了此種含義。主持人是常規的中景,而杰瑪是倒置的近景。其中的隱喻不言自明:主持人——西方文化的代表,相對于杰瑪——印度的代表,其地位是高高在上的。當主持人給出的錯誤暗示被杰瑪否決時,他氣急敗壞,甚至誣陷杰瑪作弊。由此可以看出當“文明”遭遇“野蠻”的抵抗時,它便褪下其偽善的面紗,露出了巨齒獠牙。這樣的現象屢見不鮮。總之,在這部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太多的英國在其前殖民地印度留下的印記。
二、“奇觀化”的展示
薩義德在其《東方學》中說:“東方幾乎是一個歐洲人的發明,它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充滿浪漫傳奇色彩和異國情調的,縈繞著人們記憶和視野的,有著奇特經歷的地方。”當張藝謀拍攝的《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在
世界上屢獲大獎時,卻招致了國內學術界的批評,稱其影片不過是“偽民俗”,為滿足西方人對東方的獵奇心理。同樣,在《貧民富翁》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從西方人視角出發展現出來的印度。譬如貧窮、宗教沖突、歌舞片、泰姬陵等等。印度的一切都被丹尼·鮑爾臉譜化了。他在給觀眾講述了一段印度版的“美國夢”的同時,也以一種極端化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了一個變形了的印度。在此,我們稱之為“奇觀化”。
國內有學者曾經將“奇觀化”定義為:“就是非同一般的具有強烈視覺吸引的影像畫面。或是借助各種高科技電影手段創造出來的奇幻影像和畫面。”對此定義我們可以進行擴充,其影像不應僅僅是具有強烈視覺吸引力的。按照后殖民主義理論看來,“西方”常常按照自己的邏輯與思維習慣創造出一個“東方”,從而能帶有優越感和偏見去看待東方。因此,“奇觀”它還應當包括在西方人的視角之下呈現出來的偏離了東方原貌的影像。在這個“異質化”的過程中,西方人最慣常采用的手法是“放大”。在《貧民富翁》中,丹尼·鮑爾即采用了“放大”的手段,從一個西方入的視角將他心目中的一個集貧窮、宗教沖突于一身的印度呈現于觀眾的眼前。
眾所周知,印度是世界上貧富分化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但是在影片中丹尼·鮑爾似乎無意過多的表現貧富分化,而是將鏡頭頻頻對準了印度的貧民窟。影片的開端有一段童年時代的舍利姆和杰瑪被保安追打的戲,在這一段中印度貧民窟的影像被表現了出來:污濁的河水、破敗的房屋、骯臟的孩子、破舊的衣服等等。這種影像符合西方人對貧窮的印度的想象,在滿足了他們“窺陰”的欲望之后,給他們的文化與物質上的優越性又加了一個分量頗足的砝碼。在這段場景的末尾,對于貧民窟的描寫采用了由特寫向全景快速轉化的手法,在這一過程中貧民窟五顏六色的屋頂迅速變幻,最后的影像類似于一堆紛亂的美元疊放在那里。從這一鏡頭的變化,我們同樣會體味得到金錢對于大多數印度人來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而貧窮則是他們永久的標簽。影片對印度貧窮的展示并沒有止于此,在影片后面的情節發展中丹尼·鮑爾又為觀眾奉上了一道貧窮落后的“大餐”,當杰瑪和舍利姆的媽媽死于宗教沖突后,兩人成了孤兒。不知道英國觀眾在觀看那一段殘忍的宗教沖突時有沒有想到在印度佛教和伊斯蘭教的沖突正是拜英國人所賜?當兩個流浪兒被其該集團的首領收留后,影片對于貧窮的展現由量的積累轉為了質的變化。首領采取殘忍的手段將孩子弄瞎,讓孩子成為其賺錢的工具。當一勺熱油倒入孩子的眼眶時,這種震撼手段在引起一陣驚悸的同時也讓觀眾領教了貧窮帶來的恐怖后果。影片對于貧窮的展示是與西方文明人日常生括經驗大相徑庭的,如前所述,“奇觀”是指超出人的日常生活經驗的影像,在《貧民富翁》中,貧窮的展示雖然不像很多影片一樣用大場面的“奇觀”來吸引人的眼球,但它在人的另一生理層面上形成了巨大的沖擊力,完成了奇觀化的敘事。
如同好萊塢之于美國電影,寶萊塢、歌舞片也成了印度電影的代名詞。丹尼·鮑爾在影片中加入了歌舞片的成分,這不過是一種貼標簽式的行為,只是為了從另一個側面向觀眾展示另一種形式的“奇觀”。童年的杰瑪為了能見到當時寶萊塢著名的歌舞明星,他不惜跳入糞坑之中。當滿身糞水的杰瑪拿著明星簽名照欣喜若狂時,觀眾又一次被奇觀的影像震撼了,雖然這種震撼伴隨的可能是惡心,但也是一種極端的奇觀。而且在這里,寶萊塢歌舞明星的社會影響力被放大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不能不說這是一種“臉譜化”的行為。在影片的結尾,當杰瑪和拉提卡在車站終于重逢之后,突然加入了一段從表面上看與劇情脫節的舞蹈。這段舞蹈包含著雙重含義,最直觀的角度是杰瑪和拉提卡兩人最終走到一起后,用舞蹈表達他們的狂喜之情。這時杰瑪的身份已經不再是貧民窟的窮小子,但是我們要注意杰瑪身份的改變是西方的科技文明——電視賜予的,這也是“文明”對“野蠻”拯救的勝利。因此這段舞蹈更為深層的含義是“文明”施舍了“野蠻”后的一種狂歡行為。只不過這種狂歡是導演借助寶萊塢的歌舞傳統之手,借助一種“臉譜化”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另一種“奇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