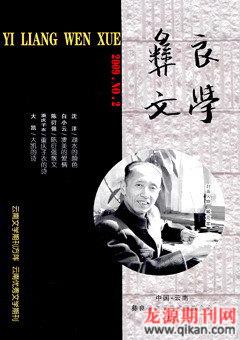陳衍強散文
陳衍強
人面桃花
大約1970年,桃花含笑的季節,我的家鄉來了一家昆明人,一個叫陳學琴的中年婦女帶著三個女兒成了我們生產隊的人。據說她是“右派”從省城遣送來滇東北的大山里勞動改造的。那時我才8歲,在腦中的印象是城里人穿得漂亮,長得白凈好看。
隔壁周家房子寬敞,家庭條件好。陳學琴一家就被安排住在周家。我的父親是生產隊長。對省城來的人很關照,干活總是安排輕的,因此陳學琴把我家當做親人,還給我水果糖,送花衣服給我妹妹。快過年了,我父親破例將生產隊所剩無幾的麥子分了10斤給她家。大年三十晚,陳學琴一家寄居的周家沒請她家吃年夜飯,我父親得知后親自去接她家到我家過年,遠離昆明和丈夫的陳學琴剛端起碗,眼里就流出兩滴叫淚水的東西。
陳學琴是一個挺堅強的昆明女人。是一個以堅韌與忍耐而著稱的昆明女人,她剛來我們山里的時候,連山路都不會走,總是爬坡腿軟,下坡崴腳。但她從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開始,背著還在吃奶的小女兒,天天與社員們起早摸黑出工,漸漸地從一個有點嬌氣的城市女人變成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村婦女。一雙磨出老繭的手與社員們一起挖地、鋤草,再重的農活也能承擔,再臟的農活也能忍受。每天收工,她背上孩子,懷里還抱著生火煮飯的柴草回家。后來,她家從周家搬到生產隊讓出的一間保管室里,與別人家的婦女一樣養了一頭豬,只是忙不過來打豬草,那頭豬只長到70多斤就宰了。我常看見她在雞聲里開門,在炊煙上升時梳她的長辮子。
陳學琴的大女兒小蓓與我同歲,長得好看又可愛,我只能用我家門前那棵桃樹盛開的桃花才能比喻那張笑逐春風的粉臉。現在想起她倚在我家桃樹下的春天。我有一種回到唐朝崔護題詩都城南莊的感覺。初夏,我家的桃子熟了,小蓓想摘桃子吃,被我大哥阻止。我很同情她,就偷了三個桃子送她。她吃著桃子。臉比桃子還紅。小蓓在鄉村上學時,與我同桌,她的數學好,我的語文好,我們就互幫互學。她還會唱很多歌,如“北風吹,雪花飄”之類。她有很多連環畫,曾借給我一本《智取威虎山》。冬天了,我們在教室里燒起柴火讀書。有的同學欺負她。不讓她烤火。因此,她每天來上學都穿得厚厚的,獨自坐在課桌前讀寫造句和加減。我那時就知道憐香惜玉。讓她與我一起烤火。
陳學琴一家,在我們生產隊生活了三年,因政策得到落實返回了昆明。她們走的時候。我家門前的桃花再度芬芳。她家說不上興奮也說不上傷感。總之心情很復雜,也許有一種悲傷是無法悲傷的。但是,不管歲月如何流逝,這世界怎樣變化,她一家是不會模糊我的故鄉的,我的故鄉肯定占據了她一家心靈史的部分。
后來我聽說,陳學琴給我家鄉的一個人來過信,信中說她在昆明民族貿易大樓站柜臺,她的丈夫是一家工廠的工程師,她的三個女兒都參加工作了。
歲月悠悠,多少往事也隨風飄散,我家門前那棵桃樹已枯死多年,現在連灰燼都消失了。但我常對往事牽念,想知道陳學琴一家后來的經歷和各種變故。我雖然常翻《春城晚報》,但始終看不到她家的消息。我雖然偶爾到昆明,但人海茫茫,就是陳學琴、小蓓從我身邊走過,或者在公共汽車上坐在我前后左右,我也認不出來。
我只能把這一段在家鄉經歷的往事留在心中了。
豫北走馬
一個無雪的冬季,我從河南西部到河南北部,仿佛從唐詩抵達宋詞,心胸更加天高地寬。線裝書的豫北,像發黃的散落在地的舊籍,使我一路行吟,并且在一日之內游歷了眾多古國,朝秦暮楚,鄭南齊北,想念一度榮華的故都,掩卷而又掩面。
乘車往豫北走,由于高速公路的緣故,似乎一晃就闖進公元前的好幾個世紀,只是在流逝的歲月中再也看不到劍掃的烽煙。在河南話中穿行,必須拋棄一切傳統的比喻,才能聽到黃河用民族唱法唱出的古歌流過豫北的身體。喂養著從無數偉大的傳說中走來的子民。我看見長滿甲骨文的殷墟,像枯樹上萌芽的春天,用象形的閃著鳥翅光芒的文字,提醒我商朝就在腳下,每走一步,都會踩碎龜殼上的卜辭、帝王的車馬、宮女的歌聲。我再一次感到,比生命更久長的是留住時間的文化。在這前不見古人的地方,我已經無法用美和荒涼來象征古樸,我只能用天真的眼睛將后來者所賦的新詞刪繁就簡,像一個精神的國王,治理變得疲倦的疆土。
途經安陽城,少女們千人一面,在南腔北調中混為一談。滿街的掛歷,正向行人出售1994年。自助餐廳的卡拉OK,工廠的轟鳴,一路吵著,只有到了袁林才清靜下來。袁林有袁世凱睡覺的墓。我像翻一本興趣不大的書一樣,一目十行。發現在他的墓壁上也有人刻上“某某到此一游”的雜七雜八的字,而我當時正想著討袁護國的往事,無法寫出我想說的。在比干廟和文王演易的監獄,我飽經滄桑與光榮的目光擦亮地攤、太極八卦,看到了外商投資的大酒店,站在有如秋風梳理的純凈的湯陰城。湯陰城是圓形的,像宋朝的大河卷來的一只裝著岳飛的盆子。我來的時候,岳飛早已從盆子里爬到岳廟,用泥塑的金身背對我,展示其母刺在背上的4個忠誠的宋體字:“精忠報國”。而百貨商場的禮儀小姐們,胸前的緞帶上也有4個字,是隸書的“歡迎光臨”。
豫北出土的很多故事,如武王伐紂、項劉爭霸、曹袁決戰,像春花秋月,不了也得了。因而我放棄了像一些古代朋友一樣立馬狂嘯的念頭。把往事付之笑談中。我途經的地方,只要一個急轉彎就可到劉震云的老家延津縣。劉震云是我很偏愛的一位作家,他在《故鄉天下黃花》《故鄉相處流傳》中塑造的許布袋、沈姓小寡婦們總是誘惑著我。因有比去延津更要緊的事,我只好上車,經過6500米的黃河大橋,回到新鄉市,感嘆一句:到了黃河,總算死心了!
豫北,只是我的一個匆匆而過的中途,盡管我沒有看到冬天的第一場雪,落在古戰場、開發區和剛長出的小麥上,但我看到“新飛”冰箱比廣告做得好,我還看到那些為生活四處奔走的人群,像南方的父老兄弟一樣。在離開豫北時,我多想喝酒,甚至想把黃河舉起來與豪爽的河南人干杯,如果醉了就躺在莽原,做一個浪漫的劍客。
洛陽行
一踏上洛陽的土地,我就踩著九個朝代。干燥的風,從隋唐吹來,吹得王城公園的牡丹如妃子的臉。凋零在后宮。
古典的洛陽,立馬中原,仰天狂嘯的是南來北往的火車。我在漂泊的人群中游牧。只見那些比牡丹更嫵媚的洛陽女子,盛開在滾過帝王車馬的大街、商場和棲滿白鴿的軍營。
在洛陽城南的龍門,我碰著一個洛陽女兵。一張國色天香的臉,閃著唐三彩的光芒,使我不得不用戀人的眼睛看她。我看見伊河的藍色翅膀掠過洛陽的天空,寧靜的水波上,漂浮著唐詩、宋詞、艷曲和桂冠的碎片。我深情的目光,擦亮一千三百五十二個石窟。看見北魏時期的巨匠,全部幻化成十萬尊石雕,使我在睡著的火焰之外,分不清誰是李姓天子,誰是握緊權力與精神的武媚娘。
我慢慢靠近洛陽的光榮與甲胄,繞過白馬寺的馬匹、高僧和蔣介石客居的別墅,用平仄的雙腳踏
上東山的履道,穿越半掩半露的松風亭、樂天堂,抵達唐朝抒情詩人白居易的墓園。站在這位古代詩友的墓前,念天地之悠悠,我開始思考詩歌、道路和跪飲死亡的神祗。墓冢呈琵琶形的草坪,仿佛離離原上草喚出的春風還在彈奏潯陽江頭的千古絕唱。看來,詩人只有夢回唐朝,才能頭戴桂花的金冠,居住在天堂里的村莊。用五十闋的新樂府喂養國家、人民和西風飛鳥。我不是江州司馬,但夾克衫已經被懷舊的淚水打濕。
我喪魂失魄,從寒冷的高處轉身,闖進金戈鐵馬的關林。想從熄滅的戰火中找回被生活消磨掉的陽剛英武。關林是西蜀大將關羽的陵園,埋著他的被刀劍取下來的首級。跨過威嚴的儀門、碑林,只見一百零四個石獅子分立甬道兩旁,如守護英雄頭顱的衛士。“從人的頭頂取走王的冠冕,正如從馬骨頭里取出一座孤城。”想起一位與我同時代的詩人的這兩句詩,我就不用桃園結義,不用過關斬將,不用夜走麥城。只要用英雄和酒鬼的眼睛,就能與大將相逢。笑談古今。
這是一年前的洛陽,落葉摘走了冬天,每一條街道都洶涌著市場經濟的浪潮。而我還迷失于唐朝的官話中,想在機器中找到牡丹的零配件,直到我走過巨大滄桑的雙腳,被洛陽百貨大樓的電梯升到離公元前十一世紀更高的地方。才發現洛陽紙貴,守望詩歌的人如紛飛的落葉。
洛陽,讓我在疲憊中暫時放棄行吟和燃燒,在你的寶座上,我多想睡去,但我只能投宿在自己夢中的疆土。
曲阜記
當我看見春秋時期的城門,差點忘了自己置身的年代,不用問,這就是古典主義的曲阜。這就是可以使人產生沖動的孔子故里。
灰色的天空下,我像一個在異國他鄉漂泊的人,混跡在朝圣的南腔北調中,三千年前的馬車,與出租車一起在曲阜的街上并肩前進,只是車上坐的不是顏回或子路,而是企業家,當代詩人,女歌星,使我看到了曲阜的過去和未來。
我沉浸在《詩經》上游的遐想中,不以為然地聽那個戴小紅帽的孔姓小姐講解公元前478年,魯哀公命祭祀孔子以孔子故宅作廟,然后在儒學的博大精深中閑庭信步。
幾進院落,穿過勾心斗角的房梁下的弘道門,在奎文閣和十三碑亭后面徘徊。我看到古老的雪花落在時間的翅膀上,而抬走春天的落葉,正在枯枝上跳起崇尚周禮的六藝樂舞。我匆匆的目光打掃著孔子故宅的詩禮堂,不知不覺已到了孔家喝過的那口井邊,我即使落井下石,也難測圣人思想的深度,就像孔子藏書的魯壁,我即使撬開一塊磚,也放不進我嘔心瀝血的詩歌。
我是從山東一詩友寄我的照片上認識大成殿的。后來又在孔府家酒的包裝盒上看到過,因此走近大成殿,雖初來乍到。卻有一種故地重游的感覺。我似乎在神游,把擦肩而過的游客當做穿麻衣的冉有和公西華。甚至把從重檐斗拱間漏下的風,聽成曾子皙的琴聲。那盤繞在二十八根廊下石柱上的雕龍,在我的眼里閃爍著不可逼視的光芒。
我從被稱為衍圣公府的孔府出來,轉眼就到了隱藏在四萬多株樹之間的孔林。孔林是埋藏孔氏家族的墓地,占地三千畝,比曲阜舊城還大,如沒有導游小姐一定會迷路。那些三足土堆成的墓,其實是一部孔氏家族的編年史,我只能一目十行地閱讀,直到發現孔子的墓才停留下來。孔子的墓是孔林中最高的一座,有惟他獨尊的氣派。這個歷經十四個春秋周游歷國的圣人。在川上曰過“逝者如斯”名言的大師,面對他的墓和墓前那塊后人從泰山運來的“封禪石”,我還能說什么呢?我只能靠在他的墓碑上感嘆喪亡與輪回的人生秘密。孔林東北部孔子六十四代孫孔尚仁的墓是很多游客忽略的地方,而我因為讀過《桃花扇》對李香君的故事略知一二的緣故,對孔尚仁的憑吊從個人感情上來說比別的都很重要。當我發現這位有民族氣節的著名劇作家的墓躲在一個不顯眼的角落,我開始對生活產生一種敬畏。面對現實。我該回答一個普通人該怎樣過普通的日子了。
我是在喝下半瓶孔府家酒的醉意中辭別曲阜的。直到曲阜離我遙遠如一個夢境,我才用詩歌精神記敘它在我心靈上留下的履痕:“我不中庸/也不懂禮節/但會種菜和逮蝴堞/我也愛游山玩水/結交天下好漢/在魯國和楚王之間/打聽歌舞廳和民航售票處/更多的時候是呆在家中/漫不經心地做學問”。
當我學會用寫作來教育自己和減輕生命的疼痛時,我知道這與我到過孔子故里有關。
登泰山記
一個無雪的冬季,我登上了五岳獨尊的泰山。我乘坐的車呼嘯奔馳著從曲阜插入泰安市已是陽光蒼白的中午。平地起高山,如同電影鏡頭的轉換,我有一種被泰山撞了一下腰的感覺。
我從泰山腳背上乘車抵迭中天門,不斷移動的車窗刪去了岱宗坊、王母瑤池、孔子登臨處的石坊。甚至連爬十八盤也省略了。就這樣。我被纜車直接吊到元朝的南天門。當我的雙腳從亂云飛渡的空中降落到現實的泰山,站在杜甫《望岳》詩中遙望“齊魯青未了”的地方,也許是云南人又生長在烏蒙山的緣故,我只有從泰山的名勝和古跡尋找他山之石。踩著向上的石階,我感覺我的思想正在升高,但我無法寫出我君臨的泰山。因為路旁的每一塊石頭,都被先我而來的人留下墨跡。生命匆匆,我也像一陣風吹過泰山的肩膀。在對崇高與偉大的理解中,我像一個滿面塵土的行吟詩人,內心不安,壓抑,沉重,甚至爬上玉皇頂,靠在極頂石上。我也不敢妄生“一覽眾山小”的英雄夢想。因為天地如此之大,我是這樣渺小,只能過普通人的日子。
登上泰山,我放棄了“磅礴”一詞。而用“巍峨”來形容。面對驚濤拍岸的云海,亂石穿空的松風,我形而上的盔甲已被汗水打濕。是的,一切都離我這么近,毓秀的山巖,殉情的孤雁,舞蹈的神靈,還有“登峰造極”的石刻,都伸手可觸。但我卻有點高處不勝寒,像詩人雷平陽詩中寫的天堂守門人,背負那些有王者氣象的廟宇,欣賞神仙,了望見塵。我已經不是在游覽,而是在泰山的高度,在詩歌的精神世界,尋找我的信仰、社稷和生活的力量。
暮色蒼茫,飛鳥如落葉飄過金瓦紅墻,飄過唐玄宗碑文石刻,我用農民的目光與高貴如婦人的泰山辭行。車子開動后,山影在車窗上大片大片退去。半睡半醒之間,我的足跡又被拉回濟南,而我的心里也裝著一塊孤獨的石頭,使我在匆匆奔走中抵達我自己。現在,我正置身云南的一個小縣城,手倦拋書,白日夢長。不管處境如何,不管外面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我都守身如泰山的一塊頑石,與思想的疲倦斗爭。在別人的夢里漂泊和游牧,我總是對我登過的泰山產生一種敬畏和感恩。
詩歌背影
我在與朋友們談詩的時候,幾乎都要返回1984年,因為在這一年我很激情和青春地寫過一首《山上,睡著姐姐》。現在閱讀這首詩,也許我使用的技術手段和對生活的“再現”都過期了。但這首詩的背影是一個故鄉女子,她的故事使我一直處于“愛與痛的邊緣”的臨界狀態。
那是我還在故鄉當農民的年代,生產隊有一個姑娘,我至今還記得她的花樣年華,要描繪她的身材和面目,我不得不想起莫言獲“大家文學獎”的那
部長篇小說名。在周圍長得醒目的姑娘中,她可以排在前三名。她性格倔強、潑辣,而且一身蠻勁,干農活時能與男子漢試比高的姑娘只有她一個。她的婚姻是父母包辦的,出嫁后,兩口子天天吵架。出嫁還不到一個月,她就跑回了娘家。當她的男人帶著一撥人來她娘家找她時,她已逃到離昆明不遠的地方。
半年后,她又返回娘家。本是良家婦女的她,一天比一天野。在我們生產隊有一條通往縣城的公路,她經常跑到公路邊等車,與好幾個開拖拉機的人混得滾瓜爛熟。有一段時間,她幾乎天天都搭上拖拉機去縣城,早出晚歸。她的娘家沒有煤炭燒了,那些開拖拉機的會幫忙拉,一拉就拉出一連串的風言風語。時間一久,人們開始對她指指戳戳。用今天的話說,她是一個“緋聞”纏身的女子。
盡管她很潑辣,不在乎別人怎么說。但后來還是被人們的冷眼和污辱壓垮了。一天黃昏,有人說她喝“敵敵畏”死了,我剛聽到這一消息時還不相信,直到我趕去她的娘家,發現她已經躺在屋檐下的兩條板凳支撐的門板上,嘴里吐著白色泡沫。才知道一條新鮮生動的生命熄滅了。我想。也許她早就對生活喪失了信心,并且認為沒有臉面活在世上。
第二天把她埋在哪里又成了問題,人們認為她的名聲不好,不同意埋在他們承包的山上。后來只好把她埋在離她很遠的深山里。抬喪的時候,只有10多個人上前,站在旁邊看的鄉親。沒有一個人流淚。由于棺木是剛砍的樹做的,很重。抬了不多遠人們就抬不動了。抬到生產隊長家門口時,由于生產隊長得罪過一些人,有人為了出一口氣,就把棺材停在他家門口,還說第二天接著抬。生產隊長只好央求大家再往前抬了一段路,抬到半山腰實在抬不動了才放下回家。人們第二天又去幫忙,費了很大勁才把她抬到埋她的山林里,我因為第一天抬累了,加之第二天外出,所以第二天我沒有去抬她。
第二年,我去埋她的那片山林里砍柴,望著她的那座亂石砌的墳,內心有一種說不出的傷痛。想不到她活著的時候新鮮生動,風風火火,而現在一個人睡在遠離親人的深山,連鳥兒都停止了歌唱,她難道不感到冷清和寂寞嗎?難道這就是人生的悲哀,盡管那時我還沒有路過愛情,但總有一些事讓我感動,總有一些痛讓我流淚。我仿佛看到一朵燦爛的花的凋謝,看到凄涼和美的毀滅。于是,我在放牛的山上,寫下了《山上,睡著姐姐》,我在這首詩中再現了另一個她,使用了“象征”和“隱喻”,不是復制,而是她的故事為我提供了詩歌資源。其實,現實中的她,按輩份是我長輩,有一個與很多農村女子一樣普通的名字。她叫秀。山東一位女詩人看了這首詩。在給我的信中說把她“感動得差點兒流出淚來”,從“淡淡的語言”中“感到了那么一點凄婉”。后來,這首詩發表在1986年第1期《綠風》詩刊。讀者們不一定知道詩歌的背影,我現在把故事寫出來,不是創作談,只是為了講述。后面這首詩,就是《山上,睡著姐姐》:
“山上,一片寂靜的松林里/睡著我家姐姐//她是爹媽栽的一朵白山茶/卻開出玫瑰紅的顏色//在山坡上放羊/她心里裝著寬敞的教室/想懂得大人知道的事情//她埋怨茅草房的破爛/袒露了她的迷人/惹出村里的謠言//后來,她害了一場重病/吃下一杯很苦的藥酒/喊著一個青年的名字/睜一雙還很美麗的眼睛/被幾個人送上了山//在清冷的松林里/她成了纏腳老奶奶的鄰居//十年后,我家姐姐醒了/在她小屋周圍和墻縫中/栽了很多小草和野花//我含淚告訴女友/姐姐不愿睡著/因為她沒穿過/你這樣好看的花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