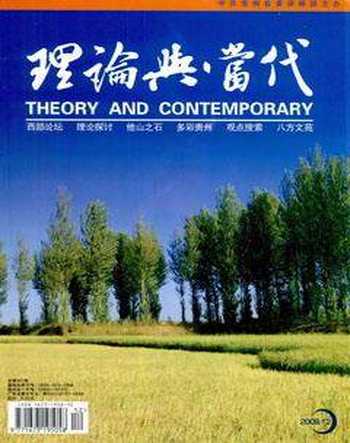為了開墾荒蕪的心靈
劉正緒
在2007年第二屆長篇小說“烏江文學獎”得主中,《儺賜》是受讀者關注較多的一部作品,究其原因,正如《儺賜·編者按》O中所說的那樣:“……王華以優美的情歌筆調,向我們講述了大山深處一個叫攤賜的地方,因為貧窮,兄弟三人同娶外鄉姑娘秋秋的故事。在那遠離塵囂愚昧的地方。貧窮和苦難演繹出的凄美愛情直抵讀者心底情感最脆弱處,纏綿悱側的愛情挽歌,令人潸然落淚。”
《儺賜》比較巧妙地解決了農村題材小說中語言形式的難題。以一個輟學高中生藍桐的身份和視角來審視自己所處的世界,這就避免了鄉下人說城里話的弊病。其語言風格的生動活潑,是很值得注意的。例如:在“我”遇險之后的一大段描寫:“大大小小的白色的坑。后來,秋秋的臉突然跌落下來,落在我的右肩上,秋秋終于沒有能壓抑得住的尖利的哭聲就在我耳朵跟前響起了……
“這樣,我才有力氣狠狠地呼吸了一口氣,然后才真正的活了回來。”
“我們的身邊圍著很多人,全是近處聽到出事后趕來看熱鬧的。他們看我真的活過來了,臉上也松活開了。剛才被關在喉嚨里的一些話這時候才出了口。”
“全都悶死在里邊了,就他躺在洞口不遠的地方。”
“把他拖出來時他也差不多沒氣了,都以為他可能也沒得活了。”
好了,這回好了,只要有氣就好了。
把他背回去吧,背回去好生緩緩。
霧冬跟我爸說,我們背回去吧。
爸把一張擠得坑坑洼洼的臉不住地點。
霧冬跟秋秋說,我們背他回去吧。
秋秋把臉抬起來,把淚珠子點得滿天飛。
秋秋和爸把我軟得跟面塊一樣的身體扶起來,放到霧冬的背上。
一路上都很寧靜,像死亡一樣寧靜。
回到家,我被洗干凈放到床上,屋子里才開始顯得熱鬧起來。
霧冬鋪開了他的道士場合,隨著一陣鑼聲響起,香火味兒也進了我的鼻子。還有桐葉湯的味道,也澀澀的彌漫在屋子里。我爸和我媽,被霧冬安排在道壇邊正襟危坐。霧冬舉著他那把叉長叉黑的劍,舞著他那件叉黑又重的道袍,兇神惡煞似的在我爸媽頭頂上空勁舞,嘴里嘰哩嘰噥念上一陣,突然喊一聲,呼哈!”……
這種把宏觀世界與個人心理感受融于一體、把聲音、行為、氣味(視、聽、嗅覺的作用)環境變化同步表達,形成活脫脫的影視畫面的寫法,使書中人物在讀者心目中“生物學范疇”的人的形象,突變為“社會學范疇”的正常人,似乎是游離于體外的靈魂俯瞰自己曾經共生的群體,感受到完善而濃厚的終極關懷,堪稱“神來之筆”。
每個人都是一個歷史的、具體的現實人,作者筆下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感情豐富多彩,充分體現了人物的真實性。在人物塑造上,藍桐是比較典型的。藍桐原是無聊的農村知識青年,是村里唯一上過高中的人,因此,對外界一“現代世界”充滿向往之情。可是,他既是“儺賜”人,就免不了有“地域”、“民族”的基因(從人物的名字上,我們不難推測出來),因而其心理活動就顯得互相矛盾。這首先表現在他對“性”的心態上:藍桐在“偷窺、偷聽新房”、旁觀“野合”以及與秋秋發生肉體關系時,性格的分裂性表現得非常充分。當然,藍桐最后還是走了。相信他在進一步融入現代社會后,會有某些改變,這是因為:“我”沒有離開儺賜,就得接受秋秋。因為我不會允許自己去促成秋秋和霧冬離婚。……我得把巖影的女人掙來了才能談這件事情。……我不想讓霧冬痛苦,也不想讓秋秋痛苦,我不愿意為救任何一個而去傷害另外一個。
當然還有其他許多的原由促使他堅定不移地出走。盡管“帶著我去遠方的路穿行在儺賜莊的包谷林里,迷蒙中包谷禾稈像為我送行的鄉親,默默地站著,凄凄地望著。有一會兒,我就停下了腳步。我站在這里,讓目光越過坡下茫茫的一片包谷林,我想對它們說點什么。”然而,他還是“頭也不回地往山下走了,走向一個離白太陽越來越遠的地方。”
我們那一代人,都記得托爾斯泰描寫愛斯基摩人的婚姻情況時,用過“婚姻朋友”的概念,但記得最牢的,還是下面一些話語:“只有愛情才能使婚姻變得圣潔;只有被愛圣潔化了的婚姻才是真正的婚姻。”;“愛是神奇的,它使得數學法則失去了平衡;兩個人分擔一份痛苦,只有半分痛苦;而兩個人共享一份幸福,卻有兩份幸福。”;“愛情不是一種塵世的感情,乃是一種天上的感情。”因此,我們最初都難以認同《儺賜》式的婚姻。
我們還記得,培根說過:“在舞臺上,愛情總是喜劇的素材,偶爾還是悲劇的素材,而在生活中,愛情卻很是惹事招禍,有時像一位妖婦,有時像一位復仇女神。”或者,王華就是受此啟發,故意在故事的開頭讓藍桐們的“愛情”近乎“生物學范疇人”的行為一其實絕大多數動物對配偶也是有選擇的,而且嚴守“界內”規則的。為此,我們不能不對《儺賜》式的婚姻感到焦慮。直至看了藍桐出走的部分(這部分真是“冗長”而纏綿呀!)后,我們才從根本上改變了看法——“儺賜”人,同樣有自己的尊嚴和追求一王華只是為了強調全社會有責任和義務關注他們的尊嚴和追求。
《儺賜》中,對兩三個男人合伙娶一個妻子提供了許多假設的理由。我國確實還有個別少數民族地區存在“走婚”、兄弟共娶一妻的“民族風俗”,但“儺賜”的情況明顯不是,而僅僅只有一個原因:貧窮。貧窮還派生出了殘疾(秋秋也是殘疾人,否則不會下嫁到這個村予)婚姻:“我哥霧冬同時還是去替我和我同母異父的三十五歲的老光棍哥巖影提親,之所以要選我哥霧冬去,是因為巖影太老,而且還沒有左耳和左手……”
那么,貧窮落后的根源又在哪里?解放后相當長的時間里,政治運動太頻繁,推遲了社會的進步是原因之一;10多年前,筆者在鄉土作家潘年英的《扶貧手記》一書中又了解到,改革開放以來,不適當的開發也是導致農民連傳統生活方式都不能維持的重要原因。由于開發的效益多被開發商所提取,尤其是礦產資源開發(《儺賜》中主要是煤礦開發),一般都伴有生態的大面積破壞,土地因污染而不能再耕種;水源斷流使農民無法生存于故土……開發一處,貧窮一處的事例俯拾皆是,而無人負責的工傷事故后遺癥,更給農民造成巨大的、永久性的痛苦。問題是,承受這些痛苦的人們,往往由于種種原因而失去了應有的話語權,除非有人來替他們說話。我想,這很可能就是作者創作的初衷。《儺賜》旨在引起社會的注意,以期改變“儺賜”的生活方式。目前,政府正在進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大力推進“三農”問題全面解決的工作,“儺賜”現象絕不能繼續保留下去。因此,我寧愿相信《儺賜》僅僅是一個寓言,一個開墾荒蕪心靈的寓言。
王華致力于藝術上的創新和突破,致力于反映出不斷前進和變化的,而不是死水一潭的農村生活,以代表性作品奉獻給社會的目標,造就了《儺賜》。同時,他把人物形象塑造得淋漓盡致,以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特別是性的關系)去揭示生活中的矛盾。作家以自已感受到的熱點與焦點,反映了農民的要求和愿望。《儺賜》真實地揭示生活中的矛盾,但并不是簡單地暴露陰暗面。而是提示我們關心“這一個”現象,并對其作出積極的反應;通過生動鮮明的人物活動激發人們的共鳴,警示我們應高度重視農村弱勢群體。《儺賜》能夠引起人們深刻的思考,正是由于它能夠以情動人。王華寫出了人的遭遇、命運、痛苦、失敗,以及“可能的”成功和歡樂;通過描寫人物之間復雜的社會關系和種種矛盾沖突來反映特殊的生活。
另一方面,王華站在新的角度和高度,反映新的(或是過去未被關注的)矛盾;以新的題材(非“主流”題材),在藝術上、形式上、風格上充分發揮文學的特性和優點,并在結構、語言以及各個方面力求提高藝術魅力,增強了作品的活力。寫人、寫情是非常困難的,《儺賜》能把人和情寫到如此的高度,應該是“烏江文學獎”評委們慧眼所衷的原因吧。
注:見2006年《當代》雜志第三期《儺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