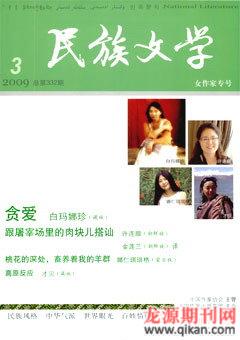跟屠宰場里的肉塊兒搭訕
2009-04-14 09:43:54許連順金蓮蘭
民族文學
2009年3期
許連順 金蓮蘭
假如有人,在周邊沒有一個人的情況下拾到別人的錢,做出的第一反應會是什么呢?從常識上考慮,應該是因人而異,可非常出乎意料,據學界分析,人們通常會做出大體差不多的反應。說是大部分人會裝得若無其事,卻迅捷地伸出腳去踩住那錢,然后飛快地觀察四周。據說這便是理性尚未介入的,人類下意識中做出的最快反應。那么,為什么需要確認四周呢?那是因為要確認有沒有被人看到。沒被人看到,錢就是自己的;要是被人看到,錢就不會是自己的,至少不會全都是自己的……
她拾到戒指的時候周邊也沒有人看見。因此,她可能想到可以把它據為己有了吧。可是。當時她并不知道這居然是一枚鉆石戒指。只當是沒幾個錢的裝飾品,因為這樣她把它擁為己有就容易得多,簡便得多。整整十天,她拿著別人的鉆戒沒有感到絲毫的自責或內疚,當然也就談不上什么不安或緊張。她后來說過,假如自己一開始就知道這是一枚鉆戒,肯定不會那么輕易昧下的,可這話實在不足為信。因為知道這是鉆石,且知道它的主人是誰之后,想擁有它的欲望反而更加強烈了,這一點她并不否認。雖然并不是原本就屬于自己的,但是現在要把它還給人家就像是拿自己的東西給人那樣的舍不得還覺得有些冤。難道,僅僅是因為它在自己的口袋里呆了十天么?
一
那些日子,她做旅店的清掃員,正熱衷于搜集客人們遺留下來的物品。一開始是扔了可惜才把它們保管起來的,可一來二去竟然滋生了少許貪婪,開始探頭探腦找尋有沒有什么值錢東西了。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