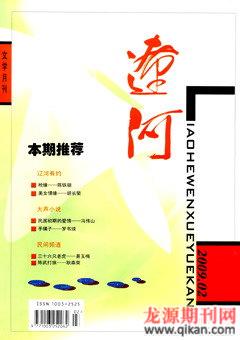散板四章
陳德根
秋思
一雨成秋,宛如一語成讖。
蜿蜒的水。九月在一場雨后喊著稀稀拉拉的號子,把季節的河拾得更高。
掌聲從大地深處響起,有水的質感。一個人的前半生,輕輕在大地中央站立。在大風中掏出珍藏了一千年的歌謠。轉身的時候,緩緩地說出一個村莊的名字。
我無語。迎風捧出薄薄的,透明的一生,放在秋水的側面。
我注定要在中途離去。是為了趕赴宿命中的約會。我不會帶走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但是,我會帶走你的一切:你的笑,你生氣的樣子,你輕輕捶打我的小拳頭,以及給你的傷害……我會用后半生的時間來打點行裝。
我背著這個行囊趕路。
如果可以,我愿意在秋天,再一次停下來。
我為你,也為我自己,準備了足夠揮霍的借口。
誦經的人緊閉雙唇。移至暗處的背影剎那間破綻百出:陰柔,遲疑;布滿了落日的光斑。
攫住流水浮云般的光陰,難道是為了等待一場繁華的惆悵嗎?
我躲在一面銅鏡的陰影里,用美麗和謊言去掩埋一路上的風聲和雨雪。
一段經歷陷入黑暗。被夜幕籠罩的吹簫人面色蒼白,氣若游絲。
我的比黃花瘦的妹妹眼波流轉:一邊是愛,一邊是憂傷。一些無法省略的細節在雨后瘋狂地開花,結果。
就這樣看著你走遠。蒼茫成墓碑上一行行淺淺、冰涼的文字。你的一生。
我愿意背負你的苦難;你的空空行囊。我用憑吊的虔誠,膜拜的心境迎著用你的骨節點燃的闌珊燈火向你靠近。
我守護著你行蹤不定的氣息,小心翼翼地穿越一些模糊的背影向你噓寒問暖。這一生一世的煙火依舊粲然。
我掬出淚水,打磨眾神眼中的悲憫。
歌聲喑啞。一道傷痕困住了我的跋涉。
國土淪喪的王,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醒來;吐出昨夜的星星;說出預言。用一支禿筆杜撰我的一生。
聽我講述生活
你的行蹤不定。你行程的篝火明明滅滅。你把你的疼痛,把你的感悟放在幾個困頓的詞語上。我知道,你這是在試圖掩飾心中的慌亂。我哭喊著,匆匆地站成另一種高度。讓我偽裝平靜,靠幾滴露珠取暖,我開始了講述生活的開場白。
我們從一場最初的雪出發,那些在紅塵中退色的塵埃和洗盡鉛華的面孔,依舊執拗地潔白著,閃爍著堅硬的光芒。
我依舊生活在一朵花的芬芳里,任憑歲月喑啞下去的濤聲把我覆蓋。
一種埋葬呼之欲出,一絲悲涼,穿堂風一般迅速地穿過我。片刻的猶豫,多么像夜里平靜盛開的雨露。
內心和夜色如此蒼茫。生活的歌子嗚咽著,滑過我日益陡峭的內心,此時。你仍在歸途。
一場大病,高高地掛著。那是一片若即若離,疲憊的云。
天色越來越深。晚歸的馬匹,滿腹心事的牧馬人,表情凝重,像天邊的積雨云。幾聲狗吠,還有見風就長的小道消息,使村莊陷入更深的靜穆和沉默里。
一些高大的榮耀和繁華潛伏著。一些困窘的背影依舊匆匆,正在逆著風返回故鄉。
那些歡聲笑語是焰火,那些晚霞是更深的孤獨。多少年了,我仍然在老地方。只有年老的父親按照節令春種秋收。
那盞祖傳的油燈曳動著,妹妹眼里的秋波,把我裹得更緊。
回家:鄉愁或其他
祭壇上裊裊的香燭,是第八十一次祈禱。在路上的人,行囊里裝滿了暮色。
這些木頭似的人,心里裝著的狗尾巴草,一次次小心地欠起身子。
八千里路云和月,故鄉在召喚。稻穗、麥穗,相互攙扶著。這些都是某種暗示。
我試圖在一滴露珠里稀釋我的淚水、汗水以及屈辱。家史,以及我的圖騰,被一些粗糙的面孔托舉著,向一汪寧靜走去。
我要在異鄉的月下流干我的淚水,說出心里的感受。選擇一個燈火輝煌的夜晚,從流水線、工地、擦鞋攤子、還有洗頭房里,我接過那些慵懶、茫然甚至有些狂野的眼神。
我要在夜色里趕路,牽著那些汗津津的手,我席地而坐,把目光投向一條小路的盡頭。
大地:村莊或其他
十二面鑼鼓被二十四只手漸次擂響,那些布滿塵土的禱詞,濕了村后的雨霧,打開了一本青翠的大書。
田園生活的橫斷面,暗藏著多少尖銳的聲音啊。鄉村的日子相互攙扶著;這些生硬粗糙的光澤;哽咽的音節正在游走,手指的陰影處,停留的是八月里走失的稻花香。
如何讓你前世今生的風霜在肩頭落下?輕些,再輕些,讓那些貧病交加、氣喘吁吁的背影進入夜色,進入空曠,進入茫然。
給你一絲近乎渺茫的期望,讓你在明明滅滅的前程里,想象春暖花開,想象在地上和地下走動的匆匆腳步。
一些樹葉般的文字,讓所有生澀的氣息都生動起來。那些簇擁著的洪流,被一個被高粱酒熏醒的人高舉著。他繼續往更暗處挪動,在黑暗中打開他的行裝。
內心的方言舞蹈著,那個人握住夜色。那些恍惚,盡情地搖晃著,在月光濡濕的夜晚,棱角分明。
那些散落在村口乘涼的人,以及那些溫暖的名字。那些在暗處的馬尾草,在向我輕輕地招手。
月華如衣,襤褸。農事、往事、村莊的根部和深處,是你醒過之后的空曠。
你在喃喃自語,鄉村的生活在起起伏伏。諺語之中、歲月之間,幸福的日子觸手可及。
唱了一半的歌謠和說了一半的話開始變暖,我心中的洪水開始泛濫。在那些屈指可數的美好日子里,那些鋒芒和棱角,驚醒和疼痛了你的風燭殘年。
這么多年過去了,你依舊不善言辭。你眼睜睜地看著許多華麗的語言在瞬間逃逸。你沉默不語,牽著那些正在衰老的歲歲年年,隱入夜色。
大地的皺褶里,一座村莊倒掛著。
村莊的盡頭,巫師的意念在閃爍,視線開始波動。
我在眼睛里打上補丁。路在遠方:大地溫暖的手心也在遠方,我必須在黃昏之前抵達。我帶上頑疾;帶上父親剛吐出唇角的讖語;赤著腳,裸露出刺青;帶上酒,帶著七分的醉意;我不敢回頭再看一眼妹妹臉上害羞的紅云。我只是在父親窘迫的生活里,一語雙關地指出三兩句反復晃動的隱語。
我想讓自己停下來,看著妹妹無邪的眼睛。讓那些失憶的水,那些訕訕的節令,也停下來。
只留一些風呼嘯著,慢慢地旋轉,穿過她,佯裝片刻的停頓和安靜。
我心中的冷暖,長滿了苔蘚。只有妹妹心中的愛不動聲色。這些晶瑩、單薄、凝固的水珠。道出了銹跡斑斑的旁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