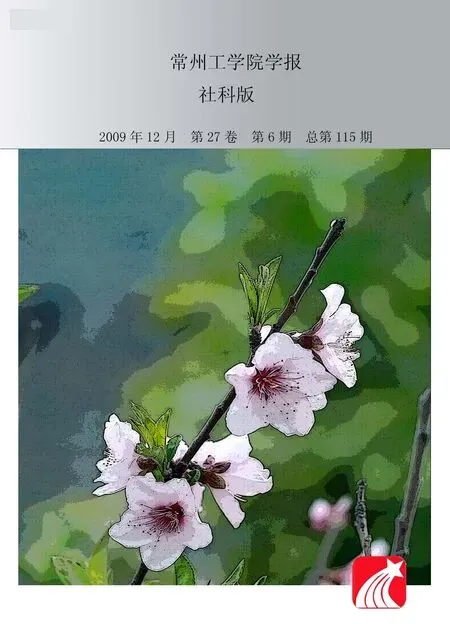洞燭幽微 微言大義
——讀趙元任《語言問題》有感
冉育彭,魏際蘭
(常州工學院外國語學院,江蘇 常州 213002)
趙元任(1892—1982),江蘇常州人,中國現代語言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被譽為中國漢語語言學之父,是享有國際聲譽的語言學大師。趙先生學科背景廣博,視野開闊,具有“哲學家的頭腦,音樂家的耳朵,文學家的才氣,數學家和物理學家的思維”[1]。袁毓林博士也說他“融會古今、貫通中外、橫跨文理、精通音樂”[2],實非過譽之詞。他一生當中曾在清華大學、夏威夷大學、耶魯大學和哈佛大學等任過教,后在加州大學一直任教到退休。其間,于1945年當選為美國語言學會會長,1960年當選為美國東方協會會長。趙元任先生是一個罕見的語言天才,能說幾十種方言,精通多國文字,學識淵博,著作等身。語言學方面的研究體現了他一生的主要學術成就。他在漢語方言、語音學、語法學等方面都做出了開創性的研究和杰出的貢獻。
《語言問題》是趙元任先生1959年在臺灣大學以“語言問題”為中心所作的一系列演講的實錄,此書較有特色,它忠實地保留了當時演講的風格,是一部深入淺出的口語式的語言學著作。全書共16萬字,分16講來講述語言學及與語言學有關的一些問題,內容豐富且具前沿性,語言幽默生動,分析精辟入木,說理深入淺出,字里行間即可感知趙元任先生的博學多才和語言天賦及洞燭幽微的能力。限于筆者的水平和興趣,在此不可能面面俱到地來談論它里面的觀點和思想,現僅就語言的本質、語言的變化及規范、語言的教與學等問題談一些感受和體會。
一、關于語言的本質和特征
“語言是什么東西吶?”趙元任先生在第一講里就開宗明義地說,“語言是人跟人互通信息、用發音器官發出來的、成系統的行為的方式”[3]3。這定義雖簡短,內容卻很豐富,它說明了語言的交際性,語言的社會性,語言的物理性,語言的系統性等重要特征。而且把“信息”概念一詞引入到語言學,這樣的提法在語言學界是比較早的。這充分反映了趙先生對當時的信息科學的吸收和借鑒。用短短的28個字就把語言的本質特征給概括了出來,充分顯示了他的睿智和對語言的洞悉。接著他說語言具有五個基本的特征:第一,它是一種自主的、有意識的行為。第二,語言跟語言所表達的事物的關系,完全是任意的,完全是約定俗成的關系,這是已然的事實,而沒有天然的、必然的關系。第三,語言是一個人類社會的傳統的機構。第四,語言同時富于保守性,也是跟著時代變遷的。第五,任何一種語言,是一個由比較少的音類所組織的有系統的結構[3]3-5。不同的語言觀對語言有不同的認識和定義,趙元任先生的語言觀可以說是博采眾長,自成一家,他對于語言的看法和論述,今天看來依然是精辟中肯的。
趙元任先生把語言看成是一種行為方式,顯然是汲取了行為科學的理論,這也是布龍菲爾德的行為主義語言學的一個重要特征。但與布龍菲爾德的語言觀比較而言,趙元任先生的語言觀更為合理科學。布氏認為語言是一系列刺激和反應的行為,這種行為明顯地帶有被動色彩。而趙元任的語言行為觀則是一種有意識的成心的行為,是主動的。第二個和第五個特征來自索緒爾的語言觀思想,索緒爾認為語言是音義結合的符號系統。語言具有任意性、系統性。但趙元任先生不局限于此,在吸取眾家之長的基礎上,他發展和完善了對語言本質的看法。總體說來,索緒爾的語言思想認為語言是一種靜態的、自足的、封閉的系統。而趙元任先生的語言觀則是一種動態的、開放的系統。他所說的語言的第三和第四個特征就是很好的佐證。所以,他對語言的看法更加準確、合理和科學。而且在論述的同時,他總能舉出一些淺顯易懂、生動有趣的例子來說明問題,娓娓道來,就如拉家常一樣,沒有板著面孔式的說教,讀來常常使人有豁然大悟、茅塞頓開的感覺。
二、關于語言的變化跟規范
關于語言的變化跟規范方面,趙元任先生從語音、語法和詞匯等方面都有深刻的見解和論述。蘇金智認為,趙元任先生對語言規劃理論研究的重要貢獻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推廣國語,二是文字改革理論[4]。
早在1916 年趙元任在《中國語言問題》中就提出了語音標準化的五個重要原則:(1)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考慮,要做到系統的一致性和簡潔性;(2)要與方言有最大程度的區別;(3)聲音要清晰優美;(4)要容易發音;(5)要與大多數方言有最大的一致性[5]。這五個原則,對于現代漢語的語音規范,我們認為仍然是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的。在《語言問題》的“何為正音”一講里,他的論述更為全面,他說“有好些地方你得要有一個規定,定了就大家公認就是這么讀法”[3]119。但是常常也要遵循習慣,不能隨便改,隨便定,而是“要看這個法律得不得民意”[3]127,即不能違背大多數說這種語言的人們的習慣,要得到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承認和擁護,也就是要考慮到“讀音的群眾性”[6]。但如何掌握這個尺度呢?他說:“得依照法律的手續來提議跟修改:什么音應該算是已經不存在了,什么字應該照事實來改。”[3]127因為“常常有擾亂的情形,就是有時候錯了,將錯就錯,錯了幾百年,沒法子改了,就是錯了幾十年也很難改,就成了‘習非成是’的局面。你改了反而覺得太怪了”[3]119。既然如此,我們就得承認事實。“既成事實,你沒法子不承認的。”[3]124但這是不是說我們在語言面前就只能聽之任之,無所作為呢?當然也不是的,我們也可以提前做一些挽救,怎么來挽救呢?他的建議就是人們“不必提早來鼓勵錯誤的說法”[3]124,這樣“或者還可以挽狂瀾于未倒”[3]125。
在《什么是正確的漢語?》[7]一文中,也可以透見他的語言規范觀,他說在對待語言的正確性問題上,不論是就一般語言而言,還是具體就漢語而言,他肯定不是死硬的純語派。那么,什么是正確的語言呢?他認為這“要看什么場合適宜于說什么話和說話人(或寫作者)是什么身份”。但“語言的正確最終是絕對的規定”。在《語言的描寫和規范問題》里,他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我們應該是見什么人說什么話,見什么事說什么話,對什么事說什么樣的話[8]。語言是有多種體裁、多種場合的用處的。最重要的是要看用得是否得體,他認為“用詞得體不得體這是大前提”[9]。基于這些思想和觀點,筆者的理解是,第一,語言規范的標準應該是發展的、是動態的,而不是一成不變的、靜態的。正如他所言,語言不是固定的,是老在那兒變的,一代一代都不同[3]129-130。因而,“規范化的工作不可能一勞永逸,需要經常進行”[10]。第二,不同的場合可以有不同的規范標準,規范的標準不是對與錯的問題,而是一個得體性和適宜性問題。第三,根據其具體的場合,規范的標準又應是絕對的。聯系到當下我們對于一種新生的語言現象——網絡語言的描寫和規范問題,趙先生的這些觀點和見解是很具有參考價值和現實指導意義的。
三、關于語言的教與學
趙元任先生一生中大半生求學和生活在美國,主要從事語言的研究和教學,特別是漢語的研究和教學。根據自己的教學實踐和經驗,再加上其本人深厚的語言素養,他對于語言的教學有著自己獨特的教學理念和方法。在《語言問題》里,趙元任先生專門花了一個章節來講語言的教與學的問題,即第十一講“外國語的學習跟教學”。在他的其它一些論文里,如《外國語教學的方式》等,也談到了語言的教學問題。從中我們可以窺見和縷析出他關于語言教學的理念及方法,他的一些教學理念和觀點,就現在來看仍然是精辟中肯的,是不過時的,對我們的外語教學及對外漢語教學等仍然具有指導和借鑒意義。
首先,他力主學習外國語文就要首先學習它的口語,學習活的語言。也就是說,外語的學習要強調交際性,注重語言的運用,要聽說領先。在《語言問題》里,他用他自己在大學學習德語的經歷來告訴讀者怎么樣才是學習語言的最好方法。他說他學習英語和德語用的就是“中國的老習慣,書拿來總是哇喇哇喇的念,就跟背《四書》、《五經》一樣”[3]155。這“哇喇哇喇”里邊可是道出了學習語言的真諦!在《羅素的抽象原則跟語言教學》里,他說“學習一個語言,是要說過了若干分量若干種的話,說到了自己會說出像話的話來,以后就出口成話了。……把最多的時間用在說、聽這些話上頭……”[11]俗話說,讀書百遍,其義自現。從對文章的理解上來說,這是非常有道理的。就語言的學習來看,也是千真萬確的。學習語言就得多練習,正所謂熟能生巧(practice makes perfect)。他的這些觀點對于我們現在的外語教學和改革是具有參考價值和借鑒作用的。
其次,語言的學習要注意語用,不能脫離語境而單獨進行。因為字/詞的意義不是一個字/詞一個意義,一個字/詞可能有好多意義,字/詞只有在“整個句子才有用處,才有所說,才有所指”[12]。比如在詞匯的學習上,他認為詞匯的學習是學語言的最容易的部分,也是最難的部分。那么,怎樣才是學習詞匯的最好的方法呢?他說,“學詞匯的時候兒,你得在句子里頭學詞的用法,記的時候兒啊,要是光記一個詞等于你本國語一個意義,那樣子一定學得不對。你得記短語,記句,這樣子意義才靠得住。……你記的句子越多越好。所以學詞的時候兒啊,得要用整個兒的語句,有了若干數目的句子啊,當然你對這個詞的用法也就可以會了。”[3]158-159在《羅素的抽象原則跟語言教學》里,他也說,凡是學外語詞類的意義,沒有東西能夠代替實例上的用法。他認為“在實例里頭由烘云托月的法子把意義給托出來”是學習詞匯的好的方法。這也正是我們現在常說的要在語境里在閱讀中學習詞匯。像在語言培訓上取得很大成功的新東方和李陽瘋狂英語等就是運用這樣的方法。
再次,外語教學應以學生為中心,讓學生盡可能多地接觸所學語言本身。他說“在上課的時間,跟自修的時間,天經地義,就是想法子讓學的人跟語言的本身接觸,……在課堂上千萬不要耗費時間來凈用學生的本國語來談論這個語言”[3]159。他認為,上課的時間是有限的,學生聽外語的時間也是有限的,因此,應當盡量讓學生接觸外語,越多越好。
當然,趙先生關于語言學習的一些觀點從現在的角度來看也有不夠完善的地方,比如他說“語言是一套習慣,學習外國語就是養成一套特別的習慣”[3]156。這是典型的美國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對于語言學習的觀點,即聽說法,此法對我國的外語教學的影響是深遠的。習慣在語言的學習過程中固然重要,但近年來隨著認知科學和語用學等學科的發展,我們知道只按一套習慣是不能完全學好語言的。語言的學習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涉及到諸如情感、文化、認知等方面。
最后說一點額外的話,就是在讀趙元任先生的《語言問題》及其它一些論著時,他的博學和好學也給筆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博學體現在他能在文章里一會兒漢語(包括很多方言),一會兒英語,一會兒德語,一會兒法語,一會兒俄語,一會兒日語,引經據典,信手拈來;好學體現在他在文章里嫻熟地運用新的科學理論和方法。如在《語言
問題》里他就運用當時新興的控制論和信息學來對漢語的傳達問題進行分析說明;在《漢語語法和邏輯雜談》一文里,他運用德布羅意的波粒兩象說來闡釋語言和科學(或者說科學思維)間的關系問題[13]。這些當然同他具有深厚的數學和物理素養是分不開的,但更為重要的是他那種刻苦與求實惟新的精神。這只是筆者讀先生的著作的粗淺的理解和體會,要深刻了解趙元任先生的思想和學理,知微知彰,還得認真反復地多讀他的著作,肯定會開卷有益。
[參考文獻]
[1]蘇金智.趙元任學術思想評傳[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6.
[2]袁毓林.中國現代語言學的開拓和發展——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選[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前言iv.
[3]趙元任.語言問題[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4]蘇金智.趙元任對社會語言學的貢獻[J].漢語學習,1999(6):28-33.
[5]趙元任.The Problem of the Chinese Language[M]//吳宗濟,趙新那.Linguistic Essays by Yuenren Chao.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1-60.
[6]戚雨村.語言學引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85:114.
[7]趙元任.什么是正確的漢語[M]//吳宗濟,趙新那.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836-846.
[8]趙元任.語言的描寫和規范問題[M]//吳宗濟,趙新那.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529-533.
[9]趙元任.國語的語法和詞匯問題[M]//吳宗濟,趙新那.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534-540.
[10]葉蜚聲,徐通鏘.語言學綱要[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197.
[11]趙元任.羅素的抽象原則跟語言教學[M]//吳宗濟,趙新那.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586-590.
[12]趙元任.外國語教學的方式[M]//吳宗濟,趙新那.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522-528.
[13]趙元任.漢語語法和邏輯雜談[M]//吳宗濟,趙新那.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796-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