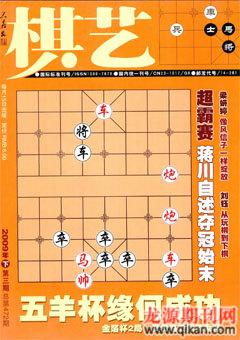偷偷的告別
閆登文
初春的雨,有些許的寒意。低沉的云。使人覺得壓抑。我望著窗外的細雨,心情迷茫。教練問我:“你怎么啦?心里有事?”我這才發覺自己的失態,忙強作歡顏地說:“沒事,耽誤不了明天的行程。”我一邊收回目光,一邊收拾桌子上的棋具。教練接著說:“這次去省城比賽,雖然不是大賽,但也十分重要,省內的兄弟棋隊基本上都參加了,算得上是一次武林大會,參加這樣的賽事,對棋手來說,很有益處,希望你能珍惜這次機會。”我咬了咬牙說:“沒問題,我會盡力的。”
回家收拾行李。
妻幫我整理衣服,她叫我去娘屋里坐會兒。娘自去年病倒后一直沒起來,四肢不靈便,口齒不清楚,生活不能自理。父親黑夜白天守護。妻也是跑前跑后。我在棋隊整天訓練,晚上回來,還要打譜、下棋,只能抽空過去陪娘坐會兒。娘就像小孩子一樣,見到我格外高興,不愿讓我離開,我也是能多陪她一會兒就盡量多陪她一會兒。
妻把我叫到屋外,低聲說:“這次比賽要半個多月的時間,你們棋隊派別人去不行嗎?娘病的這么重,你最好能守在家里。”我輕輕搖了搖頭說:“我也不放心娘。可是這次比賽規模大、質量高,我下了這么多年棋,還不曾遇到過,參加這樣的比賽,對提高棋力和心理素質都有好處,我怎么能輕易放棄?娘這邊就勞你多費心了。”妻無語,默默聽著。
這時,父親走過來,和藹地對妻說:“他說的對,你就讓他去吧。”妻解釋道:“我尋思,娘癱在床上,需要護理,家里地里那么多的活兒,他走了,娘心里難過,也辛苦了您。”父親堅決地說:“我沒事,撐得下去。只是走的時候別跟你娘說了,免得她又傷心。”
我擦了擦潮濕的眼睛,回到娘的屋里,往臉盆里倒些溫水,幫娘洗了洗臉,拿梳子把娘那斑白凌亂的頭發理了理,然后坐下陪娘說話。
第二天,我該走了。
雨還在下。蒼天無言,大地無語。我只能在心里偷偷地說一聲:“娘,我走了,您多保重!”
《棋藝》棋友群QQ:67199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