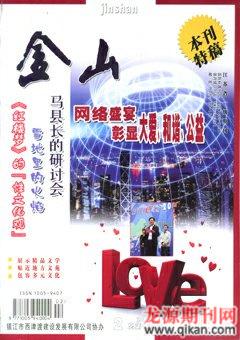媳婦熬成婆
申 弓
姐嫁去的地方叫龍鎮嶺,是個不大的村子,約有十幾戶人家,自成一個生產隊。姐夫是個靦腆的青年人,對姐很不錯。我們都認為姐嫁對了,在那里挺幸福的。
可姐回來時說,家里有個婆婆,鑰匙由婆婆掌管著,家里的一切都得經過她。婆婆挺嚴厲,姐沒有自由。這個自由,當然是經濟上的,比方想要買些什么,得要婆婆批準,得要婆婆開箱子掏錢。比方要回一趟娘家,也得婆婆準許,所帶之物,更得婆婆打點,想多給點都不行。睡得晚些她就要催,還不快睡,明早有事,也浪費燈油。你要起得晚些,她也要來催:還不起來,你看有誰起這么晚的?早起三朝賽一日。
姐的婆婆我見過,是姐嫁去的第三天我去“看朝”時見的,我叫她親家母,人不高,嘴巴扁扁的,那雙眼睛看人瞇瞇的,不太讓人喜歡。最大問題是我們家較窮,所謂窮,也是因為我們兄弟多,所處的生產隊分紅也低,加上我們還有兄弟三人在讀著書,姐初嫁到,心思還放在娘家轉不過來,常常想著要多資助一些給我們,只是礙著那嚴厲的婆婆。有一回,姐在婆婆裝好的物品擔里悄悄地多加了三升大米,卻被婆婆發現了,瞇縫著小眼看著姐說,你怎么可以這樣?這里才是你的家呀。等到有一日我不在了,還不知道會弄成什么樣子呢。因此,婆婆那串鑰匙無論什么時候都隨身帶著,從沒放開過。
姐每回回來,都感到很愧疚,總是跟母親傾訴家里的番豆婆怎樣嚴厲怎樣刻薄,其中最讓姐耿耿于懷的就是親家母褲帶上的那串鑰匙。
母親問姐,婆婆有多少歲了?姐說七十多。
母親便說,恐怕時間不多了,熬吧。
姐便這樣熬下來。
幾年后,婆婆便死了。
姐便接過了那串亮光光的鑰匙。姐算熬出頭了。
熬出頭的姐,責無旁貸地擔當起了家庭的總管,見天里要為柴米油鹽操勞。熬出頭的姐回我們家的次數越來越少了,有時半年也不回來一趟。到回來時,也不見姐多帶東西回來,見著母親,總是嘆息,這家太難當了。言語之間,對已故的婆婆沒了怨氣,相反倒有了幾分的懷念。母親卻感到欣慰,說姐真正長成人了。我知道母親所說的成人,也就是說姐已進入了角色。到了姐的兒子上學之后,姐再來時,不但沒有帶東西來,相反,每次總是說阿牛喜歡家里的什么什么,總是要滿載而歸。當然,這時,我們兄弟都已出來工作了,時常資助家里,家庭經濟已比姐好多了。母親因為生的兒子多,就這么一個女子,也就特別地疼愛,每回都總是幫著姐把帶來的袋或籮塞得滿滿的,并且還要提著送出一程,這正應了“十個女兒九個賊”的說法。
我想,姐要是討了兒媳婦,她的兒媳婦也一定要說她嚴厲刻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