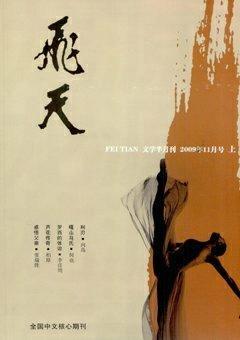《琵琶行》美學特征三題
彭 倩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唐代詩人白居易的敘事詩的代表作,《琵琶行》更是我國古代音樂詩的杰出代表,標志著中唐詩歌創作的一個高峰。
詩與音樂的聯姻,是中國古代特別突出的文藝現象。從發生學的觀點看,在藝術誕生時期,詩、樂、舞三位一體的本源性質是產生這一現象的基因。“詩與音樂的聯姻,主要指兩方面:一是詩之入樂(以樂配詩和以詩配樂)。二是以詩寫樂,即以詩形(包括詩、詞、曲)敘寫音樂的內容,如樂人、樂事、樂器、樂歌、樂曲的演唱演奏進程、樂聲形象的描寫以及音樂典故的運用,等等。后者,即我們所說的音樂詩”[1]。
《琵琶行》在我國古典詩歌中有著很高的美學價值,對它的美學特征進行研究既有利于更好地向學生講授,也對當今的詩歌創作、音樂文學的創作、音樂散文的創作有借鑒意義。本文從《琵琶行》的通感美、音樂美、社會美三個方面對其美學特征進行分析、探究。
一、視聽交匯、詩樂互動的通感美
在《琵琶行》中,白居易出色的音樂描寫使詩作具有強烈的視聽交匯、詩樂互動的審美效應,做到了“詩中有樂(樂聲),樂(樂聲)中有詩”的通感美。詩中音樂描寫視聽交匯審美效應的心理依據,就是現代審美心理學中說的通感。錢鐘書曾指出:“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即‘銷磨六門根識分別,掃而空之,渾然無彼此,視可用耳乃至用口鼻腹藏,故曰‘互用;‘易耳目之用則不然,根識分別未泯,不用目而仍須‘以耳視猶瞽者,不用耳仍須‘以目聽猶聾者也。西方神秘宗亦言‘契合所謂:‘神變妙易,六根融一。然尋常感官,時復‘互用,心理學命曰‘通感。”[2]無論是外在的直觀形式還是內在的心靈的藝術表現都離不開通感。如雪花飄落、駿馬奔馳、紅日升起、小鳥歌唱、樂器演奏等等,這些現象可以用音樂、繪畫、舞蹈、雕塑等各種藝術形式來表現,而每一種形式都可以把我們引導到一種充滿生命活力的藝術境界中去。這時,藝術給予我們的不單單是一種視覺或聽覺形象,而是通過我們的通感反應產生一幅動人的立體畫面。而我們的藝術通感能力發揮得逾充分,藝術品所呈示的畫面就逾廣闊、逾鮮明,也逾顯風采。在這里,關鍵在善于把一般的通感轉化為藝術的通感。“藝術的奧秘在善于把握對象的關系以及反映對象的各種形式關系,用各種手段啟迪人們的通感,以引起人們豐富的審美想象。為此,藝術表現上要善于把無限寓于有限,把瞬間凝結為永恒,通過個別來反映全體。這樣就要求藝術家在現實的描寫對象上選擇最理想的屬性,即能引起多方面感觸的特征和細節,把自己的美學理想寄托在‘這一點上,通過‘這一點達到整體形象的再現,從而給人以不盡的情趣與韻味”[3]。
音樂是以在時間上流動的音響為物質手段,通過旋律與節奏來塑造音樂形象的。這種能引起想象、聯想的聽覺形象,被詩人用文字描繪出來后,失去了聲音對人感官的強烈刺激性,但詩人廣泛地運用了比喻、比擬、摹擬、象征等手法,在充分發揮記憶、聯想、想象和通感等心理機能的基礎上,塑造了視聽交匯,詩樂互動的不朽的描寫音樂的詩歌藝術形象。《琵琶行》中有落玉盤的大珠小珠;有流囀花間的間關鶯語;有水流冰下的絲絲細流;有細到了幾近無聲的“此時無聲勝有聲”;有突然而起的銀瓶乍裂,鐵騎金戈……通過這些詩歌語言的杰出的描寫,琵琶女出色的演奏技巧及《霓裳》《六幺》豐富的音響猶在耳邊。人們往往說音樂是不能用文字來描寫的,文字在描寫音樂方面總是拙劣的。盡管如此,還是有大量的音樂散文、大量的音樂詩留在人類的文化史上,這足見音樂詩、音樂散文的藝術魅力及美學價值。而《琵琶行》則是中國古典音樂詩中的千古絕調。
二、敘寫樂人、樂事、樂器、樂曲的音樂美
唐朝詩歌的審美實質和藝術核心是一種音樂性的美,以詩寫樂在唐代也得到了最為燦爛輝煌的發展。《琵琶行》的音樂美是其美學特征的一個重要方面。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詩歌在節奏、韻律,動態、聲態以及情感流與音樂流的交匯融合;二是體現在內容方面,以詩寫樂,即以詩形敘寫琵琶女精湛的演奏技巧,動人的樂聲形象,展示琵琶女內心的情感世界與作者觸景生情,以自身的遭遇與琵琶女的情感交融譜成了一曲震懾靈魂的悲歌。作為敘事詩,《琵琶行》節奏流暢而富有變化,六百一十六言渾然不覺其長,瑯瑯上口,一瀉千里。押韻多變,增強了詩篇的音樂性。詩作在結構上起承轉合,起伏跌宕,深得樂曲結構之真髓。詩作具有攝人心魄的動態美與聲態美。這集中體現在對琵琶女演奏《霓裳》《六幺》的描寫中。如:“低眉信手續續彈”、“輕攏慢捻抹復挑”樂曲起始的慢節奏;“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樂曲進行到中段精彩絕倫的動態美及聲態美;“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曲終收撥當心畫,四弦一聲如裂帛。”樂曲高潮的演奏動態與聲態猶在視聽交匯之中。此外,與動態美相映成趣的靜態美的描寫也十分出色動人。如:“轉軸撥弦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均出色地描寫了動態美映襯下的靜態美,揭示了一個深刻的音樂哲學命題。
以詩寫樂,是以詩形敘寫樂人、樂事、樂器、樂曲的演唱演奏進程,樂聲形象(音樂唱奏的鳴響狀態)及音樂典故的運用。而音樂詩內容的音樂美依仗于文學表現手法的比喻、比擬、摹擬、象征等手法,在充分發揮記憶、聯想、想象和通感等心理機能的基礎上,塑造了視聽交匯,詩樂互動的不朽的描寫音樂的詩歌藝術形象,展示了詩歌從形式到內容的音樂美。
三、感事傷世、憂國憂民的社會美
社會美是《琵琶行》的又一美學特征。所謂社會美是指人類社會關系中的美,即社會事物的美。無論是山水詩、邊塞詩,抑或音樂詩既有自然美、藝術美的一面,也有社會美的一面。詩歌的創作主體是作為社會人的詩人,他總是要與所生活的時代、社會發生關系,要抒發詩人或喜、或悲、或憂、或憤的情感,從而體現詩作的社會美。“對音樂的感受,是主客體情感的交融,既受制于音樂的情感基調,也決定了聽者的感受能力與情緒心境,而在一定意義上說,后者的作用更大。無論詩人的感受和理解與歌曲或樂曲演唱演奏的情調基本一致或不完全相符,詩中的音樂形象永遠是詩人的再創造。音樂套上了詩的‘外套,就是詩人情緒的外化,就是融進了詩人個性特征的情感的寄托和傳達。所以我們說,一首優秀的音樂詩,就是詩人建構的一個自身的情感世界。”[1]詩人把社會底層的樂伎的遭遇和受排擠的正直的知識分子的遭遇相聯系,抒發自己的“天涯淪落之恨”,譜成了一曲震懾靈魂的悲歌。
白居易是一位關心人民疾苦,憂國憂民的杰出詩人。他提倡“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十分注重詩作的社會現實性。“我聞琵琶已嘆息,又問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凄凄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重筆濃彩地描繪了琵琶女與江州司馬,不同身份、不同遭遇,但相同的情感悲劇,揭示了中唐社會一個層面的悲情美。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震懾心魄。
被譽為“千古第一音樂詩”的《琵琶行》是白居易長篇巨制的傳世名篇。集中地體現了白居易詩作的社會美、通感美、音樂美。早在作者生前就已是“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千百年來為國人及海外好者傳誦,體現了強大的藝術生命力。
【參考文獻】
[1]中國古代音樂詩200首[M].魯文忠選注.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1993.7.
[2]錢鍾書.錢鍾書論學文選(第四卷)[M].廣州:花城出版社,1991.9.
[3]四川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藝術美學文摘 [C].成都:四川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1.
(作者簡介:彭倩,蘭州市外國語高級中學高級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