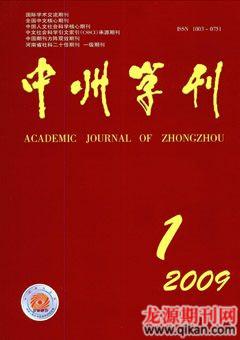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美學
在當代中國學術格局的演進過程中,美學研究的重要性正日益凸顯。繼20世紀50年代、80年代的兩次“美學熱”之后,我們似乎正迎來第三次美學熱潮。雖然其確切意義目前尚難以估量,但可以斷言的是,這次熱潮不僅呼應了消費社會的內在要求——感性化、肉身性的生存狀態本是美學的關注重心;而且表征著當代文化人的學術自覺,即純粹學問逐漸吸引了學者們的研究興趣。然而,一個不容諱言的事實是,在表面繁榮的背后,當代美學研究卻在實際上存在著“概念游戲”與“對象空泛”這兩大誤區。前者使得相關學術著作沉溺于話語的解構游戲,而只是在知識論里兜圈子;后者則使一些研究者無視學科本身的邊界,而隨意地將“美學式”的命名賦予自己的對象。對于美學的明天而言,這自然是一個令人遺憾的結果。
實際上,這種結果的出現并非空穴來風,而是有著深刻的哲學史背景,這就是彌漫于20世紀初的那場聲勢浩大的“語言學轉向”。這次轉向的批判對象是古典美學關于意義本體的常規解釋,主要發起人是瑞士人索緒爾與奧地利人維特根斯坦。通過對語言與言語、能指與所指的分辨,索緒爾發現,語言活動與實際世界之間的同盟關系并非如我們素常以為的那樣有先天的合法性,而多半是偶然性的產物。一個無法被確認的孤立的語詞其實是飄零而空洞的,處于繁雜的形式系統中的語言活動必須以具體的“關系”為基礎才具備存在的意義。他由此下結論說,歷代美學家所樂此不疲追尋的美的“本質”不過是一場語言的冒險,是終究無解的思想烏托邦。而后期維特根斯坦提出的“語言游戲說”進一步強化了這一沖擊的力度。簡單地說,這就是所謂的后現代語境下反本質主義的實際境況,是美學的思辨之舟撞見的一個幾乎致命的險礁。
然而,值得慶幸的是,這次批判的力度雖然強大,卻不足以動搖以柏拉圖主義為代表的美學的存在之根。這是因為,“語言學轉向”雖然對現代人的觀念產生了富于革命性的影響,但已表現出明顯的負面作用。隨著“轉向”裹挾而來的“主義”在解構日常陳見的同時也沖擊了世界的意義本體,導致我們身不由己地陷入一種“為理論而理論”的陷阱中。在這個意義上,甚至可以說,“轉向”不過是又一次理論博弈的產物,它存在著誘導我們放逐理性、走向相對主義的內在危險性。顯然,這些都不是我們所要的。如果說人之為人的根本在于理性的清明,借助對美的追尋探究一個意義世界是美學研究的本義,那么,放逐理性將使我們的生活變得支離破碎,走向相對主義則使我們的靈魂無所皈依。因此,有必要重新回到美學的誕生之地,重新把握美學的原初意義,探究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美學的內涵。
眾所周知,美學的思辨之舟通常奉兩千多年前的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為自己最杰出的馭手。在柏拉圖看來,在變動不居的感覺經驗下面,有一種只有理性才能認識的永恒不變的實在,這就是居于超驗層面的“理念”。作為萬事萬物的原型,理念是美的本體,只有借助詩人的回憶才能依稀辨認。因此,柏拉圖主義努力回答的終極問題是:美是什么。亞里士多德則借助對經驗世界的把握進一步區分了人生在世的三種生活方式,即享樂的生活、政治的生活與沉思的生活。所謂“享樂的生活”以“快樂”為目標,是“多數人或一般人”的價值訴求;所謂“政治的生活”以“榮譽”為目標,是“有品味的人和愛活動的人”的價值訴求;所謂“沉思的生活”則以“德性”為目標,是“自足、閑暇、無勞頓以及享福祉的人”的價值訴求。所有這一切共同構成了生活的樣態或面相。因此,亞里士多德主義努力回答的終極問題是:生活是什么。總之,我們可以認為,對“美”與“生活”本質的追問是古典美學的基本問題意識。毫不夸張地說,在漫長的西方美學史上,這也是令后世諸多美學家殫精竭慮的核心問題。而在這個問題的背后,哲人們的終極目標是深刻地理解人生幸福的真義。站在21世紀的邊緣,我們必須承認,由于這些問題如此真實而具體,它們對當代人也具有永恒的現代性。在這個意義上,研究作為生活方式的美學就不僅是一種學術思考,更是對個體幸福的追求與把握。具體而言,這一富有意義的回歸需要取道于破除理論膜拜、關懷個體生命與弘揚普世價值這三條路徑。
破除理論膜拜是第一條必經之途。不加節制地信賴理論本是我們思想界的悠久傳統。無論是零敲碎打的古典詩論,還是舶來的西方“文論”,我們無不照單全收。而勃興于號稱“批評時代”的20世紀的諸多“主義”,更是被我們當做救世良方迫不及待地吸納進來。然而,一旦理論的熱潮呈現消退之勢,一旦冷靜下來清點自己的思想遺存,我們才驚訝地發現,這些名目繁多的“主義”不僅沒有起到被期待已久的作用,而且還導致美學思辨遠遠脫離了真實的生活。它們的命運也正如上文提到的反本質主義一樣。實際上,不是理論而是理性才值得我們重視與珍惜。這是因為,歷史上雖曾有過層出不窮、五花八門的理論,但它們永遠只是邏輯演繹的結果,是一個個外在于人的概念系統;而理性則歸屬于人性本身,是能夠體現人之尊嚴與價值的最內在的標志。
其實,歷代思想家早已為我們指出過這一點。且不說康德對啟蒙本義的詮釋表露出一種發自內心深處的自信: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我束縛的不成熟狀態,從而公開而勇敢地運用自己的理性,單單是柏拉圖關于二元世界的劃分,就已經建立在對人之理性的肯定基礎之上了。所有這些,無不在以一種更切近的方式告訴我們,如果漠視了理性的聲音,關于美的思考就不僅只能在話語符號之間飄蕩,而且無法體現人之所以為人的存在根據。換言之,作為一種對感性認識的理論把握,美學判斷只有建立在個體理性的基礎上,才能走出理論主義的迷障,才能擁有一種直指本心的力度。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珍視理性也同時意味著葆有一份對真理的信任與熱愛。在人類漫長而崎嶇的求真之路上,我們對真理的那一步步跌跌撞撞的靠近,我們在黑暗時代里收獲的那一縷縷光明,都是借助于理性的燭照。
關懷個體生命是第二條必經之途。“在這個世界上,除了生命之外,沒有任何重要的東西。”英國小說家大衛·勞倫斯的此番斷言讓我們懂得了一個知識分子的人文立場。但話題顯然才剛剛開始。值得繼續追問的是,究竟該如何理解人的生命?可以肯定的是,我們通常認為的身體與心理這兩重維度并不足以概括人的全貌。這是因為,如果說強健的身體是對感官特征的把握,健全的頭腦是對心理世界的總結的話,那么,還有一個重要的維度常會被我們忽略,這就是訴諸于個體情感的精神。可以想象的是,失去了對無限高遠的精神山峰的攀登,失去了對無限豐富的情感世界的體驗,我們終將有成為詩人艾略特筆下的“空心人”的危險。因此,只有身體、心理與精神的恰當結合,才能構成一個完整而立體的人。實際上,這才是生命的本義,是美學思想應該著力關注的唯一對象。也就是說,通過對以文學作品為對象的藝術精神的研究,美學試圖發現的是一個情感的汪洋大海,一個以生命的真、善、美為終極理想的浩瀚世界。
因此,這個意義上的美學實在可稱為一種人生之學。它不回避對于世俗生活的細致透視,因為正是這種透視構成了生命的基礎土壤,使我們得以駐足于一個更加切實而具體的領地。但這同時也意味著一種別樣的超越,因為沒有對現象世界的超越就沒有精神之維的提升。這種來自生活卻又超越生活的獨有姿勢構成了美學的存在方式,是對亞里士多德筆下的三種生活的融通與綜合。同樣,這個意義上的美學也可稱為一種情感之學。這是因為,在人的審美經驗中,不僅蘊含著對自然界的秀美風景的領悟,而且還包含有對人世間的感覺經驗的歸納,最終實現情與景的圓融合一,為本來堅硬而干枯的世界賦予一種靈性的光芒與存在的意義。
在這趟關懷人生的旅程中,必須著力強調的一個關鍵詞是:個體。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生命就是個體,而個體就是生命。這里之所以作如此強調的理由是,只有從個體人格出發才能真切地體驗他人的悲歡,只有在自我實現中才能擁有生命本然的燦爛。正如有哲人曾指出的,你越成為自己,你越接近全人類。這也意味著,在開啟美學的思辨之舟時,必須把根基落實于個體的人。然而,長期以來,一個讓人扼腕嘆息的事實卻是,我們常常心甘情愿地在集體主義的懷抱中迷失,常常不由自主地被英國哲學家波普爾所批判的“大詞”所籠罩。這導致的直接后果是,當我們日漸陶醉于“解放全人類”的集體夢想時,當我們在“宏大敘事”中無私地拋灑自己的生命激情時,你與我自己的生活卻被無情地忽略了,一個個切問近思、體驗生命滋味的機緣正在漸行漸遠。顯然,這不是我們的生活目的,也滿足不了我們對幸福的企盼。“美不屬于決定化的世界,它脫出這個世界而自由地呼吸”,如果別爾嘉耶夫這個善意的提醒還有其價值,那么走出集體主義的桎梏,享受生命內在的自由,就不僅只是一個美學發展的方向,而且正是美學本身,是美學存在的理由。
弘揚普世價值是第三條必經之途。弘揚普世價值是作為生活方式的美學的存身姿態。如前所述,由于后現代主義在理論界的流行,原本確定無疑的普世價值的存在一時間成了一個問題。“上帝死了,一切皆有可能”,這種玩世不恭的說法不僅隨處可見,而且已對我們的價值體系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在這個口號的指引下,消解崇高、解構神圣似乎變成一件光榮的事情,不加任何限制的懷疑主義也成為一些學者奉行不貳的學術圭臬。在此基礎上,美學研究呈現出碎片化狀態不足為奇。但這顯然不是我們所期待的美學研究的本義。眾所周知,在這個世界上有自明性的東西如正義、良善、公理等存在,這是一切人文學術得以推進的前提。而作為一門探討人的審美意識、研究人的直覺判斷的學科,美學同樣需要具備自己的自明性基礎,這就是共通人性。換言之,只有承認人性之相通,關于趣味的價值判斷才有自身的合法性;只有肯定情感之共鳴,美學的發展才顯得空間充裕、意義充足。任何借相對主義的名義消解人性基礎的企圖,都是對美學的犯罪。因此,必須旗幟鮮明地弘揚人類的普世價值,為我們當代的美學研究確定一塊更為闊大而寬廣的思想土壤。
作出這個判斷,并非要否認個體的獨特性。恰恰相反,正如我們曾指出的那樣,成為一個人就意味著確證自身的獨特性,發現自我對于這個世界的意義。而個體生命的基本要素,如感覺、情感、行動與思想等無一不是我之所以為我的獨有標志。比如,感覺的敏銳與遲鈍、情感的細膩與粗糙、行動的迅捷與滯緩以及思想的深刻與膚淺,所有這一切無不因其貼身性而顯得無比私人化。然而,生命的悖論又在于,這些要素又同時構成了價值世界的主要內容,成為我們走出自我、溝通有無的重要憑證。事實的確如此。且不說只有憑借感覺與情感的溝通,才能在“我—你”關系中擁有一份生命的自在。單單是我們永不止息的行動與思想就足以為這個暗淡的世界賦予意義。正如法國作家雨果所指出的,一個深刻的思想抵得上50萬軍隊。可以說,正是借助思想的力量,人類才從幽深的洞穴里轉過身來,揖別黑暗與蒙昧,最終擁有了精神的啟明。實際上,正是它們,共同構成了獨特性價值與普世性價值之間的張力。而在這個永恒的張力背后,是優美與崇高之間的辯證法,是值得我們無限追尋的人文理想。
總之,失去“美學”的生活,只能是枯燥干癟的動物化的生存樣態;同樣,忽略“生活”的美學,也必然會使我們的學術思考在概念游戲中自生自滅。因此,在消費主義時代里,必須鮮明地張揚與肯定原初意義上的美學。這是因為,肯定美學就意味著肯定一種富有意義的生活方式,肯定一種奠基于生活世界、在自由創造中存身的生命態度。從而,不僅為方興未艾的第三次美學熱潮,而且為我們當下的生活確立一塊踏實穩固的精神土壤。
作者簡介:王洪琛,男,文學博士,西安外國語大學中文學院副教授,歐美語言文學研究中心研究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