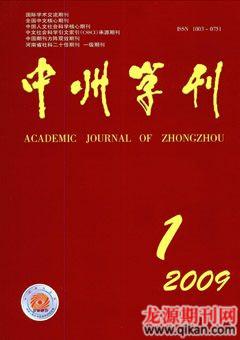存在一種審美的生活嗎
“美學與生活方式”筆談(四篇)
編者按:在當代中國學術格局的演進過程中,美學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繼20世紀50年代、80年代的兩次“美學熱”之后,我們似乎正在迎來第三次美學熱潮,其確切意義目前尚難以估量。一方面這表征著當代文化人的學術自覺;另一方面,這也是消費時代的必然選擇——感性化、肉身性的生存狀態本是美學關注的重心所在。然而,一個不容諱言的事實是,當代美學研究卻存在著視野褊狹與對象泛濫這兩大誤區。前者使得相關學術著作沉溺于概念的游戲,在知識論中兜圈子;后者的結果更是使某些學者動輒將自己的寫作命名曰“某某美學”,全然無視學科本身的邊界與范圍。實際上,所有這些誤區都源于我們對美學的原初意義的忽略——美學本是一種極富意義的生活方式,一種奠基于生活世界的、在自由創造中存身的生命狀態。正是基于以上認識,我們組織了這一組文章,嘗試從不同角度揭橥、闡發美學的原初內涵,希望能裨益于當下學術界的美學思考。
中圖分類號:B83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09)01—0225—11
無論從道德的觀察看多么不可思議,我們置身其中的社會,就大城市、傳媒、消費、大眾文化景觀而言,美學的核心詞匯與價值似乎正在重新建構一種社會表象,構成社會生產與消費的文化邏輯。體驗、感受和一切圍繞著“身體”建構起來的感性經驗,日益成為經濟與文化的共同目標,伴隨著充滿魅惑的身體表象通過文化傳播向一切社會層面擴展,似乎我們生活的整個世界都被魔法般地感性化了,使自我和社會都沐浴在純粹感性的光輝中。而美學本就意味著“感性”或“感性學”。
各種趣味和審美判斷圍繞著身體或身體性的需要被呈現出來,感性、感受力、欲望是一個時代的特質。連這個時代的哲學也從各種先驗概念范疇翻轉為身體經驗的話語,在形而上學和(政治)神學的本體論被消解之后,“身體”幾乎成為一種新的本體論,在文學藝術與大眾文化領域,身體及其欲望修辭構成了新的話語。無論是個體意識還是集體表征,身體及其感性經驗都已成為價值的核心體現。審美趣味似乎解構了一切固有理念,受其支配的時尚、娛樂、快感訴求重新建構了一種“審美的生活”。即使多數人的實際生活遠沒有實現這一美學趣味,至少在關于生活的表象空間已是如此塑造著。身體及其感性訴求被置于社會生活與時代思想的中心位置。身體及其欲望似乎再也不是靈魂的牢籠、惡的本源,不僅身體和圍繞著身體的表象塑造了一個審美的生活世界,身體自身也仿佛在這種過程中被“靈性化”了。充滿魅惑、欲望的身體被放置在這個時代商品拜物教的神龕里。
體驗、感性、感受力在文學藝術的歷史中一直表現為對狹隘的功利主義與工具理性的一種僭越,對個人經驗和社會生活領域進行著無止境的表象活動。感性經驗的表現不為別的目的,只為獲得更豐富的經驗,更復雜的感受,更大的敏感性。如同康德思想中所包含的寓意的實現似的,審美判斷或判斷力批判成為純粹理性和實踐理性批判意圖的完成,理性主義范疇內所建構的價值規范遭遇了感性批判力量的消解與重構。盡管看起來像是一種諷刺:我們自身置身其中的社會既沒有完成純粹理性批判,也沒有進行實踐理性批判,但在“武器的批判”之后也在某些時刻歸于感性化的生活世界。就現代世界的價值邏輯而言,感受力自身成為最終的價值,這是感受力、一種新的感受性所具有的“革命”意義。近代以來的文學藝術革命與創新,揭示了激進的審美感受性與陳規化的社會環境之間的緊張與沖突。基于趣味的審美判斷對人的感受性所具有的激發作用,把人們從被功利主義弄窄了的感覺領域引導出來。
如今消費社會已大規模回收了文學與藝術的感性革命的能量,消除了其激進性與批判性,并把它的感受性魔法般地轉換為發展欲望的一個物質基礎。在文學藝術的審美趣味和感性創造活動之后,是商業機制對趣味和感受性的接納與利用。在消費時代,感受力或事物的可感受性日益成為一種具有市場價值的東西。提供新的經驗、新的感受形式或敏感性,過去主要是文學藝術領域的事情,而今天則主要是文化產業和消費領域的事情。在越來越多的經濟領域,感受力或感受性的承諾開始擁有巨大的商業價值。人們似乎無法輕易區分什么是具有精神意義的,什么是物質生活,因為它們都同樣服務于人的感性經驗,服從于感受力的需求邏輯。
某些過去認為單純屬于經濟領域的事情,今天已成為滿足人們的趣味與感受力的方式。從一般的消費、娛樂活動到旅行、探險和極限運動,從小情調、格調與品位、趣味的滿足到驚訝、震驚經驗,都具有了文化心理價值,而這一切體驗都需要購買。物質生活或相當一部分產品指向人的經驗形式、人的感受性。消費活動開始指向一種獨特的感受,即對人自身的感受性與感受力的消費。對經驗的消費,成為一種最昂貴的消費,成為消費社會里最奢侈行為的無罪證明。消費各種經驗成為一種享樂形式。消費活動是為了獲得感受,而非單純地占有物質財富。只有包含了獨特的感受力的事物才值得人去感受。一切經驗甚至性經驗與情感,也逐漸成為被消費的對象,具有無限發展的神秘價值。
從驚訝、震驚經驗到恐怖體驗沒有不可逾越的清晰的邊界。發源于文學藝術的審美感受性正在發展為這個時代里的感性崇拜或感受力崇拜。感受力崇拜激發了一種經驗上的非道德性。這種非道德性的感受力在早期主要受到文學藝術的激發,而現在則受到市場經濟與商品形式的激發。感受力崇拜已經成為消費社會或娛樂世界的一種內驅力,成為現代大眾文化的內驅力。既然現代社會已經沒有可以信賴的理性主義的目標,感受性就成為唯一具有價值的、自我合法化的東西。
如此崇拜感性的時代似乎是一個完美的審美教育或審美經驗的時代,似乎實現了人類歷史上一切藝術家的夢想——一個全社會注重審美、注重感性經驗的美學理想國。然而,現實并非如此,審美的實現出現了偏差,感性經驗的至高無上也不是對純粹的經驗狀態的注重。在這個時代,一切不能物態化的東西、一切不能被物態化的感受和審美情操都顯得沒有價值而為這個審美的時代所遺棄,比如詩歌、內在感受、內心的教養,人們只相信那些能夠被物化的趣味、被物態化的審美經驗。如果沒有被物態化就不能被商品化,不能被看見,就不能進入商品的交換體系。一方面是“日常生活的審美化”,另一方面卻是審美經驗的內在交換、或審美經驗的象征交換比任何一個時代都更加微弱。與其說這個時代崇拜感性經驗、崇尚美學經驗,不如說這個時代崇拜一切經驗被物態化,崇尚使一切趣味與經驗的物化、從而被商品化,以便使之成為某種可以進入交換體系的商品,以便使藝術經驗的享受直接成為一種物態化事物的消費。在審美經驗物態化的崇拜中,終止了審美經驗的象征交換過程,一種主要發生在內心過程的經驗被物化形式所轉移,把不可言說的、總是包含著神秘與微妙要素的審美經驗轉換為確定的物質形態。
即使文學藝術的審美活動也必須作為物態化的形式而呈現,但仍與這個時代藝術經驗的物態化有著不同:我們時代的審美經驗的物態化直接作為赤裸裸的商品而出現,否則就不具備審美“價值”。在藝術消費者心目中,一切不能被物態化、不能被商品化的審美經驗都是沒有價值的,不能進入交換體系的事物就是非存在,就是無價值,同商品的邏輯一樣,交換價值取代了“使用價值”。這是社會未能進入“理智的和審美的成年”的未成熟性的表現,藝術作品成為商品拜物教的表現。藝術作品的拜物教削弱或刪除了審美判斷的批判性,使一切物化形態的藝術直接成為“好看的”或“美的”,審美價值的光暈為商品拜物教進行了加冕,卻沒有成為感受力與想象力的一種源泉,沒有成為重塑現實的力量。
日常生活的審美化或具有審美形式的商品并不能塑造一種具有深度的自我,正像商品的自身復制方式一樣,商品也以這種形式復制許多相似的或貌似有差異的個體,卻培育不出具有批評意識的審美主體。同樣的狀況發生在一切文化與藝術領域。審美經驗的自主性讓位于商品的規律,經濟的邏輯支配了文化的邏輯。與其說這是一個注重感性經驗的審美的時代,毋寧說是一個注重審美經驗物化形式的社會。在藝術成為商品之后,在審美經驗的物態化形式受到人們如此膜拜之后,藝術中不能被物化的詩性經驗、抗拒一切物化與凝結的藝術感受力反而絕少被人們所體驗。真實深刻的審美經驗,猶如古典時代的詩學思想所表述的,具有不可言說的特性,更難以被物化。它抵制著一切形式的物化,消解著暫時的物質形式和語言形式的凝結,在藝術經驗的形式化表達中,總是合法地潛在著表達形式的否認,或者說存在著對形式的暫時性的確認,保留著經驗的未確然性和變異,保留著再次言說的承諾。在藝術徹底地成為商品之前,審美經驗與審美教育總是保持著藝術自身對于物化形式的優勢,不信任任何形式的終極價值,它強調得意忘言,得魚忘筌。詩學的審美理想甚至對“言”這樣飄忽的“物化”形式都保持著懷疑,保持著暫時性的和瞬息性的觀點。當代物化的審美經驗與之相反,它對固化了的形式的膜拜遮蔽了審美經驗的內在性。可以說,這是一個輕視任何內心經驗與內在性的崇尚物化事實的時代。
當代社會“日常生活的審美化”等具有消費社會的特征,注重物態化、注重其商品形式與交換價值,而不是藝術與詩本身的特性。審美的生活不可以簡化為商品形式和器物的外觀,不是日常生活的趣味,不是環境的裝置化這樣一些內涵,也不是購買行為可以直接實現的“時尚”。對當代審美表象的贊美可能會導致這一觀察的盲目,助長消費形式壓倒其深刻的美學經驗的浮淺時尚之流弊。“日常生活的審美化”等時髦說辭放棄了判斷力批判,使所謂“生活的美學”成為商品拜物教的一部分。日常生活審美器物化的后果,使趣味與審美都只能作為個體消費者的孤獨性來體驗,而不指向一個審美表現的公共空間的塑造。然而,審美領域是一個從輕微狀態的愉悅感受直到人類復雜經驗及其伴隨感受的表達與傳遞的廣闊空間,包括古典美學所關心的對苦難、痛苦的經驗、恐懼、憤怒與同情等感受的表達。
正如康德在論述審美判斷時所說,“這種情感不論多么模糊,卻具有某種道德的基礎”,趣味或審美判斷是個體自由的一個根源,審美判斷同時也是“共通感”的保障。比起“知性”活動來,趣味或“鑒賞有更多的權利可以被稱之為共通感;而審美(感性)判斷力比智性的判斷力更能冠以共同感覺之名”。他把審美判斷定義為這樣一種評判能力:“它使我們對一個給予的表象的情感不借助于概念而能夠普遍傳達。”在康德看來,審美活動保障了一個基于判斷力之上共通感的社會,這個社會不是建立在任何先驗的未經反省的真理和不受批判的權力概念上,而是奠基于一種審美判斷的共同體。美學既存在于“個人的感受”,也存在于個人的感受與審美共同體的交流、共鳴之中。審美活動的“觀眾”組成了公共領域,美好的事物、言行與生活,是由觀眾的注視、判斷與評論塑造出來的。沒有人,沒有觀看,沒有判斷,美好的事物就不會表現出來。共通感或美學經驗的可傳遞性賦予人們作為觀看者的審美判斷力。事實上,在康德看來,“觀眾”這一概念具備公民社會的意義,而具有“共通感”的審美判斷則是某種政治共同體的道德基礎。
觀看者或觀眾的審美功能及其所延伸的道德情感體現在感受或感覺經驗的表達能力之中,趣味、鑒賞或“感覺”不是天才的特權,它們植根于經驗可傳遞性的基礎上。審美感受不僅是個人化的,也是最可供分享的經驗。經驗之所以為經驗,正是為了被分享。雖然審美經驗一再聲稱它的不可言傳性。不可言傳依然建立在有效的可分享經驗的實踐與多種文學藝術的中介形式中。審美情感、感受、體驗的可傳遞性與可分享性,正是共同體形成的基礎。正如康德所說的,當我們感受或判斷時,我們是作為“共同體的成員”去感受和判斷的。因此康德的政治思考可以在一個“自然的”、“感官的”和已經“社會化了的”基礎上發展,他強調“美的經驗性的興趣只在社會中”,而人的社會性沖動與屬性“是屬于人道的特點”,那么,我們必須把審美判斷視為我們能夠借以向他人、“向每個別人傳達自己的情感的東西的評斷能力”,視為屬于每個人的人道力量而加以促進的手段。這就是為什么審美判斷力中的“情感由于什么才會被仿佛作為一種義務一樣向每個人要求著”。康德這樣理解擺脫了愚昧的文明人:那就是他是一個樂于把情感與體驗傳達給他人的人,不能和他人分享共同感受是不能讓人感到滿意的,“每個人也都期待和要求每個人對普遍傳達加以考慮,仿佛是來自一個由人類自己所頒定的原始規約一樣”。在人類社會,關于感覺經驗的普遍可傳遞的理念“幾乎是無限地擴大著它的價值”。
共同體的概念使得開放性的精神成為可能,感受、思考與想象、經驗的可傳遞性能夠使我們獲得自我解放,并且達到一種相對的公正,這是判斷必須具備的。我們可以把產生于人類社會的一切情感與感受都納入整個審美判斷領域。感性和審美判斷之所以在康德看來是純粹政治的,屬于共同體的屬性,遠不是一般理解中的形式主義或感覺主義,是因為審美判斷力首先是一種“不要求概念”的可傳遞性、非概念的溝通能力,而且會引起普遍的共鳴。審美經驗與傳達體現為一種“自由的合目的性”,并且揭示了“我們的評斷能力從感官享受向道德情感的一個過渡”,不僅我們由此會被更好地引導向合乎自由目的地從事于審美活動,“也會使人類的一切立法所必須仰賴的諸先天能力”中的一個環節得到體現。這也意味著“從快樂到善的過渡”。
判斷力批判契合了康德對整個人類共同體和“永久和平”的渴望和憂慮:不是消滅差異與沖突,而是借助由感覺與情感“經驗的普遍可傳遞性”建立起來的判斷,審美經驗的“共通感”所形成的“開放性的精神”,預示了一種普世性。恰恰是審美判斷力使我們普遍意識到,作為共同體的成員,可能正是這一點預示著和平或“和諧”的可能性。審美判斷力意味著一種敏感性的培育,分享一種感受和情感體驗具有社會倫理的意義。在公共生活中,情感經驗的可傳遞性以及建立在可傳遞性基礎之上的共通感,產生了非強制性的社會化作用。依賴經驗的傳遞、分享與共鳴,人們建立起與他人的溝通能力,塑造出一個注重經驗的傳遞能力與注重表現價值的社會。正如阿倫特所指出的,康德的第三個批判,即判斷力批判,可以被解釋為建立政治哲學的一次嘗試。政治哲學的原型恰好是對美的判斷,因此被定義為“一種通過神奇的方式將特殊性與普遍性結合起來的能力”。
審美的生活,即建立在經驗的表達、情感的表象與話語自由傳遞能力上的生活世界以及公共社會對此經驗的分享和情感的共鳴,我們不僅能夠在文學藝術領域,也能夠在某些日益艱難地爭取著表達自由的傳播形式中窺見這種微弱的希望,可以看到一種以預言方式存在著的、也是以有限的表達實踐存在著的審美的政治共同體的某些端倪。這個政治共同體建立在審美判斷基礎上,建立在情感與生活感受的可傳遞、可分享的經驗表達之上。這好似一種道德家的空想,但也是有限的經驗事態。我們從中可以找到一種非強制性的道德感情的起源。審美經驗的可傳遞性、可分享性以及審美經驗的共鳴作用,預示著一種比道德事實更可信的經驗,這好似在借助審美經驗的共通感將經驗的傳遞變成一種責任與義務。除了傳統美學所關心的從經驗到敘述、到“作品”的物化過程,除了消費社會將經驗與體驗制作成商品與服務型的物態化產品,審美經驗最終會變為一種有關美的生活政治嗎?會變成一種自由的政治共同體的根基嗎?
審美的“生產活動”與“實踐活動”不同。商品生產的固有限制,產品的客體化,審美活動的物化形態,將變化的人類經驗“物態化”了。在消費社會,審美經驗(和其他經驗一樣)被屈從于物化過程與功利主義。這一過程在一切“生產活動”和消費活動過程中已經存在。審美的生活不僅僅是對這一審美的產品的消費,而是參與一種以判斷力批判為前提的“公共社會”。真實的審美的生活是一種生活實踐,一種由經驗的表現所構成的“表象空間”。它不是一種現成品的制造或消費,而是實踐人的生活的最高可能性的方式。需要關注的不只是建造一種靜物畫一般的審美空間,或僅僅是擁有更多的物態化的藝術品——商品,而是一種促進生活中的人們能夠進行自由地表現自我、展示出自己的最高可能性的生活實踐。一種具有多元的精神生活同時又具有社會倫理意義的生活,意味著將揭示與表現、觀察與敘述等方面的“審美趣味”與審美判斷上升為一種具有社會共同體意義的表達實踐,塑造出“個人的感受”與共同體的共通感之間對話的社會空間。
作者簡介:耿占春,男,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教授,河南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