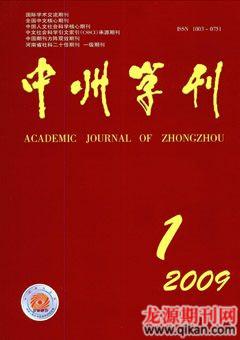中州古風與地方傳統的融合
龔建華 余 悅
摘 要:圍屋是贛南客家地區的標志性建筑,分布范圍廣泛,影響深遠,與閩西的土樓、粵北的圍龍屋同為客家民居經典。作為客家建筑文化的杰作,圍屋被眾多建筑學家所論述,但其文化內涵卻未被研究者所深究。如果以人為中心,從筑、居、思的角度切入,分析贛南客家圍屋的文化意蘊及其在整體客家文化中的建構意義,就能夠十分清楚地發現:贛南客家圍屋所體現的獨特人居文化是中州古風與地方傳統有機融合的產物。
關鍵詞:客家;圍屋;文化解讀
中圖分類號:I206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09)01—0164—06
海德格爾有一句名言,他說:“‘我是、‘你是意味著‘我居住、‘你居住。我是和你是的方式,即我們人據以在大地上存在(sind)的方式,乃是Buan,即居住。所謂人存在,也就是作為終有一死者在大地上存在,意思就是:居住。”①照這么說,居住不再單純是人類的一種生活方式,更為重要的或者說更為根本的是,居住已然成為人們體悟存在的必要形式。
作為客家建筑的代表,圍屋的筑造是歷代客家先民憑借自身掌握的先進版筑技術構建的安身立命的場所,是客家人生活追求的結果。然而,在建筑圍屋的過程中,客家人自覺或不自覺地把圍屋當成了他們追求文化獨立、彰顯文化魅力、體現自身存在價值的標志。如此一來,圍屋不再僅僅是客家文化的結晶,而且也是客家人文化追求的途徑。而贛南客家文化的核心是中州古風的余韻,又“重之以修能”,融合了地方性文化傳統在內的。一言以蔽之,客家文化是二元或多元一體的文化,贛南客家圍屋則正是這一文化特征的最佳體現。
本文的研究對象——贛南客家圍屋,即是指現存于今江西省贛州地區所屬縣、市、區,由客家人建造并使用的具有明顯封閉性、聚族而居的大型民居。本文所指“贛南”,是今江西南部現屬贛州地區的18個縣市。在贛州市范圍內,除個別城鎮因其方言(屬西南官話)和民居形式(屬徽派民居)與其他各縣市客家方言和土木混合結構為主的民居不同(這當屬非客家居地)外,其余各縣市基本上屬客家人居地,約有人口600余萬。據調查,贛南客家圍屋現在約有600余座,主要分布在贛州市南部的幾個縣市如龍南、全南、安遠、尋烏一帶,其分布范圍恰如江西省南部凸入廣東東部、福建西部的那塊“楔子”中。除此以外,在贛州中部的石城、瑞金、會昌三縣也分布有少量的土樓和圍屋;而于都、寧都、興國三縣則流行村圍。②
一、筑:圍屋存在的依據
1.十分突出的防御性能
防御性能是贛南客家圍屋最為突出的特點,特別是早期贛南客家圍屋所體現出來的防御性能最為明顯。對防御能力的要求高于一切,這集中體現了中國傳統建筑中內向凝聚性的文化因子。
許多研究圍屋的建筑學家很自然地將圍屋與東漢時代中原的鄔堡相提并論,指出兩者之間的諸多聯系。其中最為突出的一點,就是二者都突出了建筑的防御功能。事實上,建造圍屋的客家人最早的先輩恰是漢末中州之地的移民。經過幾次大規模的遷徙之后,從中原遷徙至閩、粵、贛交界山區的人群逐漸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民系——“客家人”。作為外來人群的客家人,來到閩粵贛三省交界之處,初始面臨的便是生活環境惡劣。贛南之地,歷來就有“七山一水一分田,還有一分是道亭”的說法,是農耕社會里典型的荒野貧瘠之地。惡劣的環境導致緊張的生存壓力,由此帶來的族群爭斗屢見不鮮,客家人與當地土著沖突激烈,宗族械斗也較頻繁,再加上常有野獸出沒、時起時伏的匪患,因此防御性便成為客家人建造圍屋時的第一要求。“筑”成為實現“居”的手段。一代代的客家人將整個族群對安居的渴望融進了獨特的建筑形制,從而建成了這些遍布三省之地易守難攻的鄔堡式圍屋,聚族而居。
從其外形上就可發現,贛南客家圍屋的防御性能集中體現為:封閉式外墻,墻體堅厚而高大,防御設施較為齊備。贛南圍屋的主要體型都是巨大的方形,厚實的外墻圍合成封閉的形式;四角均有高出的碉樓;底層和二層一般均不開窗,三層以上窗洞內大外小,并加設棚欄,有條件的圍屋會加設條石或鐵條窗框;圍屋外墻一般只設有一處大門,但卻機關重重。以烏石圍為例:一處大門共有三道設置,分別是木門、鐵門、水門。第一道大門門板極為厚實,外層裹有鐵皮;第二道鐵門懸置上方,以備木門被敵人攻破時即可將鐵柵欄放下進行阻擋;若是敵人采用火攻之法以破鐵門,那鐵門后面的水幕門恰好可以用作滅火。除此以外,贛南圍屋大多還增設了閘門以確保大門不失。大門以外,最受重視的便是圍屋的外墻。它們的墻體相當結實,厚度通常都在一米以上,而且在圍墻的底部常常以堅硬的鵝卵石勒腳,高達半人以上;墻體多用特殊材料,采用客家人獨有的版筑之法建構而成,與一些城鎮的圍墻相比也不遑多讓。龍南縣志曾有記載,20世紀30年代紅色蘇維埃時期,曾有白軍圍攻僅數十人防守的圍屋,歷經半月而無法攻破,足可顯見贛南圍屋的堅固。除去外圍的堅固樓墻,圍屋內部也為防守考慮周全,常常備有足夠的生活設施如糧倉、水井、畜圈等,即使緊閉大門也能維持圍屋內人們的生活。更有甚者,有的圍屋的內壁特設為客家人獨有的“面粉墻”,即以和稀面粉刷成墻壁,以備被圍絕糧時充饑度日。
客家圍屋融合了中州傳統的鄔堡建筑中“防御性”的建筑思維,便具備了贛南土著民居中原本未有的形制特點;但圍屋又結合了贛南建筑文化中的特有因子,例如材質的選擇、廳井的布置等,從而使其又迥異于中州故地的其它建筑,成為中州古風孕育于南國之鄉的奇葩。
總而言之,無論哪種形式的贛南客家圍屋,都在不同程度上體現了它良好的防御功能。在冷兵器甚至初級火器時代,圍屋讓居住其間的客家人得到足夠的安全保障,“安居”得以實現。當然,隨著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環境的變化,贛南客家圍屋的防御性能也漸趨淡化;而其內向、封閉的形式仍因能給人足夠的安全感而得以長久地延續下來,并在文化心理上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客家人,成為他們無法消磨的文化烙印。
2.高度聚居的龐大形制
作為中國建筑史上典型的大型民居,贛南客家圍屋聚族而居的特點十分突出,這也是由歷史和環境因素所決定的。客家人的幾次大規模南遷,都是在動蕩的歷史朝代中進行的。遷徙的人群也往往以家族為核心整體性地南遷。他們遷徙的目的地又是贛南、閩西、粵北這塊社會條件與自然環境在當時都頗為惡劣的地方,因此很自然地群聚一起,通族協力,共同抵御各種侵襲,謀取生存。另一方面,客家人所固守的宗族觀念,使得他們較為穩固地保留了傳統的封建家庭結構。彼此之間,以個體勞作得來的財富一定程度上以共享為主要形式,再加上以父系血緣關系為紐帶,這樣一來,整個家族的成員都經過利益和血緣兩層紐帶聯結起來。幾代同堂,數百乃至上千人聚族而居成為常態,因此能夠同心協力建成贛南客家圍屋這樣體形龐大、向心圍合的大型民居。
贛南客家圍屋體形之大、所住人口之多,在中國乃至世界民居中都是十分罕見的。圍屋中體形最為龐大的直徑可達80多米、樓層高達5層近20米,這樣的巨型民居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當下,有些圍屋雖然因為種種原因已經被居民放棄,但仍有諸多圍屋住有族人。如龍南的“燕翼圍”,四方形,每邊長50多米,高12米,共四層,內中可供居住房間達300多間;歷史上曾住有近千人規模,至今仍住有200余人。又如尋烏、安遠一帶的圍龍屋,規模大者有三圍環形圍屋圍成,占地數千平方米,500多間房;居住多達五代同堂,幾千人共居。贛南客家圍屋用它的龐大體形、堅固圍墻庇護著客家人的繁衍發展,如今依舊為圍屋內的人們遮風避雨。
3.獨特的造型、古樸的風格
贛南客家圍屋造型獨特、風格古樸,在建筑史上具有較高的藝術性。贛南客家圍屋由各個單獨的個體建筑組合而成,這種群體組合的特點使得圍屋的形體層次豐富,氣韻生動。
贛南客家圍屋中最具代表性的當然是方形圍屋。回字形的格局,從外墻向祠堂,由外向里在中軸線上逐次減低,各層建筑墻面也隨之減低,層次分明;在主立面上形成獨具一格的秩序構圖,富于韻律感與節奏感。而圓形的圍屋造型,則以一種渾然一體的態勢矗立于天地之間,層層圓環套置著方形的祖堂,通過外圓內方的布置,天地人三才的觀念就這么清晰而自然地展現于山嶺之間。圍屋那圓頂外形與蒼穹呼應,厚重的土墻與大地相連,根系于自然,氣韻生于造物,整體風格宛若天成。另外,馬蹄狀的圍龍屋,它的造型與前面兩者相比有很大不同:較為低矮的院墻,多層半橢圓式的的民居,風格也是非常獨特;堂前一池春水,屋后突起畫胎,正門橫屋瓦頂層疊而上,飛檐突起,錯落有致。圍屋中還有一種特例,即八卦形圍屋,它環環相圍,組合奇特,變化多端,群體造型生動協調。
總之,贛南客家圍屋的群體組合變化豐富,聚落高低錯落有致,整體造型和諧完美,以其特有的整體氣勢與古樸風韻,形成了與各地民居迥異的獨特風格。
4.高超的版筑技術
要想讓客家人的“安居”成為可能,那么“筑”的技術必然極為先進。贛南客家圍屋無論是其獨特的造型,還是高聳的院墻,抑或是錯落有致的格局,其文化心理得以實現的前提,就是客家人經過千百年實踐打磨積淀而成的版筑技術。
現存贛南客家圍屋中,大多以贛南常見的普通黃土為主要建筑材料,沿襲了傳統的建筑形式,在墻體建造中運用較多的是版筑墻建筑,即俗稱的“干打壘”。這是南方建筑中最為常見的版筑技術。它以預先樹立的木板為模具,當中填充濕度適宜的黃土,再以人力用“杵”筑實為墻,如此層層加高,直至達到所需高度為止。在贛南客家圍屋建筑中,夯土墻的材料大約可分為三類:一種是用一般性粘土,其中再填充鄉間常見的竹木筋夯筑而成;另一種是用三合土夯筑而成,所謂的三合土就是石灰、黃泥、沙三種材料,或石灰、黃泥、卵石三種材料;最為講究的客家圍屋,用的材料就更為精細,是在三合土中摻加紅糖、糯米飯、桐油等粘性物夯筑而成。這種材料筑成的圍墻極為堅固,硬度堪比堅石而韌性則實過之。
二、居——圍屋的人居文化
1.天人合一的思想觀念
在中華民族的文化記憶里,一直保留著關于“天人合一”這來自遠古的文化心理體驗。“天人合一”的提法,最早見之于《莊子·達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后來這個記憶被儒家學者尤其是漢代的大儒董仲舒所引用闡述③,而后即成為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記憶,源遠流長地被我們所傳承,并流轉于中華文明的各個方面,建筑自然不能例外。
這一點在贛南客家圍屋這里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先看贛南客家圍屋的選址,無—不是依山傍水。龍南烏石圍前那蜿蜒而過的小河,遠處一帶黛色的筆架山,圍后蒼翠的“龍脈”山。風習至此,即便在無水之所建造田屋時,亦必人工自行挖掘水塘,以合天地。尋烏孔田的曾氏圍龍屋即為此典型。再看圍屋內的布局:大門進入,左右兩口井,號為陰陽;房內布置等等,不一而足,均有文化蘊含。
天人合一觀念的靈魂,是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一致。中華傳統文化中所追求的天地人“三才”合一,在圍屋里得到了鮮明的體現。贛南客家圍屋中方圍、圓圍的整體房屋造型,深深契合著天人合一的文化思維。而其中的特例八卦形圍屋,更是與中國最為古老的《易經》中的文化一脈相連。研究客家圍屋多年的日本教授茂木計一郎曾經提出:“圓形土樓是母性,很像包容一切的子宮。”④其實相形之下,圍龍屋更像是一個孕育生命的子宮,“它前面的池塘,居前居下,且必然是半圓形的,它象征太極陰陽化生圖的屬陰的一儀,是充盛羊水的子宮的一半;羊水是滋養胎兒的陰精,是賦形稟陽之液;圍龍或屋后伸手部分居后居上,高昂為陽,是陽精生氣之所在。”⑤“三才”之中的人,正是在圍屋里實現了與天地陰陽的溝通與和諧相處。
2.血緣向心力的物化形式
曾有西方學者提出,中國是個親情社會,而諸多學者對中國文化經典的共同解讀也證實了這點。⑥這表現在國人的傳統思想或者說文化精神上,就是有著突出的父系血緣色彩。古代中國社會中,人群關系結構以父系血緣模式為主。由于這種關系模式的決定性地位的存在,使得人們無論是個體的日常生活行為還是集體的交往過程,都先天地沾染了親屬關系的影像。與這種血緣核心規律對應的是,生活于其中的人們,他們的思想與文化也就自然地會表現出強烈的向心性。同樣,講究血緣親情的中國式家族,必然地推崇父慈子孝、兄友弟尊的倫理關系,以此維系家族的和睦共處。但這種倫理要求若是從另一角度上進行解讀,也就往往說明,同輩之間的兄弟或者堂兄弟由于與上下輩分之間關系的趨同而相互之間競爭激烈,這又往往是導致一個大家族分崩離析的主導原因。因此,在國人的共居家族中,分外講究兄弟之間、妯娌之間的公道平均,極為忌諱偏頗失度。而這表現在贛南客家圍屋這種現今最大的家族聚居式民居上,就出現了兩個略顯矛盾卻又交融匯通的原則。一方面,所有的圍屋都以居中的祖堂為中心向四周逐次擴散,人們也按照輩分的不同分別居住于與祖堂位置對應的核心家庭中,前后的居住地位、條件都大為迥異,親屬關系在這里得到了極為嚴格的遵守;另一方面,居住在同等位置或者說同一圍圈內的家庭,每戶的格局驚人相似,除去一些裝飾的不同外,你很難分辨出它們之間的根本差異。由此可見,居住在圍屋里的客家人對血緣和血緣文化是何等的重視。如前所述,贛南客家圍屋的造型布局,其顯著特征就是向心性、對稱性與前低后高主次分明。這是以血緣和血緣文化為核心的客家傳統文化的物化模式。這種建筑以物化的形式,極為顯眼地體現出了客家文化精神中的核心概念。它既規定了住民的居住狀況,又通過它有形無形的力量影響了子孫的思想。
中國住宅建筑中的血緣文化表現,在傳統民居中并不鮮見,北方的四合院與徽州民居也是其中的代表。但贛南客家圍屋的向心性、對稱性與前低后高規律,卻是表現得最為突出的。相對而言,圓形圍屋的血緣向心性表達得最為直觀顯眼。這是由圓的獨特造型所限定的,圓圍中的所有房間(中心的祖堂除外)無一不朝向中心,處于圓弧之上的各個房間也很自然必須勻分才合理。當然,其他如方形、馬蹄形的圍屋,也都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這一文化原則。
3.向心內聚的空間布局
贛南客家族群無論何種類型、規模大小,都是聚族而居的。因此,宛如蜂巢的個體家庭小屋拼合而成的龐大圍屋,往往成為家族力量的象征。圍屋那高聳突立的外墻,圍內建筑的精心排列,所有房間的朝向,這些都具有濃厚的向心性。而這個所向的中心,毋庸置疑地集中在圍內那擺放著祖先牌位的祠堂。祠堂是供奉祖先靈位、祭祖和供典的神圣場所。它居于全宅中心,有著至尊無上的地位,也是整個圍屋家族強大內聚力的體現。
贛南客家圍屋有明顯的中軸貫穿,從而強調出中心所在;左右嚴格對稱,主次分明,結構嚴謹。在圍龍屋中,下堂、中堂、上堂沿軸線漸次升高。中軸線上最高的上堂,放置祖宗牌位,是一屋的中心所在。這一中心,不僅在平面布局上顯著,而且在立面上也明顯可見。整個住宅中,每個房間的地位都以相對于這一中心的位置而定,越近中心的居所,由輩分、地位越高的人居住。在圓樓平面布局中,也隱藏著三堂屋的中軸意識,而且祖堂居于整個圓樓中心,也表明了其至尊的地位。
雖然圍屋的祠堂多是單層建筑,遠遠低于它的外墻,也低于圍內的其它建筑,但整個圍屋無論是從平面還是立體的角度來看,所體現的正是中心擴散、向內聚集的文化含義。如同一位家族中的智慧長者鎮定居中、發號施令,周邊族人依令行事、排行有序、井井有條。總而言之,贛南客家圍屋強烈的向心內聚的空間布局,反映了聚族而居方式中必不可少的尊卑秩序,是封建倫理在建筑上的典型再現。
三、思——圍屋的“此在”與“彼在”
1.權力機制的體現
贛南圍屋的筑造起因是對抗外來的入侵,獲得安居的空間。但當客家人住進這一獨特的大型民居后,卻又為其中暗含的權力機制所束縛,成為被有效控制的群體。
法國思想家福柯說過:“建筑自18世紀末以來,逐漸射入了人口問題、健康與都市問題中。……(它)變成了為大成經濟—政治目標所使用之空間配置(disposition)的問題。”⑦在福柯看來,空間位置,特別是某些建筑設計,在一定歷史時期的政治策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邊沁(Jeremy Bentham)輻射狀規則之結構建筑的建議,現在已然成為經由建筑而實行權力集中化的代名詞,成為空間、權力和知識交織的典范性例證,它是“權力機制化約成其理想形式的簡圖”⑧。在我們看來,與福柯的述評對象同處一個時代的贛南客家圍屋,正是權力機制化的中國式體現的最佳代表。
贛南客家圍屋中權力機制化的的首要顯現,就是空間與階級的特定關系,或者說是空間布局的制度化。贛南客家圍屋的設計,包括中軸線上建筑物的分配,祠堂的位置,井、學堂等的坐落,體現的正是客家文化的權力構想。如前所述,贛南客家圍屋迥異于其它民居的最重要一點,就是它的建筑布局是以祖堂為中心等距離向外發散。其中,越是靠近中心的位置越被重視,安置其上的也是客家社會中的重點對象,包括學堂、水井等;而處于外圍的,當然是地位相對低下的、逐漸喪失話語權的建筑對象,例如水溝、圍墻等。與之對應的是居住于其中的人的身份,或者說附著于其上的階層差異:內層的住戶都是族長、長老之類的家族中的統治力量;依此類推,居住在最外圍的當然是家族中的普通個體。雖然生活在同一座圍子里,但你的鄰居依然是和你一樣的人,每個人依據自己在圍屋內的位置,身體力行著客家社會中的文化規矩:對圓心保持著敬畏,與同一周邊平等對話,警戒著自己的外圍。
當然,圍屋中的權力機制還體現了客家的或者說中國文化的另一大特色:對知識的敬畏。中國傳統社會中身份的認定更多的是職業性的。“士農工商”的劃分傳達出的文化意義,就在于對知識精英統治地位的接受與認可。因此,知識與權力便相互糾結。贛南客家圍屋中學堂的地位便僅次于祖堂;而充斥于各個圍屋建筑的“大夫第”、“進士居”,則更為直接反映出客家人對知識權力的膜拜。
2.從個體控制到“差異性萬歲”
我們可以看到,贛南客家圍屋在保持客家社會順暢運轉中表現出獨特的范式意義。它通過身份位置的對應型塑著個體,并以此為基點長期地影響一個既定的社會包括它的許多次團體。但是,“變”或者說運動,才是這個世界的根本法則,贛南客家圍屋又如何能置身事外?
在圍屋內居住的人們,“每個個體有一個地方,而每個地方有一個個體,以一個生動的工具邏輯,個體可被安置、認知、轉化與監視。在這個簡單的符號化中,方格里的每個孔洞都被賦予利于均勻使用有關紀律的技術價值。有紀律的空間的成功,有賴于對一個明確結構性組織的符號化。”依照文化制度圍屋被分割成每個小塊,在這小型舞臺上,其中的每個演員都是孤獨的、完全個體化的,并且持續可見的。福柯認為,對身體的控制有賴于權力的光學(the optics of power),而建筑恰恰細琢了這個鏡片。圍屋成為權力在空間中運作的工具。使用這些不同構造物等技術,比起建筑本身更為重要,因為它們容許了權力的有效擴張。贛南客家圍屋中各個房間幾乎并無對外的窗戶,圍屋外的光線是無法通過個體窗戶射入的;要想安全地獲得光線(話語、權力),個體必須走向圍屋內的廣場。向外的封閉性必然導致內在的凝聚力,割據的空間產生的是孤獨的世界。為了克服這巨大的孤獨,個體很自然地要向圍屋內巨大的集體低頭。于是,個體都被抽象化為一個本質的一般,人們在交往過程中習慣性地以“某某圍子里的”互相稱呼,對個體所做的評述也多是“某某圍子里的人怎樣怎樣”。在圍屋盛行的年代里,個體性悄然隱匿,正如幾年前熱演的“圍屋女人”所表達的也只是圍屋的一般性,或者加入了性別的因素。
當下的文化觀念認為,在任何傳統中,“一致性”(Unity)與“同一性”(identity)都是有問題的概念。為了達到這種一致性與同一性,整體制度的設計必須以整體化的敘事和單一化的視角為條件,而這恰是為當代人詬病的專制主義殘余。專制概念不是一個中性范疇,它壓制差異性,并且一手釀成了文化上的傲慢和排他性。圍屋所體現的文化傲慢就在于除去家族以外,再無個體的自由,各種個體自由性的抒發都必須受制于嚴格的約束。這恰恰是小說《家》給眾多中國讀者留下的突出的文化印象。
歷史發展的軌跡,必然決定著文化變異的軌跡。雖然一致性給圍屋內的人們帶來了安居的生活,但改變了的環境卻日益影響著圍屋人的意識,沖擊著他們的存在方式。根據筆者調查,自從新中國建立尤其是“土改”之后,圍內的人們興起了外居潮。直至改革開放以后,80%左右的贛南客家圍屋都被廢棄,少數尚有人居住的圍屋也呈現出人少屋漏的衰敗氣息。對于這種變化,當然可以從經濟的、政治的、環境的因素加以分析,但我們更認同的是文化心理的探究:居住者對個體性或者說差異性的追求是圍屋被廢棄的根本緣由。在圍屋的建造原則中,同一性和差異性是不對等的,也是不可比較的,它們有不同用途。可以說,同一性是圍屋得以存在的根本原則所在;一座圍屋就是一個集體,它所代表的是所有個體的一般集合。個體差異性雖然不是被完全禁止的,但也是作用有限的,它所能夠體現的只是圍屋同一性內部的細微差異。圍屋的建設者們用相似性的穩定性去建構一座文化居所,從而將客家社會錨定于其上,然后又通過圍屋形體,編創各種敘述去解除由差異性的威脅帶來的不安。
但是,個體性的追求是無法被永久束縛的。當外在的威脅已然消除,圍屋的圍墻保護顯然已經被居住者所拋棄,而由圍墻以及圍墻內的建筑形制帶來的同質壓抑卻被凸顯出來。萌動的差異性追求及對圍外陽光的渴求,誘使著一批批的居住者搬離那曾經給予過他們安全如今卻束縛他們發展的圍屋。
從客家人開始南遷的漢朝末年,直至20世紀70年代,集權主義一直是世界性的追求。整體的、宏大的、一致的,自古以來就是文化的理想范式;“他者性”(otherness)既然是相異的,就注定要被消滅,至少是被同化。圍屋的存在以及繁榮,正是這一文化范式的絕佳體現。而在當今的世界,卻是對“差異性”高呼萬歲的年代。這個時代的文化范式,用菲納芒(Joel Fineman)話來說就是:“一種故事,就是一種故事;憑借它,社會解決了、防止了秩序的癱瘓。而這種秩序,吉拉爾為它貼上了‘無差異危機的標簽,他把這種失序界定為文化特性的喪失——嚴重到可以稱之為文化自殺了。”而隨著現代化社會的到來,圍屋這一古典范式的代表作,自然也到了成為標本的時候了。
從標本的意義上來回望贛南客家圍屋,它是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是古代客家人思想智慧和文化素質的結晶。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它很好地滿足了客家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生理需要、心理需要和社會需要,并且形成了自身獨具魅力的人居文化。圍屋不再單純是人之居,而成為人之思之所在,成為客家人浸染自身傳統、習得客家文化的場域。
狄爾泰曾經指出:“如果生命的表達是完全陌生的話,那么解釋就沒有可能;如果其中什么也不陌生的話,那又沒有必要解釋了。”我們可以把這句話轉換為:“如果生命的表達是完全陌生的話,那么存在就沒有可能;如果其中什么也不陌生的話,那么又沒有必要存在了。”用這句話來作為對贛南客家圍屋的文化解讀似乎是合理的。
注釋
①海德格爾:《演講與論文集》,三聯書店,2005年,第154頁。
②村圍是指在贛南的一些地方存在的以中間房屋為中心建造的套圈式建筑,往往一個村莊即成一圍;與其它圍屋相異的是,村圍多以黃泥為墻,且一層者居多,尋烏縣的東團圍是其中代表。
③《禮記·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認為人只要發揚誠的德性,即可與天一致。漢儒董仲舒則明確提出:“天人之際,合而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號》)
④⑤茂木計一郎:《中國民居研究——關于客家的方形、環形土樓》,日本東京住宅綜合所研究財團,1989年,本文轉引自《土樓——客家人的獨特民居》,載《客家研究第一集》,林添華、廖潤德著,同濟大學出版社,1989年。
⑥例如對“仁”的解說,對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認識,都在說明國人的愛與希望都是由己為中心,按照親疏遠近的關系來劃分的,而劃分的最重要標尺就是人的父系血緣關系。
⑦“The Eye of Power”,published as preface to Jeremy Bentham,Le Panoptique (paris, 1977),reprinted in Gordon, Power/knowledge,p.1488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tr. A. Sheridan(New York:Vintage Books,1979).
⑧案查文獻,“圍”字作為民居代名詞,最早見于明末,如《安遠縣志·武事》載:“(崇禎)十五年,閻王總賊起,明年入縣境,攻破諸圍、寨,焚殺擄劫地方,慘甚。”“(順治)十年,番天營賊萬余,流劫縣境,攻破各堡、圍、寨。”又如《定南縣志·兵寇》載:“康熙三年七月,流賊由九連山出劫,沖城不克,旋破劉舍圍,殺傷甚眾。”康熙年以后,攻圍的記載漸多。因此,圍屋的出現,充其量始于明晚期。圍屋在贛南大量出現,并形成規模和特色是在清代中晚期。現存圍屋約70%都是道光以后所建。進入民國后,圍屋便少建,建國之后更是不復再建。
責任編輯:行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