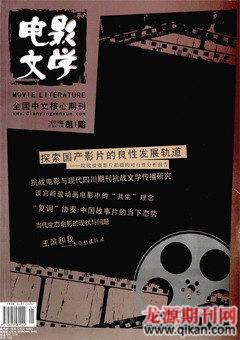“罪”、救贖、迷失
陳會力
[摘要]電影《鐵皮鼓》并不是一部闡釋宗教的電影,但是我們不能否認其中蘊含著濃厚的基督教意識和基督教氛圍。電影中蘊含著濃厚的“罪”與“罪感”;奧斯卡以自己的擊鼓和嘶喊的方式表達出對虛偽的成人世界的不滿與諷刺,但在嘶喊的背后卻隱現導演施隆多夫(乃至原著作者格拉斯)的困惑和迷失。“罪”、救贖、迷失不僅是電影《鐵皮鼓》的關鍵詞,也是理解作品的鑰匙。
[關鍵詞]電影《鐵皮鼓》;“罪”;荒誕;救贖;迷失
導演施隆多夫基本上是遵從于格拉斯的原作拍攝電影的,而且我們討論的出發點就建立在此電影基礎之上而不涉及原作,所以本文中所說的作者是指施隆多夫。電影《鐵皮鼓》并不是一部闡釋宗教的電影,但是我們不能否認其中蘊含著濃厚的基督教意識和基督教氛圍。影片中奧斯卡一家的“罪”開始于他的外祖母,并一直延續到了下面好幾代人。當奧斯卡出生之后,他無意間從他家人的身上看到了成人世界的虛偽和丑陋,于是在三歲生日的那天他就決定不再長大,他以一個“逼真的假摔”拒絕了成長。從此,他真的一點都沒長,而鐵皮鼓也開始陪伴他度過了童年,作者試圖以奧斯卡的擊鼓和嘶喊來表示荒誕世界的不滿和對正義的呼喚,但是在他嘶喊的背后卻不免隱現著作者的迷失和困惑。
一、《鐵皮鼓》中的幾重原罪
電影中有著濃濃的“罪”與“罪感”。在《舊約·創世紀》中記載著這樣一個很有名的故事:亞當和夏娃剛開始都很快樂地生活在伊甸園之中,但是有一天他們在蛇的誘惑之下,偷食了禁果。由于這觸犯了戒律,他們因此被趕出了伊甸園,從此人類也背上了贖罪的十字架。基督教認為在上帝面前,無論什么人都是有罪的,而且身負兩重罪孽:一為原罪、二為本罪。這即是說人類不僅承襲了人類始祖亞當犯下的背離上帝意志的原罪,而且還世襲著亞當不認罪、不悔罪之罪——本罪。人的一生也就是一個贖罪的過程。人要愛人如己,乃至懷著悲憫之心,去愛自己的仇敵,人必須認罪和懺悔,作為罪人懺悔,真誠悔悟,并在認罪和懺悔中走向“信靠”、獲得救贖和新生。而在電影《鐵皮鼓》當中,眾人的“奸淫”,(“奸淫”引自《新約·馬太福音》,文中“論奸淫”這一條提到:“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心里已經與她犯奸淫了”,更何況這里他們還要發生關系呢),更使他們“罪”上加罪,所以最后他們無一不受到上帝嚴厲的懲罰。
故事始于奧斯卡的外祖母安娜還未結婚的時候,有一天她在野外烤番薯吃,一個叫約瑟夫的年輕人為了逃避官兵的追捕而躲進她的大裙子,這個偶然的機會卻使約瑟夫成為奧斯卡的外祖父。一對不相識的年輕人在荒郊野外因為一個很偶然的機會相遇,于是很快就發生了關系,后來他們竟然把孩子也生了下來。我們不知道剛開始兩人的結合有沒有一見鐘情的成分,但是可以推斷的是他們的結合一定因為有欲望的驅使。基督教中強調的是禁欲,而奧斯卡外祖母的行為,顯然違背了基督教的教義,這是第一重原罪,雖然外祖母并沒有受到什么直接懲罰,但是她的懲罰可能要比其他人還要痛苦,而且上帝把她的這個“罪”一直移植到了下一代。因為是近親,奧斯卡的母親阿格內斯不能跟她喜歡的表弟布朗斯基在一起,只好嫁給了魚販馬特澤拉斯。從此,奧斯卡的母親就游走于他爸爸和他的舅舅之間。在結婚之后,由于阿格內斯與“舅舅”無法忍受相思之苦,每個星期四她都要出去跟她的表弟私通。這又是一重原罪。雖然阿格內斯也試著去找神父說出自己的痛苦,但是她不斷地懺悔只是為了維持與其表弟曖昧關系,她的虔誠換來的是可能比懺悔前還要強烈的欲望。“這里,虔誠的目的是功利性的,仟悔失去了信仰意義,變成了轉嫁良心重負的途徑和手段。”最后她的結局也只有一個,那就是死亡。當她發現自己懷孕之后,而自己的痛苦卻又得不到丈夫的理解。于是在無限的矛盾之中,她沒完沒了地吞食起了魚罐頭,最后由于吞食過量的魚而死,母親死后不久,同樣是欲望化身的舅舅也死于納粹的槍下。后來,外祖母帶了一個女仆瑪利亞回來,奧斯卡和父親都占有了她的身體。當瑪利亞生下那個孩子時,作者也就把故事的荒誕性渲染到了極點:奧斯卡的初戀情人成了自己的繼母,而兒子卻成了自己的“弟弟”。父親就這樣強行地奪走了他的初戀,父親的“奪人之愛”又是一個原罪。當蘇聯紅軍占領了但澤時,他死在了他們的槍下。至此,上帝完成了對所有有“罪”之人的懲罰。奧斯卡的外祖母雖然還活著,但是她的活著已經沒有意義,她在很早的時候就沒有了丈夫,之后又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兒子、女兒還有女婿,最后不得不跟外孫奧斯卡過完余生,這不能不讓我們想到余華筆下的福貴,那種活著只是一種凄涼。
作者通過對于充滿“罪感”的人的描寫,為的是影射出一個荒誕的世界。通過對荒誕世界淋漓盡致的渲染為的是達到對世界和自我的救贖。
二、“荒誕”之中的救贖
在電影《鐵皮鼓》當中,處處都是“荒誕”,這充分表達了作者對現實世界的理解,而作者真正所要達到的是在“荒誕”之中達到救贖。首先,從奧斯卡外祖母的經歷開始就很荒誕:一段發生于荒郊的感情,然后在一年之后當事人就消失,一個女人靠在菜場做小買賣把孩子(奧斯卡母親)折騰大,其次,奧斯卡的出生更是荒誕中的荒誕,連我們觀眾都很難判斷,奧斯卡是馬特澤拉斯的兒子還是他“舅舅”的兒子。再次,電影中的荒誕也和死亡聯系在一起。小說主人公的名義上的父親馬特澤拉斯被蘇軍士兵射殺的故事情節,死亡恐怖也同樣以荒誕的形式表現出來,從而產生了特殊的藝術效果。當奧斯卡與其他人被蘇軍士兵包圍在一間地窖里時,他把那枚納粹黨徽交還給了父親。其實以這種方式,他間接地把父親推向死亡的境地:驚恐萬狀的馬特澤拉斯試圖吞下這枚帶來殺身之禍的黨徽,但他卻被這塊難咽的納粹黨徽哽住了,臉漲紅了,兩眼圓睜,咳嗽,又是哭又是笑。所以,還等不到說投降,他早已被蘇軍射殺了,荒誕是現代西方美學中的一個范疇,是哲學家對于人的存在的一種關注。它描寫了這樣一個悖論:一個人的苦苦追求與永遠不可能實現之間的矛盾。所以,他只能做一個“局外人”。作者描寫這種“荒誕”“源于他對德國乃至整個西方現代歷史和現實社會的真實性的深刻把握以及對人的呼聲同周圍世界無理性的沉默之間的把握,他在成功地表現這種荒誕的同時,也就成功地表現了這種荒誕背后的真實。”“作者用喜劇的形式,表達了人類的悲劇,盡量不帶感情色彩地、冷靜地、甚至是戲謔調侃地描述他所看到的世界。”
可以說,奧斯卡在荒誕世界中扮演的是一個“敘述者”、“觀察者”的角色,他是超然于這個荒誕的世界之上。因此,奧斯卡的鐵皮鼓,還有他可以把玻璃喊碎的特異功能,其實都有一種文化上的象征意義。鐵皮鼓與奧斯卡的嘶喊是一種信仰、良知、道德、正義的象征。從他小時候玩伴們殘忍地逼他喝“湯”,而另一邊的成人卻熟視無睹地剝著獸皮,特別是他家里人一個個虛偽的嘴臉,他的眼中看到的是人性中不為察覺的惡與丑陋。“他
用鼓聲對付一切信仰與意識形態,用鼓聲來抵抗遺忘和抹殺歷史。”任何人只要敢搶他的鐵皮鼓(道義的象征),他就報之以嘶喊的話語方式,以此來震醒沉浸在麻木中的人們。二戰時期,納粹控制著主要的意識形態,“學校和醫院作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奧斯卡毫不留情面地震碎了老師的眼鏡(同化符號)和醫生的標本瓶(禁錮符號)。”作者描寫納粹舉行歡慶儀式的段落尤其精彩:當納粹打進但澤,奧斯卡的父親投靠了納粹。在一次去參加納粹分子的盛大集會上,奧斯卡躲在看臺下面用自己的鐵皮鼓兀自敲出的節奏,害得演奏納粹樂曲的樂隊亂了方寸,轉而開始演奏《藍色的多瑙河》。奧斯卡的鼓聲使猖狂囂張的納粹集會,變成了一場盛大的舞會,最后成為一場無聊的狂歡,從這既荒唐又嚴肅的情節當中我們能很清楚地看到作者對于納粹主義的反省與諷刺。電影通過一種夸張甚至于荒誕的表現手法,為了表示對現實的諷喻以及對其虛偽性的揭露,而奧斯卡拒絕成長也就是拒絕受到丑陋的成人世界的侵蝕,其次,鐵皮鼓與奧斯卡的嘶喊代表了奧斯卡一家甚至是人類自我救贖的一種符號,導演施隆多夫說:“其實他在這個電影里邊有兩個父親。有一個父親是波蘭人,在戰爭開始的第一天被殺了,然后另一個所謂的父親,在戰爭的最后一天被槍殺了。這其實有一定的寓意,他的母親也是因為受不了那種三角關系而自殺的。兩個父親,一個第一天被殺,一個最后一天被殺,可以說這就象征著奧斯卡的童年。”他混亂不堪的“出身”已經是一個謎,侏儒的事實更使他背上了十分沉重的十字架。當他在桌子底下第一次看到成人世界虛偽的時候,這可能要比他侏儒的事實要痛苦的多,于是,他以擊鼓和嘶喊的方式實現自我對他們一家的救贖。在他父親下葬的那一刻,奧斯卡把從不離身的鐵皮鼓一同扔進了墳墓,他決定重新開始長高。在一次被他“弟弟”的石頭擊中頭部昏厥醒來之后,他也完成了自我的救贖,奧斯卡就像鳳凰涅槃一樣實現了新生。
三、結語:從救贖走向迷失
我們很多評論者可能解讀到上面這幾點就止住了,但沒有看到《鐵皮鼓》中的“迷失”。我們往往只看到“鐵皮鼓”對于荒誕世界的顛覆與自我的救贖,卻沒有看到作者自身的困惑。奧斯卡也曾反抗權威,痛恨放縱,但是面對瑪利亞和戈莉拉的誘惑,奧斯卡終于也在男歡女愛的享樂中淪落了。在納粹軍營中當小丑的經歷不能不成為他人生永遠都無法抹去的污點。究其原因,是什么導致奧斯卡走向墮落?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欲”。因為人有永遠無法滿足的欲望,所以才會違背自己的初衷,走向另外一個可能連自己都反對的極端。按照第一部分的邏輯來看,其實奧斯卡本身也是一個原罪,也應受到嚴厲的懲罰。表面上他好像沒有遭到懲罰,但是,他的身世以及侏儒的事實已經成為他身上沉重的負擔,所以作者并沒有讓他死去。雖然說我們能從他的重新開始長大中看出作者還保留了對于未來的一點希望,但在教堂里,奧斯卡曾向圣像提出過發問。他將鼓套在了教堂中的天使塑像的脖子上,接著把鼓槌也交給了他,并一遍遍地發問:“打啊,121212……你是不會還是不打?因為你可以做任何事情。”神甫卻無情地終止了他的妄想。奧斯卡向上帝發問時所帶有的困惑,可能也是作者自己的困惑。猶太人馬庫斯的玩具店被毀于一旦,從這我們也不難看出作者心中的一絲悲觀。未來是什么,未來的路該怎么走?可能連作者也不知道,在他“弟弟”三歲生日的時候,奧斯卡回家了,他給“弟弟”帶來的禮物還是一面鐵皮鼓,這樣他把自己的困惑也傳到了更年輕的一代,“鐵皮鼓”繼續在迷失。
總之,“鐵皮鼓”在片中是一個具有文化意義的符號,它承載著人類所有的“罪”,同時它也擔著實現人類自我救贖的使命。作者通過奧斯卡的打鼓以及他的嘶喊,反抗的是現實世界虛偽的本質,以及對于純真人性的呼喚。影片表現主題時大量采用荒誕離奇的表現手法,寫出了作者對于二戰時期人性的懷疑和反思,但是其中不免流露出作者對于未來的困惑,未來會如何,只能讓未來去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