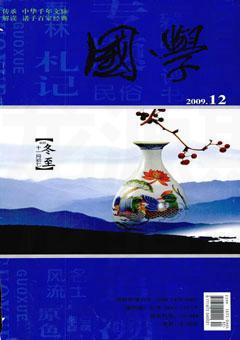可愛武漢人
易中天
武漢人其實很可愛。
外地人害怕武漢人,是因為他們不了解武漢人。武漢人有武漢人的優點。他們為人直爽,天性率真,極重友情。要說毛病,就是特別愛面子,要味。所以,和武漢人打交道,一定要面子給足。茍能如此,你就會在他們粗魯粗暴的背后體會到溫柔。
武漢人最大的優點是直爽。武漢人骨子里有一種率真的天性,說話都直統統的,很少拐彎,也不太注意口氣和方式。因直而爽,因爽而快,其結果便是快人快語。武漢人肚子里沒有那么多“彎彎繞”,喜歡當面鑼當面鼓。所以,毛澤東不但橫渡長江之先河,還寫下了“萬里長江橫渡,極目楚天舒”的名句,使武漢人大得面子,也大受鼓舞。于是橫渡長江便成了武漢市每年一度的大事。不過這事可真不是好玩的,非水性極好不可。但武漢人卻樂此不疲。
武漢人不太注意吃相。他們吃起東西來,往往“直呵直呵”地。尤其是吃熱干面。熱干面是武漢特有的一種小吃,一般做早點,也有中午晚上吃的。做熱干面工序很多。先要在頭天晚上把面條煮熟,撈起來攤開晾涼,拌以麻油。第二天吃時,燒一大鍋滾水,將面放在笊籬里燙熱,再拌以芝麻醬、小麻油、榨菜丁、蝦皮、醬油、味精、胡椒、蔥花、姜米、蒜泥、辣椒,香噴噴,熱乎乎,極其刺激味覺。武漢人接過來,三下五去二,眨眼工夫就下了肚。第二天,又來吃,永遠不會細嚼慢咽地品味,也永遠吃不膩。
愛吃熱干面,正是武漢人性格所使然:爽快而味重,干脆而利落。他們處理人際關系,也喜歡像吃熱干面一樣,三下五去二,從不裝模作樣。心直口快的性格使他們即便要說假話,也不那么順當。尤其是,當他認定你這個人可以一交時,他對你是絕對掏心掏肺地真誠。他為你幫忙不辭辛苦也不思回報,當然他可能在辦事過程中大大咧咧、馬馬虎虎,但真誠之心卻是隨處可見的。他們也會耍點小心眼,做點小動作,玩點小花招,在掏心掏肺的時候打點小埋伏,但往往一不小心就露出馬腳來,因為他們的天性是率真的。
武漢人的好相處,還在于他們沒有太多的“講究”——既不像北京人那樣講“禮”,又不像上海人那樣講“貌”。如果說要講究什么的話,那就是講“味”。武漢人的“味”確實是一種講究:既不能沒有或不懂,也不能太多或太大。
由此可見,武漢人的處世哲學比較樸素,而且大體上基于一種“江湖之道”。盡管武漢建市已經很久,武漢人也都多少有些市民氣,但他們在骨子里卻更向往江湖,無妨說是“身處鬧市,心在江湖”,與北京人“身居帝都,心存田野”頗有些相似。這大約因為北京周邊是田園,而武漢歷來是水陸碼頭之故。碼頭往往是江湖人的集散地,江湖上那一套總是在碼頭上大行其道。久而久之,江湖之道在武漢人這里就很吃得開,武漢人也就變得有點像江湖中人。
武漢人也像江湖中人一樣有一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觀念。比如他們把所有結過婚的女人統統叫做“嫂子”,這就無異于把她們的丈夫統統看作哥哥。他們當然也像江湖中人一樣愛“抱團兒”。“有恩報恩,有仇報仇”是武漢人的信念。在他們看來,一個分不清恩怨的人,也一定是分不清是非的人。
所以武漢人極重友情。重友情的人都記恩怨、講義氣、重然諾。這些特點武漢人都有。為了哥們義氣,他們是不憚于說些出格的話,做些出格的事。反正,武漢人一旦認定你是朋友,就特別幫忙,特別仗義,不像某些地方的人,沒事時和你套近乎,一旦有事,就不見蹤影。他們也不像某些地方的人,看起來一團和氣,滿面笑容,心里面卻深不可測。武漢人是愛憎分明的,他們的喜怒哀樂、臧否恩怨都寫在臉上。這就好打交道。所以,不少外地人初到武漢時,多對武漢人的性格不以為然,難以忍受,但相處久了,卻會喜歡武漢人,甚至自己也變成武漢人。
武漢人也基本上不排外。對于外地文化和外來文化,武漢人的態度大體上比較開明。不排外,也不媚外,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海貨、港貨和漢貨一樣平等地擺在柜臺上賣,京劇、豫劇、越劇和漢劇、楚劇一樣擁有大批的觀眾,不像河南、陜西那樣是豫劇、秦腔的一統天下。甚至武漢的作家們也不像湖南、四川、陜西那樣高舉“湘軍”、“川軍”、“西北軍”的旗號在文壇上張揚。武漢,總體上說是開放的,而且歷來是開放的。這種開放使得武漢人“既有北方人之豪爽,亦有南方人之聰慧”。這就無疑是一種文化優勢 有此文化優勢,豈能不大展鴻圖?
武漢人也敢哭。在武漢人的心理深層,有一種“悲劇情結”。因為他們特別喜歡看悲劇。武漢人的這種“悲劇情結”是從哪里來的?也許是直接繼承了屈騷“長太息以掩涕兮”的傳統吧!然而同為楚人的湖南人,卻不好哭。有一次,我們為一位朋友送行,幾個武漢人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抱頭痛哭,而幾個湖南人卻很安靜和坦然。湖南人同樣極重友情,卻不大形于顏色。他們似乎更多地是繼承了楚文化中的玄思傳統、達觀態度和理性精神,把人生際遇、悲歡離合都看得很“開”。要之,湖南人(以長沙人為代表)更達觀也更務實,湖北人(以武漢人為代表)則更重情也更爽朗。
因此,務實的長沙人不像武漢人那樣講究“玩味兒”。“玩味兒”是個說不清的概念,但肯定包括擺譜、露臉、愛面子、講排場等內容在內。說到底,這也是咱們中國人的“國癖”。但凡中國人,都多多少少有些愛面子、講排場的。但似乎只有武漢人,才把它們稱之曰“味”,而視之為“玩”。
武漢人這種文化性格的形成,有著歷史、地理、文化甚至氣候諸方面的原因。
武漢的氣候條件極差。上帝給了它最壞的地形——北面是水,南面是山。夏天南風吹不進來,冬天北風卻順著漢水往里灌。結果夏天往往持續高溫,冬天卻又冷到零下。武漢人就在這大冷大熱、奇冷奇熱、忽冷忽熱中過日子,其生活之艱難可想而知,其心情之惡劣可想而知,其脾氣之壞當然也可想而知。
事實上武漢人也確實活得不容易。武漢的自然環境極其惡劣,武漢的生活條件也相當糟糕。冬天,北方有暖氣,南方有艷陽;夏天,北方有涼風,南方有海風。武漢夾在中間,不南不北,不上不下,什么好處都沒有。別的地方,再冷再熱,好歹還有個躲處。武漢倒好,夏天屋里比外面還熱,冬天屋里比外面還冷。冬天滴水成冰,夏天所有的家具都發燙,三臺電風扇對著吹,吹出來的風都是熱的。那么,就不活了么?當然要活下去!冬天在被窩里放個熱水袋,夏天搬張竹床到街上睡。
在如此惡劣條件下挺熬過來的武漢人,什么苦沒吃過?什么罪沒受過?還怕什么?
所以,武漢人最坦誠、最直爽、最不矯情,有什么說什么,想什么干什么,而不必顧忌別人怎么想、怎么看。即便有人不以為然,他們也不會在乎。
同樣,最坦誠、最直爽、最不矯情的武漢人,也有著不同于北京人的“大氣”。如果說北京人的“大氣”主要表現為霸氣與和氣,那么,武漢人的“大氣”便主要表現為勇氣與火氣。北京人的“大氣”中更多理性內容,武漢人的“大氣”則更多情感色彩。他們易暴易怒,也易和易解;能憎能愛,也敢憎敢愛。他們的情感世界是風云變幻大氣磅礴的:大喜大悲、大哭大笑,甚至大喊大叫。而且,愛也好,恨也好,哭也好,笑也好,都很唰喇,都很到位。
武漢人確實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因為武漢是“鎮”。
鎮,重兵駐守且兵家必爭之天險也。武漢之所以叫“鎮”,就因為它地處北上南下、西進東征的咽喉要道。由于這個原因,武漢歷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戰爭的陰云總是籠罩在武漢人的頭頂上。所以武漢人“戰備意識”特別強。他們好像總有一種好戰心理,又同時有一種戒備心理。在與他人(尤其是生人和外地人)交往時,總是擔心對方占了上風而自己吃了虧。因而,武漢人經常擺出一副好斗姿勢。結果,往往還是自己吃虧,或兩敗俱傷。
所以,武漢人特別看不起膽小怕事、逆來順受和優柔寡斷。他們會梗著脖子死硬到底:“不服周(服輸)!就是不服周!死都不得服周!”
吃軟不吃硬,寧死不服周,這大概就是武漢人性格。這種性格的內核,與其說是“匹夫之勇”,毋寧說是“生命的頑強”。事實上,武漢也是“大難不死”。日本鬼子飛機炸過,特大洪水淹過,“十年動亂”差點把它整得癱瘓,但大武漢還是大武漢。的確,“不冷不熱,五谷不結”。過分的舒適溫馨可能使人脆弱綿軟,惡劣的生存條件也許反倒能生成頑強的生命力。
生活在惡劣環境中的武漢人不但有頑強的生命力,也有自己獨特的人生觀。這種人生觀用武漢作家池莉的話說,就是:“熱也好,冷也好,活著就好”。這無妨說也是一種達觀,但這種達觀和北京人不同。北京人的達觀主要來自社會歷史,武漢人的達觀則主要來自自然地理。北京人是看慣了王朝更迭、官宦升遷、幫派起落,從而把功名富貴看得談了;武漢人則是受夠了大災人禍、嚴寒酷暑、戰亂兵燹,從而把生存活法看得開。所以,北京人的達觀有一種儒雅恬淡的風度,而武漢人的達觀卻往往表現為一種略帶野性的生命活力。武漢的小伙子不像北方漢子那樣人高馬大、魁偉粗壯,卻也相當地“野”,各種沖動都很強烈。他們往往會成群結隊地在街上走,大聲吼唱各種歌謠,從“一個訝的爹,拉包車”直到種種流行歌曲,以宣泄他們過剩的生命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