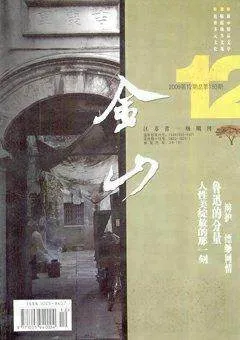一個似曾相識的早晨
眉山周聞道
其實,一月,一年,一生,又何嘗不是這樣;人生,就是一曲充滿變數的猜調,看你怎么去彈。
雖然從來就沒有人規定,一個早晨該從什么時候開始,我還是清晰地記得,這個早晨是從7點開始的。這個早晨的到來是附近建設銀行的那口大鐘,在這個時候把我從甜夢中搖醒。先是一串悅耳的音樂,清新,快樂,明麗,悠揚,像一些小石子,分輕重緩急,依次投入一泓清澈的湖,不僅聽得見聲音,還看得見水珠的跳動。過去常陪女兒練鋼琴,我知道這是猜調,不知是王建中,還是儲望華的。我對音樂的感覺很差,就像對早晨的感覺一樣,只能分辨出好與不好,舒服不舒服,不能精細,分不清邊際。因此,每一個重復的早晨對我來說,都是似曾相識。
過去曾對這鐘聲產生過厭煩,認為那是一種噪聲,在用音樂的分貝,污染這城市寧靜的早晨。時間長了也就習慣了。當每天早晨7時,鐘聲響起,便有孟浩然“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的感覺。由這鐘聲拉開早晨的帷幕,接下來的程序是似曾相識的——鐘聲過后,當是那個甜潤的女聲柔柔的播報,北京時間7點正;然后是一個美麗的提醒,選擇建設銀行,實現心中理想。這個早晨的開幕儀式,似乎就這樣結束了。其實不然。原因就在那個美麗的提醒。不知別人怎么樣,反正我有這樣的感覺,剛剛從一個夢境中走出,又步入另一種夢境,一個由選擇與心中理想交織而成的夢。
這樣的夢是似曾相識的。還是在讀小學時,或者更早,在童年星夜的仰望中就已播種。之后的行走,都是尋夢的過程,比如這個早晨。我伸了個懶腰,見身旁的妻子面帶微笑,睡得正酣,不便驚擾。心想,也許她此時正陶醉在一個美麗的夢境里,我應當讓她的愉快無限延續。一個人如果就這樣,不僅在白天,而且在夢境里也充滿了快樂,該是多好。記得,仰望星空時,我就夢想能長出翅膀,到月宮玩玩;讀小學時,我的理想是當一名手扶拖拉機手,駕著鐵牛,行駛在鄉間的路上——那些先輩們牽著耕牛行走了千年的路。我承認,我現在的夢要復雜得多世俗得多。比如此時,被那位女播報的提醒,勾起來的夢。選擇建行,怎么選擇呢?到里面去工作,當個科長行長,大筆一揮,百萬千萬的貸款就可出籠。這不可能,我的工作早已定型。比較現實的,是去成為他們攬儲的對象,支持他們得目標獎。可惜,我囊中羞澀,心血所得,只夠養家糊口。看來,我的理想注定只能與未知掛鉤,在似懂非懂、似曾相識中投放,就像不知道今天會發生什么故事。
時間已不早,9時還有會,不能像老婆那么瀟灑自在。輕輕穿衣起床,漱口,洗臉,剃須,一切必要的程序,都是似曾相識,或機械的重復。唯有做飯有些新意。吃什么呢?牛奶雞蛋是一種方式;面條、操手又是另一種選擇。只是,這些都要開爐生火,時間已來不及。我想到了冰箱里的陽坪奶粉,只需用開水一沖,放一些白糖或蜂蜜,邊吃沙琪瑪邊飲,那感覺也挺不錯。當糖水和沙琪瑪下肚后,心中便有一些踏實的感覺,仿佛未來的出發,不管行走多遠,只需這么一嚼一飲,就充實了能量,便不再擔心。
該出門了,司機已在樓下等,他一般都提前半小時到達樓下。開門,踏著石階,沿著小區的樓梯拾級而下。這是一天的真正起點。于是,我開始想今天的事。今天的日程怎么安排的呢?上午有兩個會,先是研究國債項目,那是一個民政救助站,一個早該辦的德政工程;然后是去企業慰問,這是每年春節前的例行公事,它使我變得清醒。記得,在去年慰問的時候,我們到了郊區的一個鄉村。那里依山傍水,林木扶疏,流溢著一種原始質樸的美麗。令我沒有想到并震撼的是,就在這美麗的所在,這個離繁華的城市十多公里的地方,竟有這樣的人家:兩間破敗的茅草房,在寒風中瑟瑟發抖;一條干瘦的黃狗,躺在院壩邊緣,汪汪叫了兩聲,便沒精打彩地打著瞌睡;一位體態龍鐘的耄耋老嫗,步履蹣跚地出門,一臉僵硬的淺笑。心里明白,扶貧只是一種象征,或官場的作秀。這樣的人家,怎么度過一個個的寒冬酷暑呢?我關閉了悠然的心窗,讓自己變得麻木,不愿去想,不敢去想。下午得參加一個團拜會,會看一些精彩的節目,證實這個世界的豐衣足食,歌舞升平。
新的一天就這樣開始,它從早晨出發。朝陽在寒風中照耀,小區的一切都是那么陌生而熟悉,一種似是而非的似曾相識。其實,一月,一年,一生,又何嘗不是這樣?人生,就是一曲充滿變數的猜調,看你怎么去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