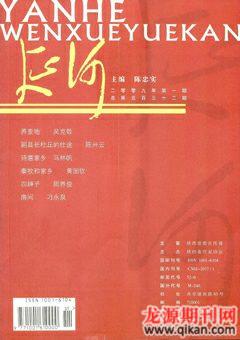閃念麻雀
2009-01-14 07:05:56周東坡
延河
2009年1期
一只鳥兒從一個枝頭躍到另一個枝頭,蹦蹦跳跳的,姿勢既不優雅,也不生動。但是,你注意到了,目光隨著它上上下下起落。
有風吹過,風搖動枝杈,打亂了鳥兒的舞蹈,你的目光一片斑駁。
它一定是快樂的,你對自己說。
快樂應該是一個符號,甚或是一個很卑微的符號,它像風一樣在自然界中往來穿梭,然后像蒲公英一樣悄悄地散落開來——你需要感知它的降臨,就像那只鳥兒。
而你確乎已經感知到了,要不然你不會看到鳥兒身處的濃郁樹木,看到濃郁樹木周圍浩蕩的森林,看到浩蕩森林之上的晴朗天空……
你的思想由此打開——信馬由韁也好,沉靜安逸也罷,你發現又可以與自己展開對話,而這一切,都源于那只不起眼的鳥兒。
這是一只什么鳥兒呢?
在城市中,我們司空見慣的鳥兒只剩下了鴿子,其他鳥類或退居鄉村或遁隱山林,它們的飛翔已經承載不了城市上空游蕩的粉塵與喧囂,只好選擇脫離。
而鴿子多不易呀,它沉著地與我們的日常生活為鄰,甚至學會了妥協,在廣場上散步,在樓群間盤旋,把自己當成人類的一分子。有時我會不由自主地想,鴿子的堅持究竟意味著什么?是否是“和平鴿”的頭銜讓它在無法從容面對生存的窘迫時不得不選擇隨遇而安?你聽,那些嘹亮的鴿哨在鋼筋混凝土間的回蕩是不是變了聲調?悶悶的,散亂的,無所依托的?
像我們。
其實,不用說我就知道那是一只麻雀,這根本無須辨別,它太平常了,平常到……我一時都不知道該說點什么。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