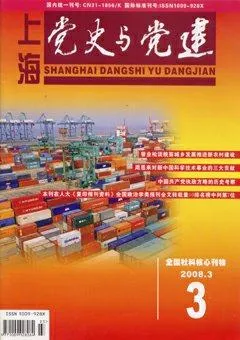盧新華:直面“傷痕”的心靈直白
口述:盧新華
采訪、整理:汪建強
采訪時間:2008年1月8
盧新華,1954年生于江蘇如皋。1978年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同年8月11日在《文匯報》發表小說《傷痕》一舉成名。大學畢業后任職于上海《文匯報》,不久下海經商,被稱為“中國文人下海第一人”。1986年自費赴美國加州大學讀書,獲文學碩士。2004年出版長篇小說《紫禁女》。在美期間,干過多種職業,現以自由職業者身份往返于中美兩地。
1、學校墻報上張貼了我寫的小說
1978年4月的一天,我起床后拿了洗漱用具正要去盥洗間洗漱,忽然發現我們所居住的學生宿舍4號樓底層的拐角處人頭攢動,男男女女的學生里三層外三層地擁擠著,爭睹新貼出的墻報左上方頭條位置的一篇小說,他們中有些人尤其是女生甚至還淚流滿面。我忍不住好奇地探過頭去,方知道大家看的原來是我入學不久后新寫下的一篇習作——《傷痕》。
看到自己的創作得到了同學們的認可,并引起了這樣熱烈的反響,我的心情既興奮又惶惑。因為就在作品剛剛完成后,我曾經滿懷信心地請一位本系教寫作課的老師幫我提意見并推薦投稿,誰知老師給我的評語卻是:“小說雖然寫得挺細膩,也很感人,但根據我曾經在編輯部幫著看稿的經驗,你的小說也存在著不少的理論問題,肯定發不出來的。我倒建議你多讀一些馬恩列斯和毛主席論文藝的著作……”。我于是聽從老師的囑咐,馬上去系資料室借書,并很認真地加以閱讀。然而讀后,我對這篇小說卻越來越失去信心,最后終于將它鎖進了抽屜。
《傷痕》敘述的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故事。“文革”時期,一個叫做王曉華的女中學生,在母親被張春橋一伙定性為叛徒后,為表白自己要做一個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于是大義滅親,毅然與母親決裂,還未畢業便主動申請到臨近渤海灣的一個小山村插隊落戶。然而,在她堅忍不拔地努力改造自己和世界的過程中,盡管作了十二萬分的努力,仍然無法擺脫“叛徒母親”帶給她的“政治陰影”。磕磕絆絆的入團經歷,曾經向往終于又不敢期待的愛情,讓她原本一顆火熱的心變得越來越灰冷,紅潤的臉龐也漸漸地失去了血色。
8年后,單位的一紙公函告訴她,所謂母親的“叛徒問題”其實是一起冤假錯案,她這才滿懷惶恐和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了探望母親的歸途。未料母親身心俱遭摧殘,沉疴難醫,竟未能看上女兒一眼,便撒手塵寰。
故事是以悲劇的形式結束的。當王曉華看著母親寫下的日記,讀到“雖然孩子身上沒有像我挨過那么多‘四人幫’的皮鞭,但我知道,孩子心上的傷痕也許比我還要深得多”時,心靈受到無比強烈的震撼。
為什么想到寫《傷痕》?起因是入學不久,有一次上作品分析課,老師講魯迅先生的小說《祝福》,提到許壽裳先生曾評論說:“人世間的慘事,不慘在狼吃阿毛,而慘在封建禮教吃祥林嫂。”這段話給了我極大的震動和啟發。那時,在揭批“四人幫”的過程中,我們的報刊雜志講得最多的便是說“四人幫”將國民經濟弄到了崩潰的邊緣。而我則忽然想到:“文化大革命”中貫穿始終的那條極“左”路線,給我們的社會造成的最深重的破壞,其實主要是給每個人的精神和心靈都留下了難以撫慰的傷痕。由此,下課后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有關《傷痕》的故事和人物便開始躁動于我的腹中。
2、小說被《文匯報》看中
《傷痕》最初的名字叫《心傷》,我曾經起過兩個頭,因為不甚滿意,就沒有再寫下去。后來我是在未婚妻家的閣樓上,趴在一部縫紉機上,從晚上六時許寫到零晨兩點,最終以淚洗面,一氣呵成的。
為什么會把王曉華插隊的地點寫在靠海邊的村莊?這是因為我父親是軍隊干部,我們全家曾經作為隨軍家屬在山東長島一帶生活過好些年,我對渤海灣,對海邊的生活比較熟悉和了解,寫起來人物和場景會感覺著比較得心應手。
小說完稿后,我一遍遍讀過去,心里很滿意,甚至還有些自負,以為至少會是寫作課上的一篇范文。未料不僅寫作課老師的評語不佳,幾個看過的同學的反映也不很熱烈。這樣,我連將這篇小說展示給別人看的勇氣也漸漸喪失了。
然而,在一個即將熄燈就寢的晚上,沉靜、穩重的小說組組長,班級墻報主編倪鑣同學輕輕地敲開我們宿舍的門,對我說:“嗨,過兩天要出墻報了,你小說寫好沒有?得交了。”我因為信心盡失,最初并沒有想到拿《傷痕》去交差,而是想重寫一篇,后來因為時間太緊,實在來不及,才迫不得已用《傷痕》去濫竽充數。我最近在國內見到已經成為“國際友人”的倪鑣同學,說起往事,他告訴我,他在拿到我的稿子后,曾仔細閱讀過,覺得挺好,于是又給另外幾個同學看了,并征求他們的意見。其中兩個同學持肯定態度,另一個同學則有比較多的批評意見。然而,他還是決定將它安排在最醒目的左上方頭條位置。現在回想起來,如果沒有倪鑣同學的慧眼獨到,或者小說被處理在墻報上一個很不顯眼的角落,所有有關《傷痕》的故事可能都將無從敘述了。
由此,我個人的生活道路也悄然改變了。那以后,復旦大學學生宿舍4號樓底層中文系文學專業的墻報儼然成了復旦大學一道特別亮麗的風景線,每天聚滿了閱讀的人群,先是中文系的,繼而又擴展到外系……后來通過中文系新留校的女老師孫小琪以及她的女友俞自由的渠道,敏感的《文匯報》編輯部編輯鐘錫知先生了解到了《傷痕》在復旦校園引起轟動的情況,旋即托孫小琪老師要去了我的一份手稿。
我后來才知道,稿子到了《文匯報》后,為慎重起見,報社馬上打出了小樣在上海文藝界廣泛征求意見。當時,整個社會都處在劇烈的新舊變革時期,一方面,“兩個凡是”的禁錮還在,另一方面,初步解凍后的思想界已日顯活躍。終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發表了,這不僅給思想界,也給教育界、文藝界、新聞界帶來了一股春風。在這樣的大氣候下,本來就傾向發表《傷痕》的《文匯報》編輯部更加受到鼓舞,于是,1978年8月11日,《傷痕》終于以一個整版的篇幅在《文匯報》發表……
3、小說發表后帶來的轟動
真可以稱之謂“一石擊起千層浪”,小說發表后,一下子“洛陽紙貴”,我的同學劉開平和我一起騎著自行車去大學附近的郵局買報,結果處處被一搶而空,只能失望而歸。發表的第二天,我們班的信箱里就塞滿了各界寄給我的讀者來信。據不完全統計,《傷痕》發表后,報社和我共收到近三千封讀者來信。這些信中的絕大多數都是因為小說和小說主人公的命運引起他們強烈的共鳴,故寫信對作品和作者表示支持的。很快,文藝界也隨之興起一股類似的創作思潮,后被中外評論家們廣泛地稱之為“傷痕文學”或“傷痕流派”……
值得一提的是,《傷痕》發表前,責任編輯鐘錫知先生曾代表《文匯報》編輯部和我談過一些比較重要的修改意見。依稀記得,意見大約有16條。重點的是小說第一句說除夕的夜里,窗外“墨一般漆黑”,有影射之嫌;故后來改成“遠的近的,紅的白的,五彩繽紛的燈火在窗外時隱時現”,同時加一句:“這已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了”;又有車上“一對回滬探親的青年男女,一路上極興奮地侃侃而談”,亦遵囑修改成“極興奮地談著工作和學習,談著抓綱治國一年來的形勢”;一直給王曉華以愛護和關心的“大伯大娘”,則改成“貧下中農”;而最后,因為據說感覺著太壓抑,需要一些亮色和鼓舞人心的東西,于是又有了我筆下主人公最后“朝著燈火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地走去”的光明結尾。現在看來,這些修改意見盡管折射出那個時代人們思維的某種局限,卻也真實地反映出《文匯報》同仁在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來發表《傷痕》時,所表現出的一種極其細致和負責的精神。
《傷痕》發表后不久,我便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成為“文革”后中國作家協會所吸收的第一批年輕會員之一,后來又被推薦和選舉為上海市青年聯合會常委,第四屆全國文代會代表。這些紛至沓來的榮譽,曾令我陶醉,繼而則引起我的警覺。為了更堅實地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抱著“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古訓,我后來決定放下所謂的“作家”的身段,從一個普通人重新做起,先是辭職下海經商,繼則出國留學。這期間,我陸續收獲了《森林之夢》《細節》和《紫禁女》三部長篇小說。而今,我正以一個自由職業者的身份往返于中美兩地。因為血管里涌動著的畢竟是中國人的熱血,所以,我更關注的還是中國社會的變革,并期望能用自己的筆為中國社會的進步盡一點綿薄之力。
作者單位: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
■ 責任編輯:袁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