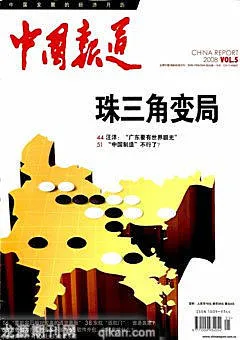資本的后殖民處境
賽義德關于“旅居”的敘述的最為重要的意義在于,資本在各種場中的可轉換性得到了足夠的重視。
愛德華·賽義德是后殖民主義文化理論的實際開創者,也是批評領域多元文化主義的奠基者之一。同弗雷德里克·杰姆遜、丹尼爾·貝爾一起,他被認為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文化批評家之一。《賽義德后殖民理論研究》(張跣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12月)是國內學者對賽義德及其開創的后殖民主義文化理論的第一次完整系統的梳理和研判,不僅填補了這一領域的空白,而且以其鮮明的創新意識和細膩的理論思辨,為國內的后殖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成果和資源。
除導論部分外,《賽義德后殖民理論研究》全書共分六章,分別研究了賽義德的早期思想和他關于東方主義、世俗批評、巴勒斯坦問題、文化與帝國主義等問題的論述,涉及賽義德幾乎全部的重要著作。作者以“不得其所”為關鍵詞,對賽義德的文化認同和學術意義進行了深入細致的探討。
“不得其所”(out of place)源自賽義德的回憶錄。有學者將其譯為“鄉關何處”或者“格格不入”。這樣的譯法顯然不能夠準確傳達賽義德思想的深刻內涵,“鄉關何處”過于懷舊,而“格格不入”又顯得矯情。在將這個詞詮釋為“不得其所”之后,作者賦予了它“生命的”和“學術的”雙重含義。就其“生命”的意義來說,賽義德從小遠離故土,經歷著包括語言的分裂、身份的困窘等常人無法體驗的深刻的心理磨難,長大之后也是東奔西走,居無定所,總是心有旁騖,保持警惕,永遠處于“世界之間”,永遠沒有真正“家”的感覺。就其“學術的”意義而言,賽義德始終徘徊于客觀知識與政治知識、“霸權”與“話語”、歷史與結構、抵制與共謀、第三世界與第一世界、本質主義與非本質主義之間。這種獨特的位置以及由此產生的文化認同如同一把雙刃劍,既賦予他同帝國主義及其霸權話語展開斗爭的武器和力量,又在一定程度上傷及自身。
基于這樣的認識,作者指出,以賽義德為代表的后殖民主義理論家占據著一個特殊的位置:既不在西方統治歷史之內,也不在東方統治歷史之內,而是與它們保持著一種切線關系。這樣,他們同西方統治歷史,就既可能是一種緊張關系,又可能是一種共謀關系。他的學術著作閃耀著思想的光輝,充滿了真知灼見和精神的力量。但同時,在他把阿拉伯文化和西方文化聯系起來的時候,他也不可避免地成為后現代狀況的矛盾性、不協調性、未完成性及其可能性問題的一個集合體。在他打破了種種藩籬之后,他自己也開始失去了依靠和根基。
回顧國內以往的后殖民研究,往往可以看到兩個極端:一種情況是,只看到西方后殖民理論家同西方霸權對立和斗爭的一面,看不到他們內在的矛盾和尷尬,尤其是看不到他們努力爭取西方文化霸權的認可的這一面目;另一種情況是,對于后殖民理論家的理論貢獻,對于后殖民主義文化理論在把現代性、民族國家、知識生產和歐美的文化霸權都同時納入到自己的批評視野之后,所產生的積極意義視而不見,完全視其為西方霸權話語的共謀。本書作者從文化認同這個具體而重要的角度出發,通過對賽義德話語實踐的多形特征的準確把握,揭示了其話語實踐具有的學術/政治的雙重性,尤其是揭示了其中既相互分裂、相互背離,又相互挪用、相互促動的復雜關系,這無疑是后殖民主義文化理論研究的發展和深入。
在對賽義德《東方主義》的開創性意義進行了充分的肯定之后,作者通過對其潛在的雜交視角的具體分析,認為“賽義德的理論是一種激進的反抗理論與批判理論,但是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理論是悲觀的、消極的,因為它過高地估計了霸權的力量”,并進一步指出,“在知識和表征活動中,既不能把這種霸權絕對化、本質主義化,也不能陷入相對主義的泥沼”。比如,在談到《文化與帝國主義》的方法論困境時,作者指出,“折中主義可能既是它力量的源泉,也是其軟肋所在。折中主義既使得它在保持其后結構主義方法論框架的同時能夠乞援于傳統的人道主義,又在一定程度上重復了《東方主義》的方法論困境”。又比如,在對備受責難的賽義德的職業生涯進行分析時,借助于布爾迪厄的“場”的概念,作者指出,賽義德關于“旅居”的敘述的最為重要的意義在于,“資本在各種場中的可轉換性得到了足夠的重視,向上流動的跨國經歷不僅僅是在索要權威,而且是在重新界定權威,這一次重新界定會有很多人受益,因為它意味著重新構成文化資本,也意味著文化資本的重新分配”,“簡言之,中心不但能夠改變,而且已經在改變”。換句話說,出生地的特權和目的地的特權不可避免地發生碰撞,處于支配性的歐洲中心話語中的他者的文化空間也因此得以擴展。這樣的論述把后殖民理論家特別是賽義德的族裔出身、文化背景、個人經歷、職業規范同他們的思想方式、理論追求結合起來,揭示了這種身份所具有的重要的文化性、政治性和地理意義,既是辯證的、深刻的,也是有富有創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