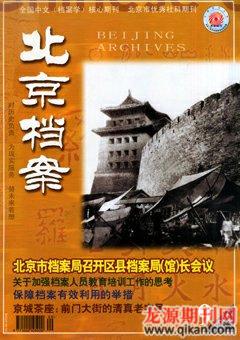從“芻議”不是“謅議”說起
知心大哥
近日市檔案學會舉辦青年學術骨干模擬論壇,一作者將論文標題中的“芻議”寫成“謅議”,被應邀點評的專家當眾指出。事過境遷,但感觸猶存。
“芻”和“謅”的音義截然不同。“芻”音chu(除),《現代漢語詞典》對其釋義有三:一是喂牲口用的草;二是割草;三是謙詞。如“芻議”是謙稱自己的議論是草野鄙陋之人的議論。“謅”音zhou(周),意為“編造(言詞)”,如胡謅、瞎謅。故不可把“芻議”換成“謅議”。
為搞清“芻議”變成“謅議”的原因,筆者查閱了幾種文檔刊物,發現《中國檔案》從1981-1998年有17篇論文的標題使用“芻議”,《上海檔案》從1987-2001年有8篇論文標題使用“芻議”,《應用寫作》從1981-2000年有33篇論文標題使用“芻議”。而上述刊物,均無“謅議”一詞。這說明“芻議”一詞在文章標題中,使用頻率不低,而“謅議”則純系生編硬造的一個詞匯。不過,正規文檔刊物不見蹤影的“謅議”,在其它刊物上是否露過面,筆者未做調查不得而知,但網上的情況卻不容樂觀。“百度”一下“謅議”一詞,立刻便有不少以“謅議”一詞為標題的文章出現。就連九十年前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也被人竄改為《文學改良謅議》。胡大師一向以學風嚴謹著稱,倘九泉下得知其著作是胡謅出來的,肯定會啼笑皆非。
“芻議”變“謅議”,多少有幾分戲謔。網上還有將“芻議”寫成“雛議”的。雖然“雛兒”在《現代漢語詞典》中,有“比喻年紀輕、閱歷少的人”這樣的解釋,但“雛議”一詞卻屬生編硬造。撰寫論文最講究用詞規范,因此,這類低級錯誤不該發生,特別是不該發生在青年學術骨干中。說是不該發生,但還是發生了,這就發人深省,說明了一些深層次的問題。
一是反映了作者頭腦空虛。毛澤東同志曾語重心長地講過,“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一些檔案人頭腦空虛,既緣自缺少社會實踐,對本職工作一知半解、不求甚解;也和不重視讀書學習有關。盡管檔案部門都訂有《北京檔案》,可真把刊物當成業務必讀書的并不多。頭腦空虛表現在撰寫論文中,就是不知寫什么好,于是只能求助于“萬能”的互聯網。參考網上的相關信息,這并沒有錯。但若對某些語詞、概念,尚未弄懂含義,更談不上消化吸收,就被一古腦兒收到論文中。那就難免使一些論文給人似曾相識之感,或鬧出笑話。所謂“摘到籃子里都是菜”,這就是當前不少論文從網上東拼西湊、生搬硬套的真實寫照。筆者以為,這“謅議”,乃至“雛議”一詞,倘若不是作者自造,便一定是從網上抄來的。
二是反映了作者沒有嚴謹的治學態度。網絡的發展拓展了信息的獲取渠道,這本來是件好事。但若不加鑒別,一概的“拿來主義”,以為網上的都是正確的、準確的、真實的,那就極有可能上當受騙,跟著指鹿為馬。近期發生的華南虎假照事件,教訓深刻,應以為戒。沒有嚴謹的治學態度,常常表現在想當然上,還拿這個“謅議”來說,作者可能以為:“芻”字加個“言”字旁,變成了“謅”,正好和“議”字搭配。豈不知這種想當然,不但沒有了原來的謙虛之意,反倒無意中把自己的論文說成了“胡謅”。
三是反映了作者缺少必要的鑒別能力。像“芻議”和“謅議”究竟哪個正確,翻翻《現代漢語詞典》,便可一目了然。若是查閱《辭海》,連出處都能找到。這種鑒別方法既能避免謬誤,又能增長知識,還不用求人,何樂而不為。所以,青年學術骨干案頭備些《辭海》、《辭源》、《大百科全書》之類的工具書,是必不可少的。當然,查閱工具書,只是最簡單的鑒別方法。遇到稍復雜一些的問題,便要下一番工夫,動一番腦筋,搞一番調研,作一番論證,這就屬于做學問了。如仍有疑問,還應請教專家,給以指點。這些都是寫作論文必備的基本功,也是寫作論文必經的途徑。如果連這些最基本的東西都不具備,或者不愿意做,那就干脆偃旗息鼓算了,也比東拼西湊、瞎編胡謅要好得多。
四是反映了作者寫作功力的單薄。寫作,包括寫作論文,需要長時間的培養磨練,不能淺嘗輒止。人言“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像“芻議”誤為“謅議”這樣的低級錯誤,專家們能一眼看出,作者卻習以為常,這就是差距。而這個差距可不是一年兩年就能趕上的,因為,糾正了“謅議”,可能還會出現“雛議”。
將“芻議”誤為“謅議”,對作者來說可能是無心的。但卻反映了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即當今的一些論文確有瞎謅胡侃的現象存在。這也難怪,要彌補寫作功力的單薄,又不愿下苦工夫,也就只有瞎謅胡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