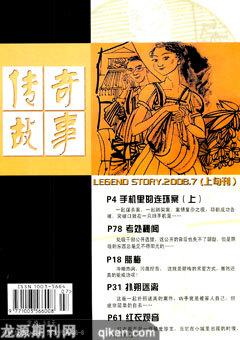手機里的連環案(上)
李 鑫
隆湖市最近奇案接二連三,糧食局長周水金被殺之后,城建局長王學忠家又出了大事兒。
那天王學忠正在市委三樓會議室參加市中層領導會議,他的手機突然震動起來。他從口袋里取出來悄悄一看,發現是一個陌生號碼。他本不想接這個電話,但這個電話響得很執著。
王學忠的座位剛好離會議室門口很近,他便輕輕地閃至門外的走廊,接了這個電話。
電話是一個陌生男人打來的,聲音透著陰冷:“王局長,您不認識我,不過這沒關系,我認識您就行了。”
王學忠一聽就知道來者不善。他本能地想關掉手機,但他同時又意識到關掉手機也未必就能擺脫糾纏,倒不如把事情搞個明白,看看對方到底要干什么?
王學忠盡量保持冷靜地問對方:“有什么事你請講。”
對方說:“聽說你這次跑官花了不少錢?”
這句話似說到了王學忠的敏感處。王學忠警惕地問道:“你什么意思?”
對方說:“沒什么意思,我只是覺得你花的錢還不夠數。”
王學忠聽了此話,嗓門像被噎住了一樣。對方不等他說話,又惡狠狠地說:“王局長,你可能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吧。我現在并不想跟你多啰嗦,你準備好100萬元,等我的電話吧。”
王學忠終于弄明白了對方的意圖:原來他是要敲詐勒索自己。王學忠心想:看來這個電話一定是與這次競爭常務副市長有關系的什么人打來的,他們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官場上的事情,認為他這次跑官花了不少錢。
現在隆湖市滿城風雨傳說的跑官花錢,只能算是民間臆猜的花邊新聞,可以說根本就是無稽之談。而現在,竟然不知道是什么人,張口就來以此對他進行敲詐要挾,這不是太滑稽好笑了?王學忠心里非常清楚,如果他軟弱可欺對此就范,豈不到了假做真時真亦假的相反境界?
王學忠猜不透這個打電話的人是什么樣子,什么身份,但他心里并不恐懼。他的嘴角露出一絲輕蔑,他問對方:
“你覺得我會給你這100萬嗎?”
對方非常紳士非常儒雅地說:“王局長,如果僅僅是因為我們剛才探討的問題,你當然不會給我100萬,但我告訴你,今天是星期五,如果你回到家,我想200萬你也會在所不惜。”
這句話對王學忠的震撼極大,他突然有種不祥的直覺:犯罪分子很可能在打他女兒的主意。
王學忠的女兒雖然才14歲,但出落得十分嬌艷;她身材挺拔頎長,看上去有些南方女子俏麗的骨感,但同時三圍柔美的曲線也在她青春的身體上展現出來。
凡見過王學忠女兒的同事、戰友,沒有不羨慕王學忠的,說這才是真正的大牌明星的坯子。有的戰友干脆就叫王學忠“名人她爸”。王學忠對女兒的未來可以說充滿了美好的憧憬。
此時,敲詐者說的話讓王學忠一下子就想到了女兒。女兒周五下午就放學了,這個時間,她自然應該在家中。女兒一向乖巧聽話,從不擅自做主離開家,假若要和同學外出,都會告訴父母親的。此時,王學忠掛斷這個奇怪的敲詐電話,就急忙給家中打電話。然而,家中卻沒有人接。王學忠本來想打電話告訴妻子,但妻子此時在金都出差,她不可能知道女兒的情況,也不可能立即趕回來的。當機立斷,王學忠急匆匆地坐車趕回家中。
家里果然不見女兒的蹤影,甚至也沒見女兒的書包。他正想給女兒的學校打電話詢問情況,此時他的手機又響起來了。
對方說:“王局長,回到家了吧?知道怎么回事了吧?我告訴你,你的女兒是我從學校接走的。當我告訴她我是你的戰友,說你在單位等她時,她竟然跟著我來啦。這只能說,你的女兒她不僅漂亮,而且非常單純。多可愛的姑娘啊!怎么樣,100萬不算多吧?”
王學忠急得半天沒有接上話,他問:
“你在哪?”
對方說:“我和你女兒在一起,想聽聽她說話嗎?”
沒等王學忠回答,電話筒里傳來撕膠布的聲音,接著,是女兒撕心裂肺的哭喊:“爸爸,救我……”
王學忠拿著電話,焦急地喊道:“女兒,你現在在哪兒?”
問話并未得到回答,大概她的嘴又被膠布給封上了。這時只聽對方說:
“王局長,你歷來是個審時度勢的人,我希望你不要再啰嗦了。想要你女兒并不難,明天下午3點你帶上100萬現金,乘趕往省城的T1820次列車,我會隨時與你聯系。你也可以報警或者失約,但我相信你知道那樣做的后果。”
王學忠當然不會失約,但報警還是不報警,他從接到電話的那刻起就一直在猶豫:要是報警,這個事情就鬧大了,很有可能直接影響自己的仕途:要是不報警,自己比起黑勢力來畢竟勢單力薄,單槍匹馬怎能斗過犯罪分子?要是犯罪分子設的是騙局,拿到錢之后還不肯還他的女兒怎么辦?
一向果敢堅定、多謀善斷的王學忠突然感到自己黔驢技窮,沒了主意。
王學忠抽了一夜的煙,直把自己屋內燒得煙霧騰騰。他的思路終于理清了:為了救女兒,他可以不當官,可以不要錢。他決定報案。
王學忠將電話打給了曾找他談過話的公安局副局長郭嘉。本來,公安局的一把手白銅國他更熟悉,但白局長近期到省委黨校學習,他只有找郭嘉。
郭嘉接到報警,本想帶刑警直接到王學忠家里去,或把王學忠約到局里來,可又擔心這樣太招搖。為了防止犯罪分子團伙作案,在王學忠家及公安局周圍留有眼線,便把王學忠約到了一個不易被人跟蹤的安全地方。
王學忠到來的時候,郭嘉和刑偵隊長呂陽等四個人已在那兒等候了。他們幾個人都穿著便裝,完全看不出是公安人員。
郭嘉讓王學忠細細地講了案發前后及與犯罪分子通話的情況。
呂陽聽后,分析道,既然犯罪分子讓王學忠上火車,那說明犯罪分子極有可能混跡于這趟列車的旅客中,到時候他們也許會制造一場諸如尋釁滋事或爆炸行兇之類的事件借機將錢取走。至于人質,罪犯會將其放在哪兒,就很難說了。但帶上火車的可能性幾乎微乎其微,因為人質畢竟不會輕易和綁架者配合,綁架者要是帶著她上火車,等于是在自己腦門上貼了一幅“我是綁架罪犯”的條子。
呂陽的話不能說沒有道理,但郭嘉心里有一個理念,那就是抓罪犯主要是為了救人質。必須要想辦法確定人質的位置。那么,人質會在哪兒呢?
幾個人經過分析,認為人質目前還在本市的可能性極大,也不排除人質已被犯罪分子用汽車運送到T1820沿線的某一站,但到底在哪一站是很難做出判斷的。因為T1820從隆湖站到終點站,至少有1000公里,狡猾的犯罪分子把犯罪的線路鋪排得太長,讓公安人員很難判斷罪犯要在哪一地段與王學忠“接頭”。
但不管怎么說,有一點是比較明確的,那就是呂陽剛才的分析:既然犯罪分子讓王學忠上火車,他應該是在火車上作案無疑。這個思路一旦清晰,郭嘉決定將警力布置在列車上。到時候,讓大伙扮成旅客或列車上的工作人員,隨時準備發現罪犯蹤跡,應付突發事件。
“那綁票要的錢怎么籌備?”郭嘉本來是問刑偵隊長呂陽的,但王學忠卻接過了話:“我來想辦法吧,同事朋友借一借,能湊夠。”
其實,王學忠在銀行的個人存款也能達到這個數字,但他知道,那遠遠超出了公務員的收入范圍,所以,他才說要找“同事朋友借一借”的話。
刑警隊的另一位偵查員十分自信地說:“湊錢?我看沒有這個必要。到時候提個里面塞滿破報紙的箱子算了,只要我們死死盯住箱子,就肯定能看到罪犯。一旦罪犯取箱子,立即把他抓住就是了。”
“不行,”呂陽說,“犯罪分子的精心預謀與奸險狡猾,我們要充分想到位。萬一我們要是在現場抓不住他,箱子又被他取走,里面沒錢,就極有可能威脅到人質的生命安全。我們要做到百分之百的努力,不讓罪犯撕票。”
郭嘉說:“好,那就準備好錢,一定要保證人質的絕對安全。”
第二天下午3時,T1820次列車經過隆湖車站,停車10分鐘。王學忠提著裝有100萬元的皮箱,準時上了火車。
按照和犯罪分子的約定,王學忠沒帶任何人,他只是多帶了一塊充滿電的手機電池,因為犯罪分子讓他24小時必須處在開機狀態,要隨時和他電話聯系。
郭嘉知道,目前只有手機才是犯罪分子和王學忠聯系的重要工具,假如能將王學忠的手機綁定,無疑是掌握犯罪分子信息的最好渠道。因此,在昨天商量事情的時候,郭嘉特意將犯罪分子的手機號碼記了下來,并向王學忠提出,最好在他的手機內安裝一個監聽器,讓公安人員監聽到犯罪分子的情況,以便隨機應變。
郭嘉的這個要求提出后,王學忠開始有些不大情愿,因為這樣一來,公安人員將會監聽到他的所有電話。王學忠有很多事情并不愿意像這起綁架案那樣希望公安人員“幫忙”。但郭嘉這個提議,并沒有看別人為難就算了的意思。王學忠想了想,最后還是答應了。為了女兒,其他隱私之類的東西就只能放在第二位了。
公安局這次出動了不少警力。郭嘉帶著幾個得力警員,悄悄趕到隆湖車站的前一站,提前上了火車,然后包了一個軟臥車廂坐鎮指揮。其他男女警員化裝成各式各樣的旅客在隆湖市火車站上車后,混跡于各個車廂,可以說,每個角落都有公安人員。一張無形的大網向罪犯張開,只要犯罪分子出現,他肯定是插翅難逃。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列車上卻一直不見綁架者的蹤影。此間警員們發現了幾個扒手,但郭嘉早有部署:不能打草驚蛇,因小失大。有局長的話在先,所有警員只有睜只眼閉只眼任小偷上躥下跳。
火車經過大墨江車站后,鉆出了一個長長的涵洞,地勢變得開闊起來。雖然說是地勢開闊,但這一帶并不是平原,而是周圍有山的丘陵地帶。這個地勢的延伸主要是因為火車道是沿河道修建的。
天已近傍晚,西方燒起了火一樣的紅霞。河對面被濃秋染成橙黃色的那一大片茂密的樹林,倒映在青綠的河水中,在夕陽霞光的照射下,泛出五光十色的艷麗。一直提著箱子的王學忠雖然內心十分焦急,但他面部卻依然冷峻。他知道,焦灼是沒有用的,他只有耐心等待那個接頭的人,至于下面要出現什么樣的場景?這個裝有100萬元的箱子怎么交出去?公安人員又怎么給他奪過來?女兒又是怎樣回到他身邊?他是不敢想也想不出來的。
列車在飛速地向前方奔馳。
突然,坐在軟臥車廂的郭嘉的監聽設置出現了閃動的信號,郭嘉趕忙戴上耳機。與此同時,在六號車廂的刑偵隊長呂陽的監聽信號也震動起來,他們趕忙用拇指摁了下監聽鍵。
電話里傳來一個陌生男人陰冷的聲音:“王局長,你很守信用,這很好。我跟你說句老實話,你能不能救你的女兒回去,就看你下一步能不能做到更誠實守信。錢都帶夠了吧?”
王學忠說:“帶夠了。我在哪兒交給你?”
對方說:“不著急,你在那兒坐好,再過幾分鐘我會派人去取的。”
既然派人來取,那說明犯罪分子就在這列火車上,甚至極有可能就在這節車廂里。呂陽警惕地掃描了車廂里的每一個人,卻無法辨認出誰是罪犯。車廂里的人表情各異:有聊天吹牛的,有打盹睡覺的,有凝神發呆的,也有東張西望的……如果按常規分析,在這幾種人中,應該是睡覺的和東張西望的旅客最有可疑性,但呂陽知道,破案往往是不能以常規做出判斷的。呂陽甚至懷疑,犯罪分子不在這節車廂中。
黃昏時分,光明與黑夜即將在兩天廣闊的地平線上進行交接。剪影似的列車呼嘯著奔向前方。此時,裝入王學忠手機克隆芯片的郭嘉和刑偵隊長的手機又震動起來。他們的監聽信號大約比王學忠的手機要早一秒鐘,在他們兩個開始監聽的時候,王學忠已打開了電話。從王學忠接電話如此快的速度可以看得出,他現在對電話的期盼是十分焦急的。
這個電話并不是犯罪分子打來的。話筒里傳來的是一個年輕女子的聲音,語調非常溫柔,也有些發嗲。刑偵隊長從聲音中就能肯定,此女和王學忠關系非同一般。
王學忠顯然不想和這個女人多啰嗦,這可能是因為在這種環境中他沒有時間和心思去應付她,萬一犯罪分子打來電話占線。那不是誤事嗎?同時他也知道,現在公安人員正監聽著自己的電話,如果話說得稍微不得體,顯露出倆人的私情,豈不是敗壞自己的形象。
王學忠畢竟老到,他接電話的時候,語氣不溫不火,讓人感到就像平時與普通朋友的對話,只是在此基礎上略顯有些客氣,讓人感到倆人的關系似乎并不親密。王學忠說:“是小蘇啊,我現在有急事在外面,你跟我說的那件事情我會盡快辦,回頭我給你打電話吧。”
王學忠簡潔地說完,掛斷了電話。他知道,這個電話肯定被郭嘉和刑偵隊長全部聽到了,好在自己隨機應變,沒有從語氣中表現出情人之間的曖昧關系。但他還是有些后悔,出發前應該給這個小情人打個電話,以免中途添亂,但當時他焦頭爛額,哪有時間考慮自己的“私事”。
王學忠的這個小情人好在是個通情達理的人,而且處事比較敏感,一般情況下,王學忠一個眼神,一句話她都當暗號琢磨,時刻想的是會不會給他添亂。現在,當她聽到王學忠用這樣的語氣跟她說話,知道王學忠有不方便之處,也就很順從地掛了電話。
郭嘉監聽到這個電話,雖然面無表情,但內心里卻會意地一笑。
正當郭嘉和刑偵隊長兩個人為剛才的小插曲感到輕松的時候,電話又來啦,這一次,是犯罪分子的聲音。
犯罪分子似乎沒有以前打電話那么儒雅,他用冷酷的聲音命令道:“王局長,你現在站起來,對,提上箱子,往車廂的前方走。”
王學忠提上箱子,按照罪犯說的,一步一步往前走去。
罪犯說:“看到了吧,你的左前方有一個打開的窗子,你走過去站到窗子前。”
王學忠走了過去站在了窗口前。
這時,就聽罪犯兇狠地說:“我喊一二三,你就將箱子往窗外扔。”
王學忠一聽,頭一下子就大了!他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是這樣的“交接儀式”。
王學忠不得不感嘆,這犯罪分子的腦袋真他媽的智慧,他怎么想到如此絕妙的高招呢!
盡管如此,王學忠心里有一條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他來到底是干什么的。于是他提著箱子急切地問道:
“那我的女兒呢?”
罪犯說:“現在不是你跟我講條件,而是我給你講條件。我告訴你,只要你準時將錢扔到火車外面,我會將你的女兒完璧歸趙。假若你不執行,王局長,那就別怪我不客氣了,你的女兒馬上就會被撕票。聽著,現在開始:一!二!三!”
王學忠沒敢有半點猶豫,他覺得此時就好像恐怖分子將屠刀高高舉起馬上就要落在他女兒那玉一般的脖頸上,在對方數到三的時候,他就像扔一個將要爆炸的炸藥包那樣,將裝有100萬元的箱子甩出了車廂之外。
錢箱子脫開王學忠的手飛出了火車車窗,王學忠本以為會聽到當的一聲撞擊,然而它卻像飛出的樹葉一樣無聲無息,王學忠耳邊呼嘯的依然是列車奔馳的轟鳴……
從罪犯給王學忠打電話,到箱子飛出車廂,不過就是幾十秒鐘的時間,然而這短短的幾十秒鐘,卻讓公安人員見識了犯罪分子的高智商。
應該說,罪犯的智商遠遠超過了公安人員的預料。比如,在犯罪分子跟王學忠數數的時候,呂陽就在王學忠的不遠處,可他卻被罪犯離奇的怪招弄得腦子發蒙了。一時間,竟無法想出來一個能與罪犯叫陣的應對辦法,他不知道是該沖上去阻止王學忠扔箱子,還是該緩一步再說?要是阻止他扔皮箱,無疑就會暴露這次行動計劃而惹惱犯罪分子,萬一犯罪分子因此撕票怎么辦?
也許在呂陽的潛意識中,他將保護人質的安全放在了首位,因此在王學忠往火車外扔錢箱的一瞬間,他做出不去阻攔的選擇。
失魂落魄的王學忠站在那里,任車廂顛簸搖動。
此時正在軟臥車廂監聽的郭嘉突然意識到,既然犯罪分子讓王學忠將箱子扔下火車,犯罪分子肯定就在列車現在經過的這一帶活動。郭嘉當機立斷,決定派警察跳車追捕罪犯。他心里非常明白,若錯過這個抓捕機會,下一步將很難再尋找更好的時機。
火車車尾一共有兩名警察,他們接到命令后,立即跳了車。因火車速度太快,一名警察在跳下去的時候,雖做了一個翻滾動作,卻沒想到遇到了一個凸起的石頭,他當時就受了重傷無法起身:另一名警察在下跳的時候順著列車的慣性往前跑了一段,終得以安全“著陸”。
跳下火車的警察很快就發現了犯罪分子。但見那人提著箱子,在天空最后一抹晚霞的映襯下,迅疾向鐵路旁的大河沿沖去。在那兒,停放著一艘摩托艇。
拎著箱子的罪犯敏捷地跳上摩托艇,一腳跺開發動機,僅用一只手就駕艇沖向對岸。平靜的水面頓時翻騰起一道白色的浪花。無奈的警察舉起手槍,在“砰砰”兩聲槍響之后,黑夜的幕布毫不留情地將整個清晰的世界全遮蓋了……
綁架王學忠女兒的罪犯大概在打開皮箱看到100萬后,就給王學忠打了電話。他說:“王局長,謝謝您這么守信用。錢我還沒來得及數,但我相信你不會缺斤少兩的。不過有一點你可是不夠意思,你竟然報了警,他們還朝我開了兩槍。雖然你報了警,我認為這樣也好,可以讓你親眼看到你約來抓我的那些警察都是什么玩藝。現在可以得出結論了吧,他們是一堆草包!”
犯罪分子大概嘴里在吃著什么東西,可能喉嚨有些發噎,他停頓了一下,接著說:“王局長,我跟你講句實話,我這個人就喜歡挑戰自我。你現在約來了警察,讓他們參與我們之間的游戲,我覺得這游戲玩起來更精彩、更刺激了。”
王學忠哪有心思聽罪犯這么閑情逸致地瞎吹牛皮,他牽心的是他的女兒能否順利回來。他問犯罪分子:“我女兒到底在哪?”
對方說:“你做父親的心情我能夠理解。請放心,我會將你女兒還給你的,但不是現在,而是三天以后。其中原因我想你會清楚的,那就是你叫了警察和我斗。你不是相信人民警察嗎?那你就繼續請他們,我倒是要看看他們的本事,看看他們能不能找到你的千金,看看他們能不能將我抓住!”
王學忠一聽犯罪分子還要將自己的女兒扣留三天,立馬叫道:“錢一到手就放人,這可是你答應的,你要守信用!”
犯罪分子說:“我是世界上最守信用的一個人,既然在玩游戲的時候你加了程序,我就不得不變換著玩,請多多原諒!”
犯罪分子說完掛了電話。
這個電話郭嘉與呂陽他們都聽到了。犯罪分子如此猖狂,如此藐視公安人員,這是他們沒有想到的。但他們不得不承認,這次火車抓捕是非常失敗的。人質沒有找到不說,還將100萬元白白地扔給了罪犯。況且,罪犯現在完全是以一種游戲心態在和公安人員盡情盡興地玩耍,這如果要是傳出去,豈不讓人覺得隆湖市的刑警是被人領著玩的幼兒園學生。
參案人員都感到壓力很大,尤其是副局長郭嘉,可以說他從來沒有這樣焦灼過。因為案件發生的時候白銅國局長不在家,任務自然落到了他的身上。而現在案子發展到如此窩囊的地步,他怎能不感到苦惱和焦急。
從列車上追捕回來之后,郭嘉就趕忙召集刑偵隊的專案人員研究案子。討論時,眾人雖然被失敗擊得有些垂頭喪氣,但分析起案情來,大家還都是積極踴躍。他們首先想判斷出綁匪到底是團伙作案還是個體作案,因為這是關乎破案全局的關鍵性問題。有的警員堅持認為是團伙作案,因為犯罪分子除了在火車下有接應皮箱的,在火車車廂內還有幫忙的,要不然王學忠怎能會被犯罪分子指揮到車廂內一個開著的窗戶前?這就是說,火車車廂內肯定有內鬼,這個內鬼提前將車窗打開,除此之外,他(或者他們)還悄悄給外面接應的人打了電話或發了信息……
呂陽聽了這種觀點,并不認可。多年的工作歷練,讓他自信有一雙鷹一般的眼睛,自他上了那趟列車后,他就在車廂里進行了多方面的認真觀察,一直沒有發現可疑人的蛛絲馬跡;事后,他又考察了這趟列車的每一節車廂,當時他發現,每節車廂這個位置的窗子都是開著的。經調查詢問,才知道那個時間全車的列車員要打掃衛生,各車廂的一些生活垃圾需從窗戶口扔出去,所以,列車員們都就勢將這個窗戶打開了。顯然,犯罪分子在作案之前已經反復做了實地考察和精心安排,幾點幾分列車將會到達什么地方,犯罪分子早把時間地點都算得非常精確。因此,這就不能貿然說是車上車下的犯罪分子在遙相呼應。也許一切的機巧都是犯罪分子精心計算出來的,可見這個犯罪分子的智商多么高。
案情分析到深夜也沒有什么實質性的進展。此時大家已連軸轉了近40個小時,身體已顯疲憊。郭嘉便讓大家解散,所有人員一律休息,養精蓄銳,隨時待命。
秋日的冷月掛在如水的夜空。郭嘉回到自己的臨時宿舍時已經是深夜一點多鐘。盡管很困,但責任與壓力讓他難以入睡。他打開電腦,決定到網上沖個浪,以調整一下自己沮喪的心情。
電腦啟動之后,他剛剛打開自己的QQ,就發現有一個小頭像在電腦屏幕的右下角閃動。
顯然,這是他的某一QQ好友給他發了信息。
他將鼠標箭頭放在那個小頭像上,雙擊了一下,很快,電腦桌面上便跳出一個界面,上面書寫著一個叫“地下黨”發來的簡短文字:
“最近看不到你,是不是特別忙?周的案子有進展嗎?”
郭嘉一看這條信息的時間,距他打開電腦的時間并不長,忙給對方打了一個問號,意思是問:“你還在嗎?”
沒想到“地下黨”的頭像一下子從黑白狀態變成了彩色狀態,并同時傳來了一個齜牙的QQ表情。這就是說,“地下黨”剛才一直處于隱身狀態。
郭嘉有些驚喜地打出字:“原來你在啊,這么晚了還沒休息?”
“地下黨”并沒有回答他的話,而是給他發了一個視頻聊天的要求。郭嘉用鼠標點了一下同意。“地下黨”的頭像很快在顯示器的屏幕上出現了。
網絡中的“地下黨”,其實就是《金都日報》的石天然,這是他在QQ上的名字。
兩個人開始視頻聊天。
“地下黨”:怎么這么晚才上線?
郭嘉:睡不著啊,現在真正體會到了三十歲之前睡不夠,四十歲之后睡不著的滋味。
“地下黨”:是不是周水金的案子把你折騰的?
郭嘉:豈止老周這一件案子,隆湖市現在是瘋了,怪案子一個接一個(郭嘉接著向石天然講了王學忠女兒被綁架的案情)。
石天然聽完,不禁暗暗佩服這個綁匪的犯罪智慧,但他對郭嘉的無法破案的低落情緒也深感遺憾。他覺得郭嘉破這個案子應該比上一個兇殺案容易,因為郭嘉在談這個案子的時候,多次提到犯罪分子向王學忠打手機。而據石天然所知,手機無論對誰,都是沒有什么安全和保密性可言的。據說,現在已經有了手機定位技術,只要一個人攜帶著手機,有關部門就可鎖定這個人的準確方位。車臣共和國總統死于非命,就完全是因為他在使用手機時被鎖定了目標,隨之導彈跟蹤而至,結果一命嗚呼。石天然想,像郭嘉所在的公安部門,雖然沒有導彈,應該早已具備了有關手機的高科技偵破手段。
郭嘉聽后,苦笑著說:“我們一個偏遠市的公安局,哪能配上這么高科技的設備,不過你倒是提醒了我,看來我們要向上級申請弄到這套設備。”
石天然說:“現在手機剛剛盛行,說不定公安部門會很快給你們配發的。不過你們要想了解這方面的事情,中國移動通信肯定是‘門清,你不妨通過電信部門做個調查取證。”
郭嘉哪還坐得住,他中止了和石天然的聊天,也不怕深更半夜打攪人,直接將電話打到電信局霍局長家。睡得迷迷糊糊的霍局長接了郭嘉的電話,他知道公安局的領導打電話來一定沒有小事,便客氣地問郭嘉有什么事情。郭嘉簡短地說了情況。霍局長爽快地說:“好,這事我明天一上班就交代人辦。”
郭嘉說:“要是方便,我現在就想過去。”
霍局長一聽,知道這是公安局在下達命令,哪還有方便不方便之說,方便不方便你都得爬起來,趕快到單位。人家要辦的是人命關天的大案。
郭嘉和呂陽乘車來到電信局的時候,電信局長老霍已經在那兒等候,他們簡單地客套了一下,就進了機房。打開通話記錄,業務人員邊操作邊介紹,郭嘉、呂陽大開了眼界。
原來,手機在這兒根本沒有什么秘密可保。所有的通話內容,所處的通話地點,電腦里都有記錄。
郭嘉讓工作人員調出犯罪分子的手機號碼,很快一排數據出來了:“這個號碼是個神州行,但它不是投放到我們市的號碼,按序列分析,應該是上個月投放到我們鄰市蘊城的號碼。”
郭嘉說:“那你查查它的通話記錄。”
工作人員敲擊了一下電腦鍵盤,通話記錄立即通過打印機打印出來。
郭嘉沒想到這個手機的通話記錄十分簡單,除了和王學忠僅有的幾次通話,別的竟然什么也沒有,顯然,這個號碼是犯罪分子專門買來“對付”王學忠的。
郭嘉突然想到石天然跟他說的衛星定位的事,他希望工作人員能測出犯罪分子現在的位置。工作人員聽后,有些無奈地說:“衛星定位我們局的設備還不能做到,估計要到明年升級之后。我們現在唯一能顯示的是對方的ID地址,這還得等到對方開機的時候。”
郭嘉聽后,覺得掌握犯罪分子的大概位置也很重要,他想了想,決定給犯罪分子撥個電話,以判斷犯罪分子現在的位置。然而,電話撥通后,對方卻是關機狀態。這就是說,對方的ID現在是無法顯現的。
盡管如此,郭嘉并沒有失望,他知道,只要犯罪分子有開機的時候,他所處的位置就一定能顯現出來。
電信局的這位技術人員顯然是一個極其熱情的人,他說,其實要查這個神州行號碼并不難,因為神州行的用戶在我們這個地區還不是太多,主要是因為它的計價費用太高,市內普通話費每分鐘就要六毛錢,要是漫游更不得了,許多人都將其稱為“老虎機”,所以,每個市的電信局進神州行號碼都比較少,每月也就是投放百十來個。上級有要求,凡是移動電話出售,銷售部門都應該將號碼持有人的身份登記得清清楚楚,這就是說,用戶在購買神州行號碼時,都要求記錄身份證號碼。所以,你們到蘊城市查這個號碼并不難,說不定一到那兒,就能把罪犯的身份搞清楚了。
這位技術員的話讓郭嘉聽后非常振奮。盡管郭嘉和呂陽也曾經想到過犯罪分子會不會使用別人的身份證,但他們相信只要罪犯做這件事情,就必定會留下蛛絲馬跡。此時,郭嘉看天已快亮,便決定和呂陽立即奔赴鄰近的蘊城市去。
路上,郭嘉和呂陽皆已困得不行。郭嘉看呂陽駕車的時候哈欠連天,便問他要不要停在路邊休息一會兒。呂陽說不用。郭嘉為了不影響呂陽,也只有強打精神,不敢打盹。
隆湖市到蘊城不過兩個小時的路程。他們很快就到了地方。
到了蘊城市遠不是在本市那樣人熟地熟,郭嘉知道,就是找人,也得等到電信局的人上班之后。于是,他們在蘊城市的電信局門口見到街邊有個油條攤,便要了幾根油條,兩碗稀飯,一碟泡菜,一起吃了起來。
吃飯的時候,呂陽看著郭嘉,發現他的臉色泛綠,兩眼深陷,那明顯是缺覺的表現。呂陽一想,從王學忠報警至今,郭局基本上是三天沒合眼了。
此時,郭嘉也發現呂陽十分憔悴,郭嘉關切地問:“是不是困得有些架不住了?”
呂陽笑笑,說:“過去和同學打麻將的時候,因為犯困不想去參與,常常挨同學罵,同學說,‘困什么困,早死兩年不就睡個夠了嗎?現在的感覺真的是想早死兩年。”
郭嘉一笑,說:“等破了這個案子,咱們一起‘死吧,反正馬上就是上班時間了,不如就堅持一下。”
呂陽說:“堅持是可以堅持,就怕我們兩個跟人家談工作的時候哈欠連天,讓人家感覺這兩個人是不是吸毒者正毒癮發作呢。”
郭嘉說:“那就找個冷水管子洗把臉吧,提提精神,不能讓人家外市的人感到我們隆湖的警察精神狀態太差。”
郭嘉正欲問賣油條的有沒有洗手的地方
時,呂陽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朝郭嘉說:
“對了,郭局,我這兒有一方妙藥,你吃下去半個小時準精神。”
郭嘉一聽,忙問是什么神藥。
呂陽說:“這可是一服產自西藏的好藥,極抗疲勞。”
郭嘉一看,一個包裝精致的綠色的小盒上印著“勃樂”二字,郭嘉心里一驚:“這玩藝不是春藥嗎?”
呂陽說:“郭局,你可不能懷疑我的品格,這玩藝的確是春藥,是上一周我在西藏工作的一個同學帶回來的,當時我們聚會的時候他作為小禮品人人發了一份,我就順手裝在包里。這人本身就在勃樂集團工作,他說這種藥是從冬蟲夏草中提煉出來的,非常金貴,房事前吃肯定能提高生活質量,但要是平時吃,也就是起一個提神作用。我的這位同學說,平時他們公司的人無論是開會還是與外商談判,只要感覺稍有疲勞,喬下一片就能精神倍增。”
郭嘉從來沒有吃過這玩藝,聽了呂陽的話,心里還是有些犯嘀咕:
“這家伙吃下去別走不動路啊!”
呂陽想樂:“走不走得動路只有吞下去才知道,說不定這家伙吃下去真的是見了女人兩眼發直,下面也直,要是電信局接待咱們的是個女的,嚇著人家了咱可是把人丟大了!”
郭嘉笑笑說:“那你還是留著嚇你老婆吧,免得在不適宜的場合吃它,讓人家感覺咱們隆湖市的公安,不是吸毒,就是好色。”
呂陽說:“那要不我們就每個人分半片吃吧,這樣我們既能保持著工作時的良好狀態,也可守住貞節,不然這困勁兒我是頂不住了。”
郭笑了:“行,豁出去了!”
兩個人各吞下半片“勃樂”,向掛著蘊城市電信局牌子的大門走去。
當呂陽向電信局接待他們的人亮出偵查證,這個人也許天生有種恐警心理,他神情立馬變得有些緊張。也許他是想掩蓋自己的緊張心理,因而對兩個警官表現得十分客氣。
他請郭嘉和呂陽坐下后,自我介紹說,他叫邱啟培,是電信局分管業務的副局長。待他聽完郭嘉、呂陽的來意,忙說:“你們先喝點水稍等片刻,我馬上就把專門分管手機號碼投放業務的經理找來,她應該知道情況。”
說著,邱啟培拿起電話撥了個號。然而,對方占線,邱啟培不好意思地解釋說:“我到樓下喊她一下,你們先坐。”
邱啟培一路小跑地從三樓下到一樓,不出一分鐘,他就領來了一個30多歲的穿著套裙的女人。邱啟培看著郭嘉與呂陽,滿臉歉意地說:“讓你們久等了,這位就是我們局市場營業部的周經理周琳,剛才她那兒正在忙業務,所以電話占線。”
女經理在邱副局長的解釋聲中,也客氣地沖兩個公安笑了笑。
呂陽示意女經理坐在旁邊一個椅子上,邱副局長見呂陽沒有招呼自己,忙知趣地說:“要不你們談,我回避一下。”
顯然,邱副局長是個很懂規矩的人。
呂陽像沒聽到邱啟培的話語,根本不理他的茬。這弄得邱啟培不知道該如何辦,他有點走也不是,留也不是,還是郭嘉客氣地朝他做了個手勢。邱啟培明白,郭嘉是讓他也坐下來。邱啟培有點像客人一樣拘謹地坐了下來。
呂陽望了一眼姓周的女經理,表情不冷不熱,一副公差問訊的樣子:“周經理,我們來主要是查一個移動電話號碼。”
呂陽說著,將手機號碼寫在紙上:“你看看這個號是不是從你們這兒發售的?”
周經理仔細地看了一會兒號碼,語氣在肯定和不肯定之間地說:“從數字排列序號上看,應該是我們市的神州行號碼。”
“你能查出這個號碼是從你們局哪個發售點發售出去的嗎?”
周經理面露難色:“這個不太好查,畢竟那么多發售點,那么多手機號,要是查起來可能會非常困難。”
呂陽說:“怎么不好查?按規定,不是每個移動電話號碼出售,都要有購買人員的身份記錄嗎?”
女經理見呂警官如此咄咄逼人,本來就難堪的臉色上又多了一些紅色。顯然,他們是沒有按上級的要求對號碼發售逐一登記。也就是說,這些手機號碼進到他們電信局后,他們全都稀里糊涂地將其投放到市場,根本就沒讓購買者留下身份證號。無疑,這不符合國家向電信部門做出的售號要求。然而,女經理并沒有對此檢討自己的過錯,而是極力在找著搪塞的理由。
她說:“是的,我們過去一直對移動號碼都做登記,但后來發現,這種登記不過就是個過場,其實是防好人不防壞人,真正的犯罪分子買號,用的都是偽造的身份證。所以,我們也就不再搞形式主義了。”
女經理一句“不搞形式主義”,給郭嘉的感受并不是說明女經理是個能扯的人,而是讓郭嘉感受到特別的泄勁與失望。
來蘊城市之前,郭嘉聽說購買移動電話都有身份證登記,心中似觸摸到了案子欲破的希望。而現在,希望瞬間破滅了。
此時尷尬的不僅僅是營業部的周經理,還有電信局的邱副局長。因為他們畢竟是這個單位的管理人員、而他們管理的漏洞隨著呂陽的一句問話,頃刻間暴露無遺。
尷尬的邱副局長好像突然想起了一個能夠扭轉被動局面的辦法,忙向周經理問道:“你們營業部不是有一個記憶力特別強的人嗎?看看她能不能幫助公安同志回憶一些情況?”
周琳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忙應道:“對了對了,我們前不久招來的一個營業員確實厲害,別看她長得平平常常,但她的記憶力可非同一般,凡是她看過的,不管是人是物,可以說是過目不忘。”
呂陽望著眉飛色舞的周琳,覺得這位女經理不僅能“扯”,還十分能吹。呂陽心說,世界上是有過目不忘的人,但大多都是頂級的領袖人物,那種奇才可以說幾百年才出一個,現在周琳張嘴就說他們營業廳就有,未免也太夸張了。
盡管如此,呂陽他們還是希望見見這個營業員,現在是調查了解,多見一個人,也許就多一分收獲。
邱局長見他們點頭同意,就急著想喊那位女營業員過來。呂陽卻說,直接到營業廳去看她。郭嘉心里明白。呂陽是想捎帶著到那里去看看環境。
來到營業廳,這里的人并不多,郭嘉呂陽被周琳領著直接找到女營業員。
女營業員的長相確實普通,普通得讓人感到看了她之后自己的記憶就不會再存在。但呂陽還是盯住她這張不容易被人記住的臉問道:“聽說你記憶力非凡,你能記住你賣出去的手機卡號嗎?”
“能。”
呂陽沒想到女營業員真敢這樣回答。講內心話,他問這個話時就是準備難為女營業員的,因為他不會相信一個營業員能夠記住她所賣出去的手機號碼,試想一個手機號碼11個數字,一個營業員即便每天只賣一個號,那么工作一個月也是30個號,這30個與11相乘那就是一大串數字,一個營業員哪有可能記得下來。然而,面前這個女營業員竟然說出了“能”,這讓呂陽感到她是不是有點“二”?
呂陽毫不客氣地將那個手機號碼推至女營業員面前。然后看著她的表情。
女營業員低頭看了一會兒,不出一分鐘。竟然就肯定地說:“這個號碼是從我們廳發售
出去的。”
本來對女營業員沒抱什么希望的呂陽和郭嘉聽了這句話,真是吃驚不少,他們也一下子振作起來:“你可看準了!你沒有任何筆記記錄,憑什么說它是從你們營業廳發售出去的?”
女營業員并沒有回答他們的問話,只是說:“肯定沒錯,這批號是上月23日局里向各營業廳投放的一批神州行,我們這個營業廳一共進了200個號,現已基本售空。”
照女營業員的這一說法,郭嘉、呂陽他們負責破的案子無疑又找到了突破點。本來,兩個人對這個女營業員并不抱什么希望,但聽了她這句話,興奮點又被激活了。
呂陽心想,既然她能說這個號碼是從此柜臺售出去的,也許有什么數字上的規律。但不管怎么說,她在記憶力上,還是有超出常人的東西。呂陽決定好好問問她。
“那你對購買神州行號碼的人還有什么印象嗎?”
呂陽話一出口,連他自己都覺得這話問得過于苛刻,每天來電信大廳那么多人,而且時間已經過去近一個月,哪有那么好回憶的?但“有病亂問藥”,呂陽也只能這樣了。
“你讓我想想,”女營業員思考了一會兒,說:“那天應該是上個月的24號,就是我們這批神州行投放市場的第二天。買這個號的人大約三十歲左右,人很瘦,但他的眼睛很亮,好像是白多黑少的那種亮。他在我們這個柜臺上大約轉了一會兒,就選了一個號,放在他自己的手機上試好后才走的。”
呂陽簡直有些不大相信在這么浩渺的人群中,一個營業員能回憶出一個購買號碼的人,呂陽問她:“你對他記憶這么清楚,他當時和你有過多交談嗎?”
女營業員說:“買賣東西肯定要交談,但沒有更多的交談,那人看上去很平靜。他要買號,我也就賣給了他。”呂陽不知道女營業員說的是否準確,甚至不能確定她說的話是真是假,但是,他現在只能相信這個女人。
為了弄準那個買手機號的人的形象,呂陽展開筆記本,對女營業員說:“你再把他的形象說細致些。我把他畫出來你看像不像。”
呂陽在女營業員的敘述中,飛快地點厾著畫筆,一個男人的形象逐漸躍然紙上:但見此人長臉,尖下巴,牙有縫,稀發,耳朵有些豎,呂陽按女營業員說的這個形象描畫著,再加上白多黑少的眼睛,人物畫出來啦,郭嘉一看,竟然發現這是一個非常眼熟的人:
“你說的這不是葛優嗎?”
女營業員說:“對,他是有點像葛優,但他沒有葛優那么面善,最不同的是他的腰特別細。”
呂陽正在畫人的臉面,根本沒想到要畫人的腰,現在聽著女營業員的話,不得不在頭下面加上細腰身子,弄得這幅畫畫得不像個嚴肅的破案畫像,反而多了許多幽默的意味。呂陽將畫好的畫又放到女營業員面前,女營業員這次認真地點了點頭。
郭嘉、呂陽對這個過于自信的女營業員提供的內容,真是又想相信,又覺得不是那么可靠。見她對這幅畫點頭,呂陽有點像電視臺的主持人那樣,忍不住地問她一句:
“你確定嗎?”
女營業員盯著“葛優”,很堅定地回答道:“確定!”
郭嘉、呂陽聽了女營業員的話,不知道是不是該松口氣。假若罪犯要真是此人,并不是不好找,這就是說,這個人最致命的地方是長了一張名人的臉,凡是那些長相像葛優的,可能都是嫌疑人。這樣有特色的人物是很容易被眼睛雪亮的群眾舉報出來的。
雖然眉目出來了,但呂陽還是不放心女營業員的記憶力,她憑什么就說這個神州行號是賣給了“葛優”?要是她說的根本不是事實,或者張冠李戴,那問題就大啦。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小伙子突然跑過來幫女營業員說話了。
這個小伙子是坐在營業廳門旁邊的一個修表師傅,在這寸土寸金的大廳一角,他租了一個一平方米的柜臺,平時的工作就是專門幫人修修手表、換換電池什么的。
呂陽他們當然不知道,這個小伙子一直在暗戀著女營業員。平常有事無事的,他總喜歡到女營業員的柜臺邊轉一轉。今天,在郭嘉與呂陽找女孩談話的時候,他又轉了過來,當然他不知道這兩個人是來調查案子的警察。只是在他看到桌臺上放著的“葛優”的圖像時,他叫喚了起來:“這個人怎么這么眼熟?我肯定在哪兒見過他!”
呂陽聽了這話,自然是不會忽略他。但同時呂陽心里又特別明白,他畫的這個人畢竟長的是明星臉,人們對其眼熟都是正常的,呂陽便不想讓其走更多的思維彎路,而是直截了當地提醒他道:“你是不是在電影里見過他?”
小伙子卻說:“不是,是在電視里面。”
呂陽一聽就覺得又好氣又好笑,這不是廢話?誰不知道葛優既演電影,也演電視。
其實,是呂陽的思路狹窄了,小伙子所說的電視并非電視機或電視劇的泛指,而說的是DV,即小型攝像機。這個攝像機是他一個月前買的。邵天,他正在專注地修理手表,突然有一個人來到他跟前,問他要不要DV?小伙子抬頭看看這個人,又看了看這個九成新的DV,他猜想,來人極可能是一個吸毒者或是小偷,當時,小伙子猜不透他這Dv是他自己家的還是從別人家偷來的,只是感到他急于出手,于是就問了價錢?來人要兩千,他腳脖子上砍了個價,張嘴叫200元。賣者顯然是需要錢,最后兩個人討價還價,250元拿下。
修理手表的小伙子拿到DV之后,真是愛不釋手。他舉著攝像機一只眼睛睜著,一只眼睛閉著就開拍起來。他的第一個畫面,是對著柜臺那面的女營業員的,恰恰那個時候,女營業員剛好正在和“葛優”做著交易,這不,“葛優”買號的經過就全部放進了取景框。
因為這是第一次錄像,小伙子對自己的“處女作”舍不得刪除,就把它保留了下來。
呂陽聽了小伙子的敘說,忙讓他把DV拿來,呂、郭二人認真地看了那段錄像。
在所拍的畫面中,能看得出小伙子對姑娘的多情,所有的鏡頭幾乎都是對著年輕的女營業員,只有個別鏡頭才出現那個長得像葛優的人。畫面里顯示的是他們兩個人的側面,那男的說是像葛優,不如說更像呂陽畫的那幅肖像。這讓呂陽很振奮,這么意外輕松地確定了歹徒的長相,順利得真是猶如神助。
此時郭嘉卻不是那么激動。因為他覺得今天的事情似乎來得太順利了,凡事太順利,就讓人感到心里不太踏實。郭嘉甚至想,是不是眼前鎖定的這個罪犯的長相太特殊了,容易被人記住,因此才就認為是他作的案。此人是買過神州行號碼,但僅憑一個女營業員的記憶,即使再加上DV的記憶,就能確定他所買的那個號一定就是作案用的那個號?再說,DV記憶的只能說明這樣一個人來買過號,并不能說明他買的就是那個號,畢竟DV沒在交易那個號碼的時候將其推一個大特寫:從目前錄下的聲音辨別,也非常的嘈雜混亂,并沒有從中聽到買賣雙方提及到這個號碼。照這樣推斷,營業員一口咬定是“葛優”,顯然不能令人信服。
郭嘉甚至認為,現在問題的關鍵已不是罪犯是不是“葛優”的問題,而是要論證女營業員的“記憶”準確性到底有多大的問題。
女營業員顯然是一個敏感的人,她已從郭嘉冷峻的臉上看出了對她的疑惑。果然,郭嘉說活了:“我想再問你,你是用什么特殊的方法來記住這個號碼的?同時,你是以什么理由確定這個號碼就是售給了這個人?”
女營業員面露難色:“我無法向您解釋清楚這個事情,但我就是能確認這個號碼肯定是他購買走的。”
周琳見郭嘉太想知道女營業員的記憶秘方,而女營業員又不能表達出來,忙上來圓場:
“她的記憶力肯定沒的說,她屬于那種啞巴吃餃子,心里有數的人,但她到底用的什么方法,她自己解釋不了,別人也搞不明白。反正,她在記憶上是有絕招。你們就相信她吧。”
郭嘉、呂陽何嘗不想相信她,但任何案件總是要以事實為依據,而不是靠神神叨叨的所謂“特異功能”來給人定罪的。
郭嘉在無意識當中,無奈地搖搖頭。不成想,他的這個輕微的搖頭讓女營業員捕捉到了,她像蒙受了奇恥大辱一樣跟郭嘉說:“你們公安人員怎么這么不相信人?我說的都是真話,而且是絕對的準確。這個道理你們非要讓我解釋清楚,那我舉個例子,你們這位公安人員為什么拿一支筆,就能把罪犯的面容畫出來?你總不能說他這就是特異功能吧?這說到底就是一種技能,只不過,你們不具備,我具備了而已。這根本不應該懷疑。”
女營業員說的話,有點讓郭嘉感到微微的窘迫,不管怎么說,今天收獲還是非常大的。走的時候,他們帶走了那個修表的小伙子的錄像帶,準備回去再做鑒定。
呂陽從蘊城市電信局回來的第一件事兒,就是將那份錄像帶交給了技術科進行識別。這期間,呂陽一直在琢磨著一個問題:按照人們購買手機號的常規心理,往往會對挑選號碼比較較真,營業員拿出一個卡號,他們常常會認真地研究一番,不滿意還會換上一個。也許就在這個時候,購買者會將卡號念出聲來。如果那樣,DV上應該留有聲音,據此來確定買這個卡號的人是誰,就很有把握了。
然而,技術科并沒有從聲音上鑒別出來,因為“葛優”與營業員買賣雙方在交易這個號碼的過程中,根本就沒誰念出過這個號碼。呂陽覺得很遺憾,但他不死心。
呂陽心想,既然不能從聲音上發現問題,是否還能從畫面上發現那個手機卡號?呂陽將這個想法告訴了技術科的那個叫田尚雨的年輕人。
這個想法一說出口,呂陽自己都覺得是在琢磨異想天開的事情。因為,錄像帶自從拿回來之后,他已經仔細地看了多遍,但始終未見那張神州行卡在畫面上出現過。顯然,現在對人家技術科的同志說這話,要求不能說不過分。
但技術科的田尚雨脾氣非常好,他是那種有求必應的人,聽了呂陽的想法,便積極地說:“人的眼睛在一定的時速和空間中,有時是很容易遺漏目標的。要不我們用M技術慢放一遍錄像,看看能不能發現問題。”
M技術是一種奇特的視頻技術。呂陽和田尚雨緊緊盯住畫面,突然,他們真的發現有營業員給“葛優”遞卡的鏡頭。田尚雨十分精明,在呂陽的手勢剛剛抬起,他就將這個鏡頭定格了。然后,他又通過電腦對那張卡實行了特殊放大。讓呂陽吃驚的事情一下出現了:上面竟然顯現出了綁架王學忠女兒的那個罪犯使用的手機號碼!
現在看來,這個購買手機卡號的人,很可能就是綁架王學忠女兒的犯罪分子,退一步說也是他的同伙。此時,呂陽盯著這個卡號,最嘆服的不僅僅是這奇特的M技術,更多的還是那個女營業員。她到底是什么神人,記憶竟然如此厲害?公安局真是太需要這樣的神人了。呂陽想,待案子破了之后,一定去拜訪拜訪她。如果有可能,應該推薦她到公安部門來工作。(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