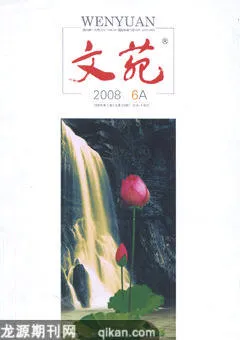淋漓暢快屬民歌
武才人
在這個時代說起“民歌”,常讓人想起的是“十五的月亮”、“祝酒歌”、“翻身農奴把歌唱”等。而其實,此“民歌”非彼“民歌”,已經有了概念上的混淆。既然是“民”歌,應當是起源于民間流行于民間的才對。
如果你說猥瑣三人組唱的那《現打斑鳩現拔毛》等才是民歌,我基本同意。
民歌起源于《詩經》,發展于漢魏六朝樂府,興盛于明代。近來研讀明代通俗作家馮夢龍編寫的《桂枝兒》時,在大樂的同時也不免大吃一驚。原來我們的老祖宗們曾開放到了如此程度,那些明顯讀來少兒不宜的民歌“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
看來明時的《桂枝兒》和現在滿天飛的黃段子有一拼。但格調明顯比現在的黃段子強多了。在這方面,我們的古人才是天才。就說《玉蒲團》、《金瓶梅》、《三言兩拍》等艷情文學的極品,今人恐怕難以望其項背。
《桂枝兒》開篇第一首《私窺》——是誰人把奴的窗來餂破。眉兒來,眼兒去,暗送秋波。怎肯把你的恩情負,欲要摟抱你,只為人眼多。我看我的乖親也,乖親又看著我。
這首將一對有情人之間的眉來眼去的親昵描述得十分可愛有趣,在讀的時候不知不覺地微笑起來。愛情自古以來面目相差無幾,無非首先是合眼緣而已。看來看去地看上了,余下的才好做安排。
說起來,癡心的還多是女人——俏冤家,說聲去,當真要去。看你急忙忙,慌速速,全沒些殷勤的意兒,千方百計留不住。我平時怎么看待你,你暗地里也要自三思。就是一塊石頭也,我抱也抱熱了你。
郎心似鐵。真是一塊石頭,其實抱熱了也沒用。
五月端午是我生辰到。身穿著一領綠羅襖,小腳兒裹得尖尖翹。解開香羅帶,剝得赤條條。插上一根梢兒也,把奴渾身上下來咬。
這里詠的乃是粽子。想歪了的面壁去。
同性戀在古時曰“男風”。這里有一個吃醋的女子,將她那有斷袖之癖的男人喝罵道——癡心的,悔當初錯將你嫁,卻原來整夜里摟著個小官家。毒手兒重重地打你一下。他有的我也有,我有的強似他。你再枉費些精神也,我憑你兩路兒都下馬。
最剽悍的乃是那句“他有的我也有,我有的強似他”。不由人不拍案大笑。
相愛時都會喜歡賭這樣的誓發這樣的咒吧——要分離,除非是天做了地;要分離,除非是東做了西;要分離,除非是官做了吏。你要分時分不得我,我就離時離不得你。就死在黃泉也,做不得分離鬼。
看到這樣的文字總是惻然。想起劉三姐也唱過:哪個97歲死,奈何橋上等三年。白頭偕老是個美好的夢想。雖然我們大多數人的人生,愛情最終不過是虎頭蛇尾的潦潦草草,或者是相厭到老的慘淡荒蕪。
《桂枝兒》是明代俗文化的代表,雖然也有些“明月穿窗影,清風過柳溪”這類的美麗句子,還是打情罵俏居多。戲謔調笑,醉生夢死。在一個封建社會的沒落期,全民縱情聲色,不足為奇。或許馮夢龍正是看透了這一點。
《紅樓夢》里的一些謎語和酒令,也容易讓人想起馮夢龍。不說薛蟠“秀房躥出個大馬猴”之類的下流之作,印象深刻的還是賈寶玉的那首:女兒悲,青春已大守空閨;女兒愁,悔教夫婿覓封侯;女兒喜,對鏡晨妝顏色美;女兒樂,秋千架上春衫薄。
即便是俚語之作,依然清新討喜,毫無淫邪之氣。令人嘆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