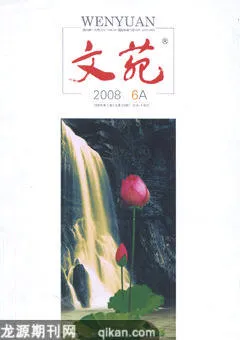堅定的表達
2008-07-28 06:34:32秦明
文苑·感悟 2008年6期
秦 明
經常疑惑:如今還有沒有人在用干凈、漂亮的漢語寫作?
是否有那樣一種人,堅定地只寫自己真正想表達的感受或想法,即便無人喝彩,也仍然心懷虔敬和慈悲,而不是把語調轉為嘲諷甚至是囂張?
我深知自己遠達不到那樣的境地,卻喜歡看這種風格的文字:干凈、地道、暢達的漢語,端莊、冷峻卻又不失幽默的語氣。它們最能讓我迅速地進入到閱讀的狀態,而不是瀏覽或調笑。
《世說新語》就是這樣一本好書。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點評得很精當:“記言則玄遠冷峻,記行則高簡瑰奇,下至謬惑,亦資一笑。”
人情相去不遠。倘若100 年為一代,每代人派一名代表,在歷史長廊中列隊而站,那么我們即使是和孔子,也不過就隔了20多個人。前人的痛苦,痛到今天都沒完。
從每個單獨的人的體驗來看,我幾乎不相信有所謂的歷史進步。蘇東坡和我們有什么不同?他無非是不用電腦打字罷了。
回到《世說新語》。《任誕》篇有云: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裈衣,諸君為何入我裈中?”(竹林七賢之一的劉伶特別愛喝酒,舉止放蕩不羈,有一天在屋里脫光了衣服。別人看到了都嘲笑他。劉伶卻說:“我以天地為家,以房屋為衣褲,各位又為何闖進我的褲襠來?”)
此事和今日之“艷照門”有形似之處。
然而陳冠希還沒有出息到像劉伶那般瀟灑。假如現在再寫一本新《世說》,不知那講故事的人,胸懷是否還會像劉義慶和他的門客那般通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