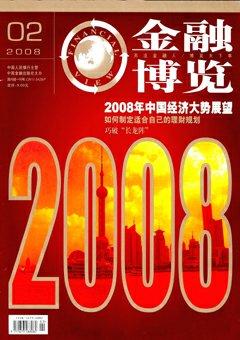事,都辦好了!
張永東
母親生病住院了!妻打電話告訴我這消息時我正在武漢出差,手頭正忙著專項央行票據兌付申報材料最后的整改工作。我們一行幾人正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夜以繼日地對申報材料進行最后的修補。在這節骨眼上,我沒有理由不和同事們一道完成這最后的工作任務。
母親今年72歲了,要說她生病在我眼里倒也不算是什么意外。從我記事的時候起母親就一直有哮喘的毛病,特別是每年到了冬天就咳嗽得特別厲害。我們幾個兒女長大后為給母親治病,也想了不少辦法,進過大醫院,找過民間偏方,可就是沒見好轉。母親經常說這是她年輕時落下的病,不可能治好了——她生育了我們兄弟姊妹六人,卻從來沒有休過什么假。因為在那個靠掙工分養家糊口的年代,沒有什么能比分上口糧養活我們這六個嗷嗷待哺的兒女更重要的了。
一個多星期后我們的申報材料終于通過了人行武漢分行審核。似箭的歸心催促我一刻也不停留地趕回家中。妻子見面就說這次母親確實病得不輕,而且生病時剛好父親也不在,她在醫院吸了幾天氧才見好轉,出院后住在四哥家。我去四哥家看母親時,哥嫂都去上班了,家里只有母親一個人。母親開門看見我第一句話就是:“回來了啊!事辦好了?我以為都見不到你了呢!”看著母親憔悴的面容和每況愈下的身體,我仿佛聽見秋天的葉子一片一片從枝頭掉落到地面上的聲音,我忍不住鼻子發酸,說不出一句話來。

母親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農村婦女,沒上過學,也不識字。聽父親說年輕時她還能寫自己的名字,老了可能連名字也不會寫了。但在我們六個子女中,就連趕上“文革”的老大也讀到了初中畢業。在那個年代,母親從來也沒因為要掙工分而和鄰居家的父母一樣讓我們拉下學業。我至今記得,我上初中時,因為學習成績優異我要到離家三十多里外的集鎮上讀書,每個星期六回家時總能遠遠地看見母親站在老屋門前那棵蒼老的核桃樹下眺望。星期天我上學時總是能裝上滿滿一包核桃、板栗、紅薯干、柿餅以及蘿卜絲、漿豆之類能管一個星期的菜瓶和零食。偶爾褲袋里還會有母親靠撿賣橡子一分一角攢起來、用手絹包了一層又一層的一沓角幣。直到如今我依然能感受到那沓角幣上殘留著母親暖暖的體溫。
母親住我家了。妻子忙碌著給母親添置了新的棉衣棉褲,女兒每天放學總忘不了稚聲稚氣地問:“奶奶,好點沒有?”我堅持牽著母親的手上樓下樓,走過馬路去醫院檢查身體。母親總說身體好多了,想回家。我也明顯感覺到母親每夜的咳嗽聲漸漸減少了。但才下眉頭又上心頭的是,在醫院檢查時醫生說她又患了老年性白內障,如果不及時治療就有失明的可能。現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給母親的眼睛做手術,讓她每天都能看見她的兒女在她膝前轉悠!
就在我寫這篇文章時,專項央行票據兌付工作傳來了湖北省首批參加兌付的16家信用社全部免檢的喜訊,母親也已經同意去做眼睛的手術了。如果一切皆如人愿的話,周末母親就會去做手術,兩個星期后出院時,正好是專項央行票據的法定兌付日。那時我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對母親說:“事,都辦好了!”(作者單位:湖北省保康縣農信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