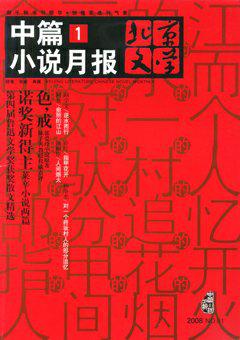對一個符馱村人的部分追憶
一題解
或說,以題目看,不晦澀也不復雜,題解不僅多余,專列一節,更有故弄玄虛之嫌。其實不然。世事和人事難說者居多,有些看似復雜的,卻往往簡單,看似簡單的,卻偏偏復雜。就我這一篇的題目,晦澀倒不晦澀,但說簡單,可就有些絕對,是簡單也有些復雜的。比如“追憶”,不就是要說一個死人的事么?是的,他已是死去的人,所以用“追憶”,但何以是“部分”呢?或說,沒有人有本事把一個人的經世之事全部寫出,這當然也說得通。但我的“部分”,不是因為沒有必要,而是因為缺失太多。比如,他是做官的,他何以當官?如何當官?尤其是現在,尤其在現在的中國,僅這一面,就可以有許多追憶的好料。但是,很可惜,我對他的這一面,卻偏偏所知極少,只記著他的幾句“椅論”和“狗論”,還是聽別人轉述的,可靠性有幾多,我不敢肯定,但既然說到了,加個塞寫在下邊,權作存疑——
“椅論”誕生于他在咸陽做官的時候。據說,一位朋友去他的辦公室看他,做官自然是很忙的,也就自然不免要在辦公室接見某個朋友。朋友看他,也不免看他做官的辦公室。做官的辦公室自然不免有煙酒,有西洋參,有的自然還有許多。也有桌子,有抽屜。抽屜里的東西只有他和抽屜知道,朋友即使不免想看,卻不免不好意思要看。但只看見的,已足以讓朋友贊嘆了:
“這多啊……”
“噢噢。”
也不免有來匯報工作的,進門時一樣地彎腰,臉上一樣地帶著一樣的笑,以至于要讓朋友相信,笑是可以和做磚瓦一樣用模子做的。朋友又一次贊嘆了:
“啊啊,真是的,你看……”
這一回他沒“噢噢”。他笑了一下。然后,就從椅子上站起來,發表了他的“椅論”。
“你以為他們是對我啊?”他說。
“不是的。”他把他剛才還坐著的椅子拉出來。
“是對著它的。”他說。
“不會吧?椅子在桌子背后的。”朋友說。
他搖著頭,換了另一種笑,說:“誰坐這把椅子,他們就對誰笑。”
又說:“幾年前,我也對它笑過。”
又說:“明天換個人來,他們同樣那么笑。”
“噢噢。”朋友似乎聽明白了。也許并不明白,因為“噢”完了,并沒合上嘴,依然張著。
他拍拍朋友的肩膀,給朋友提了幾條煙。
“別這么張嘴,拿去抽吧。只是,”他說,“別羨慕我這號人。”
然后,就到了西安,坐了另一把椅子。以做官論,自然是升了的。
卻偏偏發表了他的“狗論”。當然也是私下發表,對另一個朋友。寫成文字就是:
“做官不是人事,是狗事。對上,你是狗;對下,你和狗。”
憑他的“兩論”,我完全可以猜測,他的做官,一定有過許多糾纏和事故,但我不愿我對他的這一篇追憶是小說,不能用猜測和臆想來敷衍。他這一面的糾纏和事故,在我不知的領域。符馱村的人也不知曉。他的妻子和兒子也未必知曉。沒辦法,只能缺失。只能是“部分”。
這就剩下“符馱村人”了。我所說的復雜正在這里。為了這篇文字,我專門回過一趟符馱村,也去西安找過他的妻子和兒子。
“不是。符馱村不認這個人。”這是符馱人的一種說法。
或者干脆說:“符馱村沒這個人。”
“符馱村人不做符馱人的事,算什么符馱村人!”
他們翻騰出許多事故,以支持他們的“不認”和“沒這個人”。可是——
是不認,還是沒有?
是現在沒有,還是從來沒有?
“不認”就可以是“沒有”么?
若以國家可以開除一個人的國籍比照,“不認”也就可以是“沒有”。但國家有開除一個人國籍的權力,符馱村人有么?
若以國家權力來自人民比照,符馱村人就該有這樣的權力,他們不認,他也就不是符馱村人,可以是“沒有”。
若以人民不能直接行使權力而必須通過政權來比照的話,符馱村并未舉行過表決,村委會也沒有發表過類似的通告,他們的“不認”和“沒有”是不能算數的。
何況,還有另一種說法:
“敢說不是!他狗日的敢說不是!”
支持這種說法的依據很樸素,也很直白:
“他狗日的是符馱村的水土和五谷造出來的!”
這是說,符馱村的水土和五谷滋養了他爸他媽,然后才會有他,和狗沒有關系。拉扯上狗純屬感情用事。
“他狗日的也是符馱村的水土和五谷養大的,養了他二十多年!”
這是說他的成長。
他生于符馱村,長于符馱村,二十多年后才離開符馱村,不認是可以不認的,但說“沒有”,就和提到他的時候一定要拉扯上狗一樣,也屬于感情用事。
還有他妻子:
“符馱村?符馱村是誰?”
還有他兒子:
“別提符馱村。別提。”
我不能感情用事。我是以人事檔案中的籍貫為準的。
我一直很討厭人事檔案,也曾經和幾個同事在一間地下室里整理過所在單位的人事檔案,這一次的經歷使我對人事檔案的討厭升級為厭惡。我厭惡里邊的許多欄目,更厭惡里邊的五花八門的材料,比如學習心得,比如審問一樣的談話記錄,可比如的還有許多。但現在,在我要寫這篇追憶文字的時候,我以為人事檔案里的“籍貫”還是必需的,而且以為,一個人的籍貫是無法被開除的。
他的人事檔案凡有籍貫一欄的,填寫的都是奉天縣符馱村。
二一筐好話
符馱村人的感情用事,不能把他推離開符馱村,他妻子和兒子的感情用事,也不能把他拔離開符馱村,反倒從另一面坐實了他和符馱村的關系。他們之間有著生與死的糾纏。這不是我的推測,我有過去知道的一些事故作證據,也有后來搜羅到的許多事故作證據。
但這樣的糾纏,不是一開始就清楚就明了的。或者說,糾纏是已經糾纏上了,卻彼此并不感到在糾纏。
比如他的出生。以科學的說法,那當然也是一個奇跡。別的不論,單就那多少億個活蹦亂跳的精子,都在沖撞,都在努力,最終穿破卵子的怎么偏是這一個呢?如果是另一個,就該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個生命,另一個人了。這么想下去,是真要讓人驚嘆,也要讓人駭怕的。
符馱村的人不會這么想,也不以為是什么奇跡。娶婆娘就要同房,就要做那樣的事,要舒坦,也要生娃,天經地義。用他們的話來說這件事,分階段各挑一句,就是這樣的:
“某某給婆娘弄上了。”
“肚子腆起來了。”
“快了。”
“生了。”
如此而已,和符馱村所有人的出生并不兩樣。
然后一天天長大。
看上去,符馱村的人像林子里的樹一樣,一棵一棵的,有的挨得近一些,有的離得遠一些,但大致都是各長各的,各過各的日子。但大致也要打招呼或不打招呼,發生碰磕或不發生碰磕。他和來娃就碰磕過。
八歲的他和來娃提著小镢頭去城壕里挖樹根,挖著挖著就發生了口角。
來娃說:“你到別處挖去。”
他說:“別處沒樹根。”
“別處去。”
“不去。”
然后動了手腳。來娃比他壯大,壓倒了他,左右連續一陣耳光,讓他叫爺。
“叫爺!”
他不吭聲。
又一陣耳光。
“叫爺叫爺叫爺!”來娃說。
他咬牙堅持著,不叫,也不動。
也許來娃以為他服輸了,也許來娃感到累了,便松開他,提著籠子要走,或許已經走了,他突然從地上爬起來,掄起手里的小镢頭,照準來娃的小腿肚砍過去。
這是來娃沒想到的。來娃沒覺得疼,以為挨了踢,回頭看他,或許想著再一次壓倒他。
但血流出來了,也終于感到疼了。來娃捂著流血的小腿肚坐下去,“哇”一聲哭了。
來娃媽來了,看著來娃的腿,然后又看他。
他提著小镢頭,也看著來娃媽。
“你你你……”來娃媽顫著身子,口齒有些不清。
來娃爸也來了。
他看著來娃爸,以為要挨打了。
沒有。來娃爸像不認識他一樣,看了他好大一會兒,然后說:
“土匪。”
來娃爸抱起嚎叫的來娃了。來娃爸扭過頭,又說了一聲:
“土匪!”
然后,和來娃媽一起跑著給來娃療傷去了。
類似這樣的碰磕,符馱村都記得的,也會提起,只是,在不同的場合,因不同的心情和態度,說法也就不同。
比如,他帶著勤務員回符馱村探親的時候,他們是這么對他說的:
“能下手就能成事。所以毛主席坐牢了江山。”
來娃也在場,連連點頭,說:
“就是就是。”
又比如:
“狗日的心太毒了!小時候就毒,下得了毒手!”
這是在他死后。他們已經憤怒了。他們想起了他們和他的許多事情。也包括和來娃的那一次。
來娃也在憤怒者之列。他滿臉漲紅,摸著終生沒有褪去的疤痕,說:
“狗日的就是!每到下雨天我就腿疼!他個狗日的……”
但在當時,在他砍來娃小腿肚的時候,他們沒有這么說,沒有發現他們后來發現了的意味。來娃和來娃家也沒有。在一個村子里,像這樣打歪鼻子撕破耳朵的事時常會有,何況,來娃敷了幾回藥,好了。
再說到樹上去。
有詩人寫過這樣的句子:
“他們像樹根一樣/糾纏在一起/一個人死了/就驚動全村……”
詩人寫的是村莊,從樹根上得到了靈感。
但人畢竟不是樹。樹根的延伸是有限的,糾纏也就有限。
還有,樹挪了地方呢?挪出了林子呢?是可以不再糾纏的。人卻不一定有樹那么灑脫:
你走了是吧?你是從這兒走的!
你“狗日的是符馱村的水土養大的!”
你能走脫這種干系么?
也有可以走脫的。生在符馱村長在符馱村,然后離開符馱村,然后卻不見有什么氣候,走脫走不脫,在兩廂都無所謂,走脫也就走脫了。事實上,這樣的“符馱村人”也有不少,扳著指頭數,是可以數出幾十個人的。
但他是成了氣候的,做了官的。
在當兵的那些年里,他就把扛長槍變成了挎短槍,帶勤務員回村探親的那一次,就已經挎了短槍,是軍官了。
然后轉到地方,是地方官。然后又許多年,忽兒是這樣的地方官,忽兒是那樣的地方官,不管是什么樣的,從咸陽到西安,就證明是往高處變著的。
在符馱村,不單是“一個人死了就驚動全村”,有可能驚動的還有很多,比如過去的當兵,比如現在的上大學。按說,這完全是個人和他們家的事,但符馱村的人不會這么淡漠寡情。也是戶族的事情。也是全村的事情。
所以,臨走的那幾天,他家里來過許多人,先是家門戶族里的,然后是不是家門戶族里的。女人手帕里包著幾個雞蛋,或者拿幾雙襪墊。男人呢?男人是不拿東西的。他們抽著煙,或者不抽煙,但都坐著,蹲著,沉思著,然后,會給他說幾句話。
比如:“人是要奔大前程的,符馱村沒有大前程。大前程在外邊。”
比如:“聽領導的話,別給咱丟臉。”
比如:“你得了光榮,也就是你爸你媽得了光榮。也就是咱家門戶族得了光榮。也就是咱符馱村得了光榮。”
都是暖心的好話。都是從心窩子里掏出來的,可以裝滿一筐。
在符馱村的人看來,話和東西一樣,是可以送人的。要不然,“你給某某帶個話”,或者,“我只要他一句話”,這怎么解釋?不是東西能讓人帶么?能給人要么?
掏心的話就更是東西了,也許還要比任何東西都要貴重。
當然,他很感動,每聽一句,心里都會忽兒忽地發一陣熱。
當然,他也吃了幾個雞蛋,其余的雞蛋和襪墊留給了家人,然后,穿著一身嶄新的綠軍裝,坐著接兵的卡車走了。
當然,也背著那筐好話。
三另一筐好話
符馱村人在送他一筐好話的時候,是否就存了遙遠的心思呢?
我以為,這樣事后的臆測是不應該的,也有些不善。說給符馱村的人,他們會跳起來的:
“說他媽沒×的話!誰知道他一定能成!”
“存心思也存在我們自家兒女的身上,說他媽沒×的話!”
“說這話就該給他幾個耳光,唾他幾口!”
事實上,每一個當兵走的,都會接到這樣的一筐好話。大多的情形是,當了幾年兵以后,又回來了。符馱村的人和他們怎么樣了?沒怎么樣。最多,有人會有幾句感嘆,更多的是連感嘆也沒有的。
也許在心底最深的那一層里存著吧?只是埋伏得太深,自己不覺得,到一定的時候就會冒出來。
這該是有人說的所謂潛意識了。我沒有研究過潛意識,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東西,符馱村的人是否潛懷著后來又轉而為明,也就無法判定。
或說,就因為潛懷著遙遠的心思,所以才給每一個都送,說不定有一個兩個會成氣候的。
這就是一種策略了,所謂“普遍撒網,重點收獲”。可是,一個村莊的策略該要村人一起研究制定的,符馱村卻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研究。
默契吧?愛人之間有默契,家人之間有默契,村人也該有的。
就算是默契的策略,也不見得奏效。比如劉西奇。
劉西奇是工農兵大學生,由當時的貧下中農推薦,村上蓋了章的,走時也得過一筐好話,后來成了氣候,現在是西安一家大公司的老板。村上修路的時候給他要過錢,給了。蓋學校又去要,也給了。修另一條路再去要,卻不接茬了。村長打電話,他在電話那頭說:符馱村的路是我家的路么?隨后關了手機,怎么樣呢?
“狗日的不認符馱村了!”
“狗日的回符馱村就摧他出去!”
這里的“摧”含有打和推的意思,打著推出村去。
說這話不久,劉西奇就回來過,似乎沒有人真去“摧”。不但沒有摧,還有人和他笑著打招呼呢。
可見,糾纏是有深淺之分的。符馱村和劉西奇之間的糾纏是淺而不深的。
總之,我不愿懷疑那一筐好話的真誠。就算他們懷著遙遠的心思,但首先是希望他好的。他也發過熱的。不僅當時發過熱,在以后的許多年里,也不時會想起這些好話會繼續發熱的。誰敢說這一次次的發熱在他一步步往上走的時候沒起過作用?一點也沒有?
何況,在他倒霉的時候,他們又送過他一筐好話。這在符馱村人的送話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他被“雙規”過一段時間。
“雙規”是個新詞,大意是:在規定的時候和規定的地點交代(也叫說清楚)需要交代的問題。“雙規”只適用于在黨的且做官的人。據說,許多在黨的做官的提到這個“雙規”,就會色變,不尿也要打尿顫的。如果有哪個在黨的做官的突然找不見了,人間蒸發了一樣,沒外逃也沒自殺,那就極有可能是被“雙規”了,等到再現人間的時候,十有八九是要交司法進監獄的。也有不交司法不進監獄卻要開除黨籍撤銷職務。當然,也有沒“規”出問題的,那就回家回單位,繼續為人民服務。
他屬于后一類,因一個案子的牽扯,“規”了一段時間,說清了。
但也變過色,打過尿顫的。
解除“雙規”后,他回了一趟符馱村。盡管他已經越來越少回符馱村了,但這一次,他想回去一趟。
“我回老家一趟。”他說。
“為什么?”妻子問他。
“不為什么。”
“可是,為什么?”
“凡事一定要為什么嗎?”
“唔,噢……”妻子似乎想通了。
“你呢?”
“不。”妻子搖著頭。她對符馱村一直保持著警惕。父母死后,她就不再和他回符馱村了。他一個人回去的。
“啊啊……回來了?”他們很詫異。
“噢噢。”他說。
“不是說……沒事了?”
“沒事了。”
然后,家里來了許多人。有家門戶族的,也有不是家門戶族的。他們抽著煙,或者不抽煙,喝著他哥和嫂子端來的茶水,坐著,蹲著,沉思著,然后和他說話:
“啥叫‘雙規?”
他給他們做了解釋。
“這不和坐牢一樣么?”
“一樣也不一樣。”
“打你了?”
“沒有。”
“屈打成招的事古今都有。”
“我沒有。”
“沒有為啥拉你去‘雙規?”
是啊,為啥?他們想不通了:
“沒有的事為啥要問?沒有的事為啥要拉到那種地方去問?能隨便拉一個人到派出所問人家聽說你是賊你偷沒偷能這么問么?”
然后,他們就得出了結論:
“這不是問人哩,是害人哩!是明擺著臊人臉哩!”
然后,他們憤怒了:
“他們嫖客日的!他們婊子養的……”
這是罵,也是話,但不能推敲。拉他去“雙規”的人未必是壞人,就算是壞人,就一定是嫖客和婊子的后代么?嫖客和婊子的后代就一定是壞人么?嫖客和婊子相遇不是為了生養,有生養是因為不小心,這樣不小心生養出的后代能有多少呢?世上的壞事大多是辦過正經手續的父母生養的人做下的——符馱村的人不知道這些么?知道的。可是……
這就是我說的那另一筐好話么?是的,上邊列舉的都是,包括他們的罵話。如此粗鄙的罵話也算好話么?也算。話的好壞不能以粗鄙和文雅區分。聽這些話,在他不只是感動,也是一種享受。只有符馱村的人才能以這樣的方式給他。
難道能懷疑他們在給他這一筐好話的時候,也存著心思么?
“難說。”這是他妻子的看法。
她緩緩地搖了幾下頭,眼睛有些濕了,又說了一句:
“難說。”
四辯誣
符馱村的人認為他妻子的“難說”是誣蔑。如果把他妻子和符馱村人的說法用對話的形式記錄下來,就該是這樣的:
他妻子:這些所謂的好話是在他解除“雙規”以后說的。“雙規”的時候怎么不說?符馱村的人呢?在哪兒?
符馱村人:你甭問符馱村的人在哪兒,你先說說“雙規”的時候他在哪兒。你知道么?你也不知道!鬼知道他在哪兒!不知道他在哪兒,咋和他說話?
他妻子:家里不能來嗎?
符馱村人:哪個家?符馱村還是西安?問他哥和他嫂子去。多少人去打問過,連來娃也打問過。小時候砍過人家一镢頭也去打問了。為啥要去西安呢?知道他不在家為啥要去西安?就是有一背簍的好話見不著他給誰說去?給你啊?
他妻子:那些天我像掉了魂一樣,流的眼淚能濕透幾個枕巾。單位的人不來了,認識的朋友不來了,符馱村的人也不來了。我是他的家人,不該安慰幾句?
符馱村人:這么說證明你對符馱村不了解,別看你和他過了幾十年可你對符馱村不了解。安慰家人是女人的事。你讓符馱村的女人跑百十里路去西安給你說好聽的話陪你抹眼淚么?這么怪符馱村不是也太過分了吧?憑你那股子嗇皮勁兒,你不怕你家的枕巾不夠要花錢買么?安慰你幾句能咋?能把他從“雙規”的地方安慰回來么?沒問題他才能回來嘛。沒問題他自然就回來了,不是么?
他妻子:要有問題呢?進監獄呢?
符馱村人:這就是兩可的事了。也許符馱村有人會去監獄看他,也許不會。去了也沒好話給他。進監獄就是壞人了。符馱村沒有給壞人說好話的習慣。符馱村對每一個出去的人都千叮嚀萬囑咐,讓他聽領導的話,就是不讓他當壞人做壞事。你要當壞人做壞事符馱村的人有啥辦法?沒辦法。符馱村里沒有國家主席,沒辦法給監獄的人說哎哎他是符馱村的把他放了,就是有國家主席也不能這么做!
他妻子:就因為他沒問題回來了,你們又看見希望了,所以又送好話。
符馱村人:希望錯了嗎?難道你對他沒希望?你會說因為你是他的婆娘。婆娘把希望承包了?別人不能希望了?世上有這樣的理么?按時間算,符馱村的人比你早多了。他在符馱村捏尿泥甩炮的時候,你在哪兒?他在符馱村的麥茬地里灌黃鼠的時候你在哪兒?他在符馱村上高沿低掏鳥蛋的時候你在哪兒?你說你和他生兒育女了,沒錯,符馱村的水土沒養他你能和他生兒育女?你感謝符馱村還來不及哩,別給符馱村的人擺那個婆娘的譜!
他妻子:你們真讓我惡心。
符馱村人:知道你惡心符馱村的人,早看出來了。既然惡心符馱村的人,就別說安慰不安慰的話。
他妻子:沒錯,早就惡心你們了。沒想讓你們安慰,躲都躲不及呢!多少人來過我家?縫紉機自行車買一個拿走一個買一個拿走一個。多少人拿過錢?過去工資少,三塊五塊,后來就三十五十。衣服襪子,什么沒拿過?包括我兒子的鉛筆盒作業本,連鉛筆盒里的鉛筆也不留下。再后來又讓給這個給那個安排工作。你們真會說話!“你侄子在家沒個事干你說咋辦?”“咱兒子中學畢業了沒考上你得管。”你侄子咱兒子,多親!多動聽的話!
符馱村人:再動聽也沒打動你,證明還不動聽。去過你家的人有幾個沒看過你的臉色?你惡心符馱村的人,符馱村的人也惡心你呢!所以,有好話也不會給你說,他不在,也沒人去你那個家。去干啥?看你的臉色啊?說實話,你的臉并不難看,可你的臉色咋就那么難看呢?一見符馱村的人,你的臉色咋就那么難看呢?
他妻子:幾十年我們家成什么了?全讓你們攪亂了。
符馱村人:全是符馱村人攪的?符馱村的人拉他去“雙規”了?你這話說得太欺人了吧?咋個亂?不能吃飯睡覺了?不能屙屎尿尿了?不能生兒育女了?你們家你們家,這話也夠動聽的。如果和你較著勁兒說,你可別嫌難聽。他是你男人,你是他婆娘,一個鍋里吃飯,一個床上睡覺,往好聽的說是夫妻關系,往不好聽的說就是肉體關系。他和符馱村呢?是水土關系,血脈關系!
他妻子:是水土關系血脈關系就欠下你們了?就要對你們負責了?就要對全村負責了?
符馱村人:好狗護三鄰,好漢護三村,這是古話。啥是好狗?咬狼的狗。啥是好漢?有情有義之人。一個人成了氣候做了官,該不該給家門戶族給村上人幫點忙解點困?能幫解不幫解成什么人了?你也是念過書受過教育的人,你自個兒想去。你給全中國的人說去,說給全世界的人去!事實也不是你說的那樣,好像全符馱村的人都蒼蠅一樣粘到你家的門窗上了。就說找工作,讓他給七十歲的人找工作了?讓他給三歲的鼻嘴娃找工作了?他確實安排了幾個人,等到再讓他安排的時候,他死毬了,還整了符馱村一把,害了多少人!這話就不說了。人已經死了說了沒毬用。
他妻子:是你們把他纏死的。
符馱村人:啊呸!這樣的話!你聽這婆娘的話。他明明得的是喉癌,咋是符馱村的人纏死的?啊呸!沒聽哪個狗毬醫生說喉癌是人纏出來的。人有這樣的本事?符馱村的人有這樣的本事?有這本事就好了。符馱村人就發財了。符馱村成立一個纏人公司,生意肯定紅火。求他辦點事就是纏了?就算纏吧,符馱村的人也纏過劉西奇,咋沒見劉西奇得喉癌?
他妻子:劉西奇聰明,不吃纏。
符馱村人:他也可以不吃啊。
他妻子:說來說去成他的問題了?
符馱村人:是你先把話說絕的。
……
平心靜氣一點想,符馱村的人說得也沒錯,他是可以不吃纏的。劉西奇一句“符馱村的路是我家的么”就掛斷了手機,他卻沒有。他吃纏了,而且越纏越深,這又能怪得了誰呢?
纏是互相的,纏與不纏,深與淺,是因人而異的。
他為什么就不能和劉西奇一樣呢?
“是啊,我至今也想不通。”他妻子說。
又說:
“他也是,到死都沒想通。”
可見,他妻子也承認他有問題。
五關鍵詞
婆娘
一個人成為另一個人的婆娘,是偶然的還是必然的?說不清。
退回去幾十年,還在當兵的時候,他是訂過婚的,是鄰村的一個姑娘。他們遇過面。父母問他咋樣?他說我不知道咋說。哥嫂說好不好總有個感覺吧?他說沒覺得好也沒覺得不好。他走了以后,家里開了一個家庭會,統一了看法,以為他不好意思其實是有些滿意的,萬一他當兵幾年沒當出名堂又回來了呢?那就連有些滿意的也找不到了。于是,就交了一部分彩禮,訂了這門親事。但不久,就接到了他的信,說組織上信任他,要培養他,婚姻的事卻只字未提。家里犯難了。萬一組織上要繼續信任繼續培養,進一步信任進一步培養呢?不行不行,這一樁婚姻要重新考慮。父母說這話我張不開口我不去說。只能哥嫂去說了。哥嫂繞了許多彎子,終于讓媒人明白了他們要退婚,也要給出去的彩禮。媒人說定了的事要反悔是不道德的,但婚姻之事和其他事情不同,強扭的瓜不甜強扭也是不道德的,這話我可以給女方家去說,可以退婚,但給彩禮不是強扭的,潑出去的水攬不回來屙出去的屎塞不進屁眼明白么?哥嫂像扭了腸子一樣一臉痛苦,一個說也是也是,一個說明白明白,又給媒人說了些謝承的話,了結了這件事。
果然,他連續幾次得到了組織上進一步的信任,還上了一年軍校。那些年,他的心思都在組織的信任上了,婚姻之事直到轉到地方都沒考慮,所以,那一次回家探親帶的是勤務員而不是婆娘。
到地方上的時候,他已過了三十歲。
符馱村有人說:“他可真能憋啊!”
符馱村另有人說:“志向大著哩!”
但終于憋不住了。也不想憋了。也有了不憋的資本,可以不憋了。他想找一個城里的有文化最好是上過大學的女性做他的婆娘。那時候找對象時興“共同語言”的說法。在他看來,只有城里的有文化最好上過大學的女性才能和他有共同語言。當然,做官的三十歲的童男對女性也是有著很大的吸引力的。
就找到了她,師范學院畢業,在一家中學做老師,小他八歲。
符馱村的人又說了:“啊哈,難怪一直憋著,他想著不吃毛栗,是要吃仙桃的!”
也有人說:“人家能憋住也能憋出成果,有人硬憋,憋到死怕連毛栗也吃不上哩。”
他們說的就是她,他的婆娘。
惡心
有沒有見第一面就對一個人感到惡心的?大千世界無奇不有,不能把話說得絕對。但他妻子對符馱村人的惡心不是一開始就有的,而是在時間和事故的積累中完成的。結婚前和結婚后的幾年里,她對符馱村人不但不惡心,反倒是喜歡的。甚至,在她還沒去過符馱村之前就喜歡上了。每聽他提說到符馱村,她就會產生一種親切感,還會產生無邊的想象。
“皂莢樹真能像鈴鐺一樣響么?”她問他。
“當然,有風的時候,滿樹的皂莢就會響。”他說。
“皂莢真能洗衣服?”
“當然,符馱村的女人都用皂莢洗過衣服。”
“澇池還有水么?有一圈洗衣服的女人?”
“下雨以后才有。”
“那就下雨以后再去,和你們村的女人去澇池洗衣服,不用洗衣粉,用皂莢。”
也會提到某個人,比如來娃。
“他啥樣的?會不會記恨你?”
“不會,小時候的事了。”
“多好的人!”
然后就去了符馱村。雖然和想象中的差距有些大,那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從來都是“看景不如聽景”,人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真去了蘇杭,也會以為走錯了地方,心生疑惑:這就是天堂么?哪怕是西湖,哪怕是三潭印月,哪怕是虎跑泉。符馱村能和蘇杭比么?“我是愛屋及烏了。”她會這樣說。
當然,她也見到了符馱村的人,得到了許多從來沒聽過的贊美話:
“多水靈。”
“白菜一樣。”
“能掐出水來。”
“還有一肚子的學問哩。”
后一句能聽懂,前幾句似懂非懂。就問他。也許是故意的。
“水靈是什么?”
“好看么,歌里也唱水靈靈的眼睛……”
“噢噢,那白菜呢?我是白菜么?”
“是說你年輕,漂亮。”
“為什么不說成一種花?”
“在他們看來,花雖然好看,但不中用。”
“噢噢,那掐出水呢?”
“嫩嘛。”
她覺得他們夸人夸得別致又新鮮。
來娃也見了,平平常常的,抹起褲腿給她看小腿肚上的疤痕:
“你男人用小镢頭砍的。別抿著嘴笑啊,當時口子可深了,血直往外冒。不過,是我先打他的嗬嗬……”
“還疼么?”
“早不疼了,嗬嗬。”
來娃放下褲腿,給她笑著,伸手拿了一顆他和她帶回來的喜糖,扔進嘴里咯嘣咯嘣嚼著。
她覺得符馱村的每一個人都很有趣味。來娃嚼水果糖的樣子也很有趣味。什么是詩情畫意?符馱村和符馱村的人就是。所以,這一段可稱為“詩情畫意時期”。
符馱村不免有人會去咸陽和西安,自然也不免去他們家。開始的時候,她也愿意他們去,遞煙倒茶水,也削蘋果,還有水果糖,走的時候還會抓一把給他們:帶回去給娃們吃。
可是,前街有人蓋房蓋到半截了:
“匠人非要先付點工錢,不付就要停工,萬一下幾天雨我哭都沒眼淚了,想來想去,頭都想破了,就想到你這兒了……”
還有,后街有人給兒子娶媳:
“后天就進門,卻要加兩捆棉花,不給人家女子就不進咱家門你說氣人不?我說棉花要錢買啊都這時候了你讓我給你生錢去不成?我說日他媽不進門就不進門這媳婦不娶了,村上人都勸我說最后這么一哆嗦了千萬別往氣門里走,我就趕緊搭汽車來了……”
還有:“城里鄉下可真是兩重天。你看你娃,上學用的鉛筆寫都寫不完,還有鉛筆盒,我娃見都沒見過,作業本是麻紙訂的,兩面寫……”
還有的還有許多。
她沒有心情遞煙倒茶拿糖果了,不愿聽他們說話了。再有人來,她就躲在臥室里,或者干脆出門去。回來的時候,家里總會少去一樣兩樣東西。
“怎么這樣啊!”
她難以接受了。這一段,可稱為“怎么這樣啊時期”。
然后,他哥看上自行車了,自行車就沒有了。
然后,嫂子看上她的縫紉機了,縫紉機也沒有了。
沒有的還有許多。它們大部分去了符馱村,另一些去了他舅他姑他姨一類的親戚家。
“符馱村的人怎么這么多啊!”她說。
“噢么,你不是去過么?”他說。
“你們家怎么那么多親戚啊!”她說。
“噢么,要怪就怪過去不搞計劃生育,像現在這樣一對夫妻只生一個就沒這么多親戚了。”他說。
這就到了“惡心時期”。
“惡心!”她說。
“你說誰?”他問她。
“你家里人!你戶里人!你村上人!他們真讓我惡心!”她說。
“噢噢。”他覺得她說得有些嚴重了。
“也惡心你!”她說。
“噢噢……啊?”他看著她。
這卻是他沒想到的。
六關鍵詞續
肉體關系
在符馱村人看來,夫妻關系就是肉體關系,肉體關系也就是夫妻關系。貓可以叫咪咪,咪咪就是貓,一樣的。
你要問:婚外情呢?是肉體關系,卻不是夫妻。
他們會說:那叫不正當的肉體關系。
你再問:一夜情呢?
他們會說:那叫一次性肉體關系,要付錢的話,就是嫖客和婊子的關系了,這下你明白了吧?
所以,他們辯誣就可以說:“他是你男人,你是他婆娘,往好的說是夫妻關系,往不好的說就是肉體關系。”區別只在于,一個是文雅的,好聽一點,一個是粗鄙的,難聽一些。
是夫妻當然要一個床上睡覺嘍,過性生活嘍。但符馱村沒有“過性生活”這樣的說法。含糊一點的說法是“睡”,明確的說法是“日”。像“日久生情”這樣的詞語,他們也有他們的用法和解讀,可以是:相處久了,就會生出感情;也可以是:肉體關系久了,舍不開了,就成為夫妻。他們對他們的說法很自信:世上所有的夫妻都逃不出這兩樣。
夫妻鬧別扭打架呢?他們說,那就是“日久生事”了。
他妻子和他既有“日久生情”的時候,也有“日久生事”的時候。
他們的“日久生情”是不用說的,想也能想得出來。他憋了那么多年,正是精血氣旺的時候。她呢?不但是城里的,“一肚子的學問”,而且,小他八歲哩!“多水靈”,能“掐出水來”哩!想想,這么兩個人,在床上,也許顧不得到床上哩……如果他們是兩只鳥,就可以用老話說,叫做“戲水鴛鴦”;如果他們是兩個人的組合,就可以用一個新詞,叫做“和諧社會”。至于怎么個“戲水”,怎么個“和諧”,那就只有他們自己知道了。城里不是符馱村,不會有人問他們這號事,他們也不會口無遮攔地把他們的性事活動講述給想聽的人。這也是城里人吝嗇的一個證據。自己的男人自己的婆娘,說說有什么呢?大家樂一樂笑一笑嘛,又不是貪污受賄,說了有人追查你,抓你進監獄。村上也有人問過他,他笑而不答,也是城里人的脾氣。吝嗇吝嗇,沒勁沒勁。
但“戲水”了,而且是“和諧”的,看臉上的氣色也看得出來。
然后就“生事”了。“生事”和“惡心”有關。
那時候的她正在“惡心時期”,偏偏他哥來了。
她躲進了臥室。這個時期的她已經不愿見符馱村的任何一個人了,包括他哥。但客廳里的動靜是能聽得見的。
他哥蹲在客廳里的茶幾跟前抽著他遞過去的紙煙。他哥每次來他家都這么蹲著抽紙煙,和他說話,說他坐不慣沙發。但這一次,他哥連抽了幾根紙煙,卻沒說一句話。他問他哥咋了?他哥說不咋不咋。他說不咋你咋不說話?他哥說想好了再說。他又給他哥點了一根煙。他哥抽了一陣想了一陣,說:你嫂子冬天給幾個娃縫衣服做鞋納鞋底,手都裂口子了,干疼干疼的。他說噢噢,給我嫂子帶幾盒凡士林回去抹著潤手。他哥搖搖頭,說:今年抹了明年還得抹,治表不治本。他不知道怎么才能治本。他哥說:你家三口人,不干重活,省衣服,縫紉機整天閑著不用是不是?他明白了。他說噢噢,用還是偶爾會用的,當然了,我嫂子……
臥室里的她一直惡心著,突然又一陣惡心,想吐了。
“唔啊!”
他聽見了,進來問:“咋啦?”
“唔啊!”
他哥不抽煙了,站到了臥室門口,驚恐地看著她,問:
“病了?”
“唔啊——哇!”
她捂著嘴跑進衛生間,吐了一陣,吐出來幾口酸水。
他跟到衛生間,“要不要去醫院?”
她擺著手。漱口了。又回臥室了。
當然,惡心以至于嘔吐是攔不住縫紉機的。
她坐在床邊,一直坐到晚上。
他進來了,挨著她坐下,用一只胳膊抱著她的肩膀。
“吐了?”他說。
她的眼眶里似乎涌著淚水,她把他那只充滿關切的胳膊摘開了。
“你我兩個人一個月的工資還得不吃不喝你知道不?”她說。
她的眼眶里涌滿淚水了。
“知道,可是……”他說。
他又一次伸過胳膊去,被她擋開了。
后來,這樣的惡心以至于嘔吐的事故還發生過多次。他一直以為人煩人的時候說“我惡心我想吐”只是一種情緒反應,生理上的惡心和嘔吐只有看見什么不堪入目的穢物或生病的時候才會有。他妻子糾正了他:心理上情緒化的惡心是可以轉化為生理反應,會真嘔吐的。
一個惡心并嘔吐過的人能和他戲水和諧么?就算她已經惡心嘔吐過了,睡到床上了,可是,她會想起她的嘔吐和為什么嘔吐的。就算她撥著他的胳膊說算了算了東西已經拿走了再想就是和自己過不去了,可是——
“想要就直接說啊,拐彎抹角繞來繞去你別動我真讓我惡心!”
這不又想嘔吐了么?
他知道她說的是他哥,又扳她的胳膊了,“算了算了想要東西難張口都這樣的。”
“憨憨厚厚扭扭擰擰可憐兮兮一個模式,好像一個學校培訓出來的一樣的模式別動我,真讓我惡心!”
這不又想嘔吐了么?
他知道她從他哥想到其他人了。他放棄了動她的努力。
此夜沒有肉體關系。甚至許多夜都不會有。人不是機器,沒有電閘也沒有開關,說不想就能不想?說不惡心就能不惡心么?
當然,兩個人的肉體關系或者性生活發生問題的原因不會是單一的,惡心也不一定都會引起嘔吐,摔門摔碟子摔碗同樣會影響到肉體關系。
當然,不能說他們所有的肉體關系問題全都是符馱村的人造成的,我說的只是和符馱村的人有牽扯的部分。她妻子辯誣說的“我們家成什么樣子全讓你們攪亂了”,其中就包括肉體關系問題,說“全”是不符合事實的。
當然,他們也并沒有完全杜絕肉體關系,因為有時候他們彼此也會想的。他們都是正常人,正常人身體里生長的東西他們也會生長,包括性沖動。實際的情形是,他們的性生活是在“生情”和“生事”之間穿插變換不斷反復的,一直持續到他查出患了喉癌之后。他化療過很長時間,她陪床。在此期間,他們也有過想的時候,但不能。她知道他時間不多了。她很可憐他。她想幫助他,安慰他。她用手。完事之后,她給他掖被子。他說“謝謝你”,臉上帶著笑,聲音虛弱到幾乎聽不見。她捂著鼻子流淚了。他也眼淚汪汪,又說了聲“謝謝”。她哭出了聲。她說你別說了別說了好不好,他就不說了,閉上了疲憊的眼睛。
這也算一次肉體關系么?如果算,卻是不可以用戲水與和諧來言說的。她又一次想到了符馱村,因為她認為他的病和符馱村的人有關。她又嘔吐了一次。
沒想通
這個詞是從他妻子辯誣的話語里拎出來的。
他妻子:“我至今也想不通。”
還有:“他到死都沒想通。”
就是說,他們都想過,無數次地想過,想得很痛苦。不但各自想,也一起想過。不說別的,只憑他們對正常的性生活的需要這一點,也應該在一起努力地想一想。
她:“他們為什么要這么纏你?”
他:“他們不以為這是纏。”
她:“這個來要錢,那個來拿物,這個要安排,那個要工作。他們以為很容易是不是?把我們家攪成這樣子他們想沒想?這一切都是應該的是不是?你欠他們什么了?欠了么?”
他:“他們認為是容易的,也是應該的。把我們家搞成什么樣子他們不會想的,也想不來。這也不是欠的問題。”
她:“是什么問題?”
他:“說起來太深奧。要細想能把頭想破。”
她:“你不理他們不行么?他們能把你吃了去?”
他:“吃是吃不了的,可是……”
她:“你就不能像劉西奇一樣么?劉西奇能做到你為什么就做不到?你壓根就沒想從這種糾纏里拔出來!”
他:“我不想?我天天都想!一見老家的人我的頭轟一下就大了,比身子還大。我也恨我自己,恨我為什么不是劉西奇。我擰過我的大腿,揪過我的頭發,你信不信?可是,人和人是不一樣的,我想拔卻拔不出來。所以,你惡心他們,也惡心我。”
她:“就是。這么糾纏著,也有你的問題。”
他:“你想沒想過你呢?你是我妻子,我想拔拔不出,很痛苦,你至少該理解一點吧?可是,啪一聲,門甩上了;啪一聲,碟子碎了;唔——哇!你惡心你嘔吐了。然后,連你的胳膊也不讓動了……這不也是糾纏么?”
她:“怎么怪到我了?”
他:“不是怪,是說他們和我的糾著纏著然后又變成了你和我的糾纏。”
她:“沒有他們和你的糾纏,我就不會。”
他:“沒有和他們的糾纏,我還算人么?你愿意和不是人的人做夫妻么?”
她:“劉西奇是不是人?”
他:“以符馱村人的眼光看,他就不是人。也不僅是符馱村人的眼光。我說過了,這很深奧。”
她:“沒辦法了?”
他:“沒辦法。”
她:“就這么你纏我纏要纏到什么時候?”
他:“不知道。”
她:“沒盡頭了?”
他:“有還是有的。”
她:“什么時候?”
他:“我死了以后。”
她無語了。她反省了一陣自己,覺得自己似乎也是有問題的。但是,她又有些不服氣。
她:“我盡量不糾纏你,可我控制不住了咋辦?”
他:“我盡量往出拔,可我拔不出來我咋辦?”
她:“那就互相纏著吧,往死里纏。”
他:“也只能這樣了。在官,是人也是狗;在符馱村,是人也不是人。”
這是訴苦,也是感嘆。在他看來,人不一定是世界上最聰明的動物,但卻是最復雜的,牽扯的東西太多太多。就他自己吧,僅和符馱村的牽扯就已經復雜到了說不清也想不通。他掙扎過,或者說一直在掙扎。他沒給妻子說謊。他無數次下決心要和劉西奇一樣,可他做不到,也說不清想不通為什么做不到。
他甚至憎恨自己,因為他沒法憎恨別人。別人都是有理由的,甚至是天經地義的,比如符馱村的人,比如妻子,比如拉他去“雙規”的人。所以,他只有憎恨自己,也只能憎恨自己。
在他妻子撥開他的手不讓他動她的時候,他想過自殺。這并不夸張,人在想不過的時候,拿別人沒辦法的時候,尤其是拿自己的親人沒辦法的時候,就會有這樣的念頭,用消滅自己以驚醒和懲罰親人,讓親人后悔。但生命是一次性的,死了就不會再活過來。就算親人驚醒了后悔了,愿意讓你動她了,而你已經死了,沒法動了,也就沒法享受自殺的成果。你說我已經死了也就沒欲望也不會想去動誰了,后悔讓她后悔痛苦讓她痛苦去吧我管不著了,那你算人嗎?自己解脫了把永久的痛苦留給親人你還能算人嗎?你說死了的人是無所謂人不人的我還是自殺吧,那你就得有自殺的勇氣。事實證明他沒有這樣的勇氣,因為他沒有自殺。
他擰過自己的大腿,很疼,就不再擰了。在皮肉之苦和精神折磨之間,人更愿意忍受后者。
他也揪過頭發。揪過兩次。第一次揪下來二十三根,第二次揪下來十三根。查出喉癌住院化療以后,他還有過揪頭發的沖動,手伸上去,卻沒有頭發可揪了。他很后悔他沒保存那三十六根頭發,要保存下來就好了,可以拿出來看看。可是,那時候他怎么能知道他會化療呢?就算知道要化療要掉光所有的頭發,一個正陷身于糾纏的人,一個因糾纏而讓自己和自己也糾纏著的人,怎么會有這樣的雅興呢?有雅興會這么揪頭發么?
關于兩次揪頭發的數量問題,即第一次多第二次少的問題,他是能想通的。第一次的揪在上世紀的九十年代,他四十多歲,頭發還算茂密,一把揪去,揪下來二十三根并不算多。第二次揪已是跨世紀之后了,十幾年的時間,日復一日的人狗變換,符馱村的這個那個,肉體關系的時有時無,諸如此類的因素再加上年齡的原因,頭發由密而疏,由蓬勃而蔫軟就是自然的了,除了自揪下的那二十三根,其他的均為自行脫落。到第二次揪的時候,他的頭發幾乎已到了要“地方支援中央”的境地,每次去美發店洗頭理發,他都會委婉地提醒服務生要小心對待他的頭發。如此境況下的自揪,數量的減少該在情理之中。當然,揪的時候本就潛存著憐惜,也是可能的一個原因。
他想不通的是,自揪頭發是因為糾纏而情急,情急之下能自揪頭發,為什么就不能從那個使他情急的糾纏里自拔呢?
還有,大部分的頭發是自行離他而去的,各類的糾纏為什么就不能和頭發一樣呢?
還有,可揪的東西還有許多,比如鼻子,比如耳朵,為什么不揪鼻子耳朵而要揪頭發?尤其是第二次的揪,頭發已經很少了,怎么揪的還是頭發?
還有,兩次揪頭發之后為什么要一根一根地數呢?
硬要解釋的話,只能是:頭發可以揪下來,耳朵和鼻子則不可以;頭發是能自行脫落的,那些糾纏則不能。至于為什么要數那幾十根頭發,似乎是硬解釋也解釋不了的。
七木牌戰略
第一次揪頭發和他侄子有關。第二次是因為符馱村的請愿談判團。
他侄子叫萬利,長身體屬于那種偏重橫向發展的類型,長智慧也有些特別,處理人事往往會想出一些出人意料且行之有效的點子,但念書卻不太靈光,考試成績總在及格不及格升級留級的邊沿上徘徊。以他哥他嫂子的判斷,這孩子不是念書的料,但可以做事。基于這樣的判斷,在兒子考大學落榜之后,他們就不想讓他復讀了,就給萬利說萬利萬利你別復讀了復讀還是個考不上你干脆做事吧你說呢?萬利說我也是這么想的你們到西安找我大大去。
他哥和他嫂就提了二斤菜籽油,去了一趟西安。
他哥他嫂子去西安找他總要提一些掛面菜籽油一類的東西。這一回是菜籽油,二斤,不算多,但掛面菜籽油一類的東西是不能以斤兩論輕重的。也不以他妻子給不給臉色決定提不提的,因為:“我是提給我兄弟的。”
自然,他知道他哥他嫂子是有事要說的,給他嫂子倒上茶水給他哥遞上紙煙點著后,就等他們說話了。
“我和你嫂子是為萬利來的。”他哥說。
他嫂子正吹著茶杯里漂浮著的茶葉,趕緊抬頭給他一個笑。
“就是就是。”他嫂子說。
他問萬利咋啦?他哥說你看你咱娃今年高考你都不關心。他嫂子說就是就是你是他大大你不關心。他說噢噢事情太多都暈頭轉向了考得咋樣?他哥說落榜了。他說噢噢。他哥說沒考上。他說噢噢。他哥說我和你嫂子就是專程為這事來的想聽你個意見。他又說了一聲噢噢,然后想了一會兒,說:
“要問我的意見,就讓娃復讀,明年再考。”
他哥連搖了一陣頭,說,不成不成不是念書的料復讀也是浪費時間浪費錢。他嫂子說就是就是萬利也不想復讀。
他說:“讓萬利來我和他說。”
他哥和他嫂子一起搖頭了,說,他愿意來我們就不來了他狗日的不愿意來他想讓你給他找個工作。
他說:“噢噢,找……”
他哥沒等他說完,就截斷了他的話。他哥說萬利的想法也許是對的他不愛念書但能做事你就給他找個工作我和你嫂子就省心了你也省心。他說噢噢那我就想辦法托托人找找關系看看。他嫂子的臉立刻開放成了一朵花,說:
“你把萬利的事情辦了,嫂子把你頂在頭上到縣城南什字轉一圈。”
要說送禮,這就是符馱村人心目中最大的禮。在符馱村人的心目中,縣城南什字就是奉天縣的天安門廣場,不但把你放在了高處,而且是用頭頂著,在那樣的地方轉一圈,世上有比這更重更大的禮么?這樣的大禮只在求人辦事的時候才會送,當然,是預送。事成之后會兌現么?好像沒聽說有誰要求預送者兌現,真要求兌現,那一定是神經出了毛病。
兩個月后,他哥打電話說母親病了,讓他回去。他回去了。母親確實病了,感冒加咳嗽,吃點藥就會好的。他哥說咱媽病是讓你回來的一個原因,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想問問你咱萬利的事。他說噢噢萬利的事我記著哩太忙還沒顧上這得慢慢來。這就聽見了廚房里馬勺的響聲。正在廚房做飯的嫂子扔了馬勺,不做了,回屋里去了。他哥沖進屋里,給了嫂子兩個耳光,然后踩著嫂子的哭叫聲走回來安慰他,讓他別和女人一般見識。他喉嚨里一陣一陣發堵,給他哥“哦”了兩聲。他媽要去廚房給他做飯,他攔住了。他讓他媽好好養病,過一陣他再回來看她。他哥送他出門時還在勸他別生氣。他說不生氣不生氣真生氣的是我嫂子你趕緊回家寬解我嫂子去萬利的事我會想著的。萬利說大大你光想著是不行的你得行動起來啊!
然后就到了春節,他是值班的帶班領導,要值兩天班,就沒回符馱村。大年三十晚上吃完餃子,他和妻子兒子看春節聯歡晚會,電話響了,是嫂子。嫂子說兄弟你真不回來啊我們等了你整整一天你是不是給嫂子記仇了?他說嫂子你誤會了我不是打電話給我哥說過我要帶班嗎?嫂子說可是你在家看節目你沒帶班啊你吃過年夜飯了吧?他說吃過了謝謝家里也吃了吧?嫂子說家里吃不吃無所謂只要你和你媳婦你兒子吃了舒服了就行了你看你的節目吧——啪啦,電話掛上了。他拿著電話半晌緩不過氣,喉嚨又一陣一陣發堵了,然后又牽連到胃和肺以及胸膛里邊的所有器官。手似乎也在發抖。他仰頭對著虛空眨了幾下眼。
“我沒有撒謊啊!”他說。
“確實要帶班啊!”他說。
他妻子把遙控板甩給兒子,說:
“就是不帶班不回去又怎么了?這不是存心不讓人過節嗎?惡心!”
然后,回屋里躺下來,臉朝著墻壁。很明顯,他們的肉體關系又要發生問題了。好不容易有一個可以不回符馱村的春節,他本想著要好好動動她的。
正月十五是可以回符馱村的,原來也有這樣的打算。但妻子不回了。
“不去。我和兒子不去,你也不許去。”
自從進入“惡心時期”以后,他妻子就把“回符馱村”改為“去”了。
“事先說好的嘛。”他說。
“說好的也可以改變。你嫂子不讓咱過節,偏要過。春節沒過好,十五好好過。”
他聽得出來,他妻子的“好好過”里是包含有肉體關系的。
是啊,嫂子的一個電話為什么要剝奪我的節日呢?是啊,從初一到十五,除過帶班的幾個夜晚,其余的夜晚都是和妻子在一個床上挨著的,和欲望與沖動艱苦斗爭著的,身心煎熬著的,為什么就不能有一個或者連續幾個好好的肉體關系呢?
妻子已有安排了:
“白天去興慶公園,聽長安縣的唐韻鑼鼓表演,陪兒子滑冰。”
“好的好的。”他說。
“晚飯后上城墻看燈展。”
“好的好的。”他說。
去興慶公園了,很好。長安縣的老年鑼鼓隊敲出的是否唐朝的宋朝的韻是無關緊要的,管它什么韻呢!兒子也滑冰了,雖然摔了幾次,但很好。
上城墻了,也很好。不但看了燈展,還猜了燈謎。然后,抱著一堆燈謎獎品的兒子說“我累了我要回”。這就更好。妻子的安排也許正是要讓兒子早說“我累了我要回”的。
回家后到上床前的一段可以略去不說,只說上床以后。妻子很主動,沒等他撥她的胳膊,她已經把他的手往她身上拉了,很好很好,往下會越來越好的。妻子雖然惡心了十幾天,但現在不惡心了。不惡心了的妻子自然就有了沖動,何況還有嫂子的電話這一人為因素的加入,就是沒有沖動,妻子也會讓自己沖動起來,她把他的手往她身上拉就已經證明她有了沖動或者要制造沖動。這也就是所謂的“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吧!很好很好,嫂子的電話……
叮鈴鈴鈴——電話響了。就在這節骨眼上,電話真響了!
他們被嚇了一跳,正在動作著的都停了下來。
“不會是嫂子吧?”他說。
“不接!”妻子說。
他不能不接。萬一有突發性事件和風波呢?上邊有通知的,節日期間每個單位不但要安排值班,也要保證所有的通訊二十四小時暢通。正月十五也是節日啊。
他下床接電話時看了妻子一眼。妻子臉上剛剛泛出的紅潮正在消退。但不要緊,如果沒有突發性事件需要處理,如果不是嫂子的惡意騷擾,回到床上,紅潮還會再泛起來的。
不是單位打來的,也不是嫂子,是侄子。
“是萬利。”他扭頭給妻子說。
妻子立刻把頭扭向了墻壁。
萬利說大大我知道你已經睡了也許沒睡正看電視可我睡不著全家都睡不著都在想我的事。萬利說大大事實證明你對我的事是漠不關心的我必須采取行動讓你關心。萬利說我所說的行動很簡單我做個木牌子寫上你的名字也寫上我的名字并寫清這兩個人的關系我掛在胸膛上去西安啊。萬利說大大我知道這么做有些丟人現眼可我已經丟人現眼了也無所謂了。萬利說大大你在西安做官我在符馱村沒事可干符馱村的人怎么看我怎么看你這不叫丟人現眼嗎?萬利說我沒準哪天就提著木牌子來西安了大大你可聽清了我說的是提不是掛。萬利說我先提到西安讓你看看掛不掛就看你嫌不嫌丟人現眼了。萬利說人活臉樹要皮傷我的臉也就是傷你的臉因為你是我叔父你要覺著無所謂不怕傷臉我就真掛在脖子上每天在你家院子在你單位門口轉悠直到你把我的事落到實處。萬利說大大你要生氣了硬狠著心不落實我就一直轉悠下去我說到做到哪怕轉悠到死也不后悔。萬利不緊不慢心平氣緩地一連串說了許多。
電話聽筒是怎么放回去的,怎么回到床上的,和妻子有沒有發生肉體關系,他一概記不得了。能記得的只是喉嚨一直被什么東西堵著的那種感受。
許多天以后,萬利推開了他辦公室的門。萬利說我沒去家里是怕我嬸子不給我開門我知道你家門上裝著貓眼。萬利提著一個包袱,解開來是一塊牌子,確實寫著他說過的內容,只是把“大大”寫成了叔父。萬利說寫成叔父是為了讓所有看見的人都能看懂。
他想罵萬利太不要臉,又覺得沒用,要臉就不這么做了,所以,就咽了一口唾沫,說:
“你這么做我就不認你這個侄子。”
萬利說:“我現在還沒做,真做了也就不怕你不認了。你不認我就不是你侄子了?這是老天安排的,人是沒辦法改變的,國家主席也改變不了,你的官沒有國家主席大吧?”
萬利又拿出一套破舊衣服,說:“我掛牌子就穿這一身。”
又拿出一個干糧袋,說:“我不要你管吃管喝,我吃自己的,吃完了回符馱村再拿,來回都掛上這塊牌子。”
他問:“你這么做你爸你媽知道不?”
萬利說:“他們攔不住我。”
他咽了幾口唾沫,說:“你先回去吧。”
萬利很理解的樣子,說:“我這一次來也沒打算就掛牌子,我只是想向你表示一下我的決心。”
萬利用包袱包好牌子,收起破舊衣服和干糧袋,出門時又說了一句:“大大你放心,不到必要的時候我不會真掛的。”
萬利給他笑了一下,拉上了門。他聽著萬利走了。他直直地站著。
“唉!”他突然叫喚了一聲,手抓到了頭發上,卻并沒有揪。
“啊!”他抓著頭發,跺了一下腳。
“唉啊!”他又叫喚了一聲,這才揪了。
他緊握著揪下來的頭發,想著他侄子和那塊牌子,想了好長時間,然后就不想繼續想了。他想他要繼續想的話還會叫喚的,還會揪的,不叫喚喉嚨憋得難受,不揪頭發心里發急,再這么叫喚著揪著說不定會有更嚴重的事情發生。
他坐在了沙發上。他伸開手,看著手心里的頭發,一根一根數著,是二十三根,長短不一。他把它們倒在另一只手心里,又數了一遍,還是二十三根。沒有更嚴重的事情發生。他朝它們吹了一口氣,看著它們飛向各處,飄落下去。然后,他拍拍手,坐到了辦公室后邊的椅子上,端起茶杯一口一口喝茶水了。
萬利的木牌子沒有派上用場,因為萬利到底在西安做事了,成了西安人。當然,是他給落實的,這倒不是因為駭怕萬利真的實施木牌戰略,沒有木牌戰略他也要想辦法落實,為什么呢?就因為他是萬利的大大。萬利說得對,這是老天爺安排的,國家主席也改變不了。
萬利也許早忘了木牌子的事,也許記著,只是不再提起,但符馱村的人卻時不時會想起,會說到的。正因為時不時會想起會說到,忽兒就受了啟發,就有了十幾年后的請愿談判團。
八談判
是人都有眼睛,但眼界不同,有人看得遠有人看得近,有人看得細有人看得粗。也有人看世界太紛亂覺得煩心就干脆閉著眼睛不看了糊里糊涂往前走,符馱村的人就叫做混世界。他是做官的,不可能閉著眼睛混世界,是要看的,但是否看得不太細致呢?比如,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中國發生了多少大事情,他當然是看到了的,但符馱村呢?符馱村不是世外桃源啊,是中國的一個村子啊,中國發生的許多大事情會在符馱村引起反應并造成影響的。對別人,符馱村可以忽略不計,但對他,一個和符馱村有牽絆的做官的人來說,是不能忽略的,因為中國的變化牽扯到符馱村,繼而也可能牽扯到他。后來發生的事故證明,他沒有看到這一點,當符馱村的請愿談判團坐到他家客廳的時候,他竟然一時驚愕得不知道該張大眼睛還是該閉緊眼睛了。他沒有這樣的精神準備。
快速發展的商品經濟使符馱村的人種地不掙錢反要賠錢了,有人氣不過干脆“日他媽”撂下不種了。像火車不斷提速一樣的城市化進程使符馱村一些年輕人去廣東一帶打工了,時不時會寄錢回來,看得另一些人眼饞心熱了。怎么辦?都去廣東么?
有人想到了萬利和萬利的木牌子,想到了他。
然后就有了:“何必舍近求遠呢?遠就是廣東,近就是西安。”
然后就聯絡了一伙人,去找黨支部書記兼村委會主任趙互助,要求趙互助出面去西安找他。他們認為這不是解決一個人的問題而是解決許多人的問題,應該由村委會出面。
趙互助想了一陣,說:“這是好事情,為啥?村上閑散著的年輕人是潛在的不安定因素,有人已經開始偷盜搶劫了。聽說也有人吸白面了。能給一部分年輕人找個正經出路,當然是利國利村利民的好事情。但是,”趙互助又說,“這事情雖然牽扯面比較大,但沒有牽扯到每家每戶,說到底還是私人問題,所以,村委會出面不合適。”他明確表示了他本人的態度:不參與但不反對。
他們說你不參與你啥都合適著哩你當然不參與。村委會不出面我們自己組織起來去西安找他總可以吧?你幫我們出主意想辦法總可以吧?不出主意不想辦法幫我們判斷一下總可以吧?趙互助說判斷當然是可以判斷的。然后,就把他們想出的辦法在腦子里倒騰了一陣,說:
“第一,萬利可以用木牌子給他施加壓力因為萬利是他侄子,有血親關系,你們沒有萬利的優勢。第二,你們一伙人去西安成群結隊浩浩蕩蕩像請愿示威,這恐怕不好吧?請愿示威要挨戳的。”
他們笑了。因為趙互助說的兩點他們已經想過了,也解決了。第一點是上官月解決的。上官月讀了大半輩子《論語》,是有說法的:中國人講究血親姻親,也講究族親干親和朋親,我們拉扯不上前兩親,后邊的幾個親是可以拉扯上的,比如來娃,小時候一起耍大的,挨過他一镢頭,沒記仇沒結冤,不是族親算朋親總該可以吧?關于第二點,高文革當場給趙互助作了說明。他曾經和普選打過官司,經見過法律。他說我們不打牌子不舉旗子不去省政府而是去我們村里人家里,對的是個人不是政府,就不是請愿示威,不犯法律。
趙互助也笑了,說:“還是請愿示威嘛,給人家施加壓力嘛。人家不報警你們就不犯法,要報警一樣犯法挨戳。”
他們說壓力當然是要有的,找他就是要給他壓力他會報警嗎?我們求他辦事和他說情說理他會報警?我們找他最多能說成協商和談判他就是報到公安部也不能說成犯法。
但還是把原來的想法作了調整,不浩浩蕩蕩了,選五個人做他們的代表。他們對請愿談判的復雜性作了充分的考慮,有三個人是不能不去的,他們是:熟讀《論語》的上官月,打過官司懂得法律的高文革和挨過镢頭不記仇不結冤的來娃。
請愿談判團也應修正為請愿談判代表團。
請愿是好說的,一句話便可說清,幾位代表坐在他家的客廳里,說明來意不管他是張大眼睛還是緊閉眼睛,請愿的意思就已明了。但談判及談判的過程就有些復雜了,怎么說好呢?如實記錄可以是一種方法,可是當時雙方都沒有記錄,只能依據幾位當事人事后的回憶概述了。但概述也可以有多種方法,比如,把他們的談判看成一曲音樂呢?就可以分為幾個樂章。看作打拳或廣播體操呢?就可分為幾套或幾節。這樣概述是否會別致一些呢?但當事的雙方并沒有演奏音樂或打拳做廣播體操,我于音樂和打拳都是外行,也不喜歡廣播體操,別致的想法未必有別致的果實。我在作文,還是以“篇”分述較為合適,當然,偶爾也夾帶一點現場實況——
李知篇
奉天縣人都知道李知,符馱村人當然也知道,從符馱村走出來的他也知道的。李知先是西府游擊隊的骨干,解放后是奉天縣第一任縣委書記,然后去咸陽,然后去西安。上世紀五十年代國家大規模工業化的時候,他負責陜西省的國防工業,先后有上千奉天縣的年輕男女經他的手進入西安的國防工廠,成了公家人,端上了公家的飯碗。當然,李知已是故去的人了,但李知在奉天人的心里活著,是奉天人的驕傲。上官月借用《論語》中的話給李知作了這樣的定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君子也,仁人也。
提起李知并把這樣的定論說給他,意思是很明確的:李知立了自己達了自己,也立了鄉親達了鄉親,你可以也應該和李知一樣的。還有,李知立達了幾千人,我們只要你解決符馱村區區十幾個。當然,君子仁人的標準不在于立達了多少而在于立不立達不達。
當然當然,他說,李知是我的前輩確實了不起確實是君子仁人,我也很敬佩他。只是,現在的情況和李知那時候不一樣了。那時候國家恨不能一夜間就工業化而工業化是需要勞動力的,而農村人大都不愿意去工廠的,他們更愿意在剛剛分得的土地上種莊稼,離不開老婆孩子熱炕頭的。許多人進了工廠吃不了苦又跑回去了,咱村上就有嘛。
這倒是事實,也很丟人的,也很后悔的。劉抗戰的婆娘照明他媽就是跑回來的,想挨毬了嘛,回來的當晚就讓劉抗戰把腿折騰軟了,走路像面條一樣,劉抗戰為此得意了許多天,后來就有了照明,再后來就后悔了。她要不跑回來,照明就是西安人了,兒女也是西安人了。這一次要你解決的人里就有照明的兒子。前車之鑒,后事之師,你可以放心,那樣給人家李知丟臉自己后悔的事不會再有了。至于說現在城里不像李知那時候缺人的問題,我們也相信,缺人的話就不找你了嘛,不給你添麻煩了嘛。我們的意思是,西安城那么大,再不缺人擠進去幾個符馱村的人能把它撐破嗎?撐不破吧?
也順帶著批評了奉天縣人:都記著李知的好卻只說在嘴上,怎么不給李知立碑紀念呢?毛主席對全國人民好毛主席有紀念堂,天天有人獻花圈。這是符馱村人應該從中汲取的,受人恩惠不能只說在嘴上。
官官相護相通篇
這是因為他的一句話引發的。他說現在不是李知那時候的時代他也沒有李知那么大的權力,解決這么多人的工作太難太難幾乎是辦不到的。
談判團的說法是:人和人是相通的,官和官也是相通的。一個人做不成的事人托人合起來就能做成。一個官辦不到的事官托官就能辦到。他們看他一臉怪異的神情,就說,你可能以為我們在說夢話,你要是想一想就不會以為我們是胡說。人不是單個的,是你連我我連他這么連著的,只要下功夫,人托人是可以托到中南海里邊去的。也可以托到外國,和克林頓也能拉上勾的。中國人總有認識美國人的吧?美國人里總有克林頓的親戚同學同事朋友吧?一個托一個,勾不上么?全世界人民是一家,毛主席曾說過這樣的話。現在雖不時興說他老人家也不是他的時代了,但他的話還是對的(上官月插話說,不時興說毛主席但時興說古人了,古人說“四海之內皆兄弟”,和全世界人民是一家一個意思)。人托人能托到美國官托官不能和西安的官們拉上勾么?自古官官相護官官相通,到哪個時代也不會變。你就托一托嘛,托到幾個算幾個,解決幾個算幾個,功夫下到了,也就都解決了是不是?
城鄉比較兼罵文人篇
這是因為他的一句感慨而引發的。
他說:“為什么非要往城里擠嘛!”
他們說:“城里有錢掙。”
“錢不是一切啊。”他繼續感嘆著。
“聽不懂。”他們說。
“錢買不來安靜,買不來清新的空氣,買不來……”
“在我們看來,錢就是一切。全中國的人都這樣看了。錢能買房子買地買媳婦買感情,也能買春,有啥能買啥。有錢啥也不買揣在懷里心情也好啊,你踏踏實實安安靜靜地躺著,咋能說買不來安靜呢?”
“城里有城里的不好。”
“我們只知道鄉下的不好,倒愿意嘗嘗城里的不好。有人愿意和鄉下人換么?他們搬到鄉下,我們住到城里……”
“確實有許多有錢人想過鄉下的日子。”
“那是因為他們有錢了,去鄉下也是找樂,找幾天樂還會回城里的。別說一輩子,真讓他們過一年兩年鄉下人的日子試試。讓他們三伏天割三畝麥起幾天牛圈背幾天麥糠試試。讓他們有兒女上學沒學費去看老師的白眼去。看他們還想不想過鄉下的日子!還有那些狗屁文人寫鄉下這么好那么好,都是不缺錢不愁吃喝的眼睛看的,不缺錢不愁吃喝的手寫的!有哪個真正的鄉下人寫過這樣的文章?沒有!寫這樣文章的人都是路人,走過了看過了覺得好這也沒啥,別說啊,別寫啊,可偏要寫,顯擺自己,還要騙人騙世界。狗日的他們。你在城里呆久了是不是也沾上這樣的文人氣了?可別啊,嫖客逛窯子買春享受了但不會寫文章夸婊子的,婊子本來就沒啥可夸嘛。那些文人是連嫖客都不如的。”
根本篇
你的根在符馱村你不會不認吧?
當然,他是認的。
全世界人民是一家,符馱村的人更是一家。一九五八年吃大灶全村在一口鍋里吃過幾年飯你也吃過的記得不?不是一家人你離村時能給你送雞蛋襪墊給你說那么多好話么?根連根心連心都希望你好啊(上官月插話:這也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符馱村的人從心里給你鼓著勁)。也常常牽掛著啊。有人正在鋤地鋤得腰疼了扶著腰忽兒就會想起你的。這樣的牽掛可以從符馱村搜羅出一大堆。為什么牽扯?一家人啊。你要是能把你和符馱村說成兩家,我們立馬就走,不和你費口舌了。
“當然,一家人還是一家的話還是可以這么說的……”
上面是從“根”上說的,你認了就好不認也沒關系我們還要和你說“本”。本是啥?本錢啊!你別這么受驚了一樣看我們,你沒拿過符馱村哪個人的錢符馱村的人也沒錢給你,但雞蛋呢?襪墊呢?那些掏心掏肺的話呢?你不認為這些東西也是你闖世界走天下的盤纏么?這么說好像成商人了。這也是沒辦法的辦法商人就商人吧商人也是人還是正時興的人呢。君子之道行不通行商人之道也可以。以商人之道,你能給那些雞蛋襪墊和掏心的話還有那么多的牽掛定個價錢么?能算出利息么?話說到這兒我們就抖底子和你說了,總之不管行哪個道我們都要和你有個結果,回去也好給符馱村的人有個交代。
結果是代表團拿出來早已擬好的兩份合同,一份依君子之道,一份以商人之道,實質內容當然是一樣的:他要下功夫托人托官解決符馱村十幾個年輕人的進城問題。
他在兩份合同上都簽了字。他說這兩份合同他都認可。至于代表團離開后他情急之下第二次揪頭發的細節,是和第一次大致相同的,“唉啊”一聲,揪下來十三根。唯一不同的是,他不知道為什么像哭一樣笑了一陣,然后才朝手心里的那十三根頭發吹氣。
九解纏
“在那樣的合同上簽字你不覺得荒唐嗎?”妻子質問他。
“為一個合同的事你這么朝著我吼叫你不覺得可笑嗎?”他也質問妻子了。
“你應該摔到他們臉上去!”妻子說。
“但我沒摔,我簽了。”他說。
“惡心!”妻子拍下正吃飯的筷子,要去洗手間了。
“我沒想讓你惡心,但也攔不住你惡心。”他說,“我應該做的就是不做這個官了,辭官。”
“那怎么成!”妻子立刻扭過身來,似乎不惡心了,“這樣會讓人怎么說?別忘了你是被雙規過的,你不做了讓人怎么看?我和孩子讓人怎么看?”
“呃呃,呃!”吃進去的一塊肉丸子卡在喉嚨里了,怎么也咽不下去。
然后就去醫院檢查和化驗,就查出了喉癌,晚期。然后就開始化療,還要做手術。妻子說晚期也要做手術,轉移到哪兒就做到哪兒你們不能見死不救啊醫生!她很激動,眼里噴出的淚水也帶著激動的情緒。
他一點也不感到突然。他甚至為跑前跑后日夜陪床的妻子感到心疼。妻子呢?似乎不但沒再惡心過,反而對她過去的許多次控制不住有些后悔。
“我真是我怎么就那么控制不住自己呢?”她捂著鼻子要哭了。
“我倒是能控制,卻控出了喉癌。”他說。
“嗚嗚。”妻子把頭埋在他的跟前,真哭了。
“沒關系的,別這樣。”他摸著妻子的頭發。
又說:“每一次控制的時候,喉嚨就堵,就想,總有一天會出事的。”
“嗚嗚,我不要你這樣!”妻子說。
“我也不想啊。”他繼續摸著她的頭發。
就在那天晚上,她用手和他有了他們的最后一次肉體關系。他很感謝她,我前邊已經說過了。
但不是所有喉嚨發堵的人都要得喉癌的。
躺在病床上的人,思維似乎比平常活躍,會想到許多,甚至無數次想過的也會再想。比如被拉去“雙規”;比如妻子的惡心和嘔吐;比如萬利的木牌子,還有新近的談判和合同。當然,也會想到癌。這是他正在遭遇或是最終遭遇的要面對的東西。他能推離它么?或者,能從它的糾纏里拔出來么?癌事和人事比,更讓人無奈,一旦纏上,即是劉西奇者流,也難以或簡直就無法推開。但醫生說了,早發現還是可以被摘除的。而他不在此列,是晚發現的,能推開么?
癌的來路和人的來路一樣,至今還是一個未知,說未定也可。它在人不知道的時候在人體的任何一個部位生成并生長,并任意游走,消耗直到消滅人的生命。這是它比人的有力之處。但它是依附于人的,人的消滅也正是它的末日。這或許又證明了它并不比人更有力。
人因癌而痛而恨癌,是把癌沒當作生命(醫生說癌不但有生命而且有旺盛的生命力),或者看作有害于生命的生命。是生命就要生長,也該有生長的權利,包括有害于生命的生命。老虎和雞都是生命,老虎是吃雞的;雞和小蟲子都是生命,雞是吃小蟲子的。都是為了生存。人吃豬吃羊也一樣的。癌吃人也一樣的。生命世界,可謂天經地義,被吃會有痛苦,但何恨之有?中央電視臺的《動物世界》幾乎天天都有這樣的講述,看過的,為什么沒想呢?為什么沒把這些和人事合在一起想呢?也許是還沒遇到癌。
現在想了,也似乎能夠想通。已經遭遇,痛是不可避免的,也可以忍的,恨卻是不應該的,不僅不應該,還要感謝癌的。他做不到的,癌可以幫他做到。
“啊啊?感謝?”妻子驚訝得眼睛要鼓出來了。
妻子摸他的額頭,以為他在發燒。他撥開了妻子的手。在他的記憶中,這是他唯一一次撥妻子的手。他說:
“我忍住了許多,但喉嚨不爭氣,對不起……”
妻子聽不懂,要叫護士。他搖了一下頭。
“也許是我的官做得不大,沒做到北京去。”他說。
說完,又自嘲一樣給妻子笑了一下。
“哪兒跟哪兒啊,你想得太多了。你應該想癌。”妻子說,“你能忍過去的。醫生在努力,你也要努力。”
這回,他沒搖頭,點頭了。
但喉嚨還在堵,又似乎想不通了:我說都說不清楚你,醫生也不怎么能說清,為什么要纏上我呢?就因為你是我生命里的一部分么?
每到這時候,他就會給自己搖幾下頭。
手術前幾天,他讓妻子找了兩頁紙和一個信封,又借用護士值班室給那兩頁紙上寫滿了字,疊好,放進信封,用膠水封了。然后,用手機給符馱村的代表們打了電話,讓他們來一趟。他們來了。
“啊啊你病了?”他們說。
“我簽了字,我該兌現。”他把信封交給了他們。
“病好了再說好了再說嘛。”他們說。
兩頁紙上寫著三十六個單位的地址和聯系人,不知是有意還是巧合,和他揪下來的頭發一樣多少。它們分布在北京上海哈爾濱廣州深圳等十幾個城市。
他們堅持要等到他進手術室以后再回去。他說不用了我婆娘不愿意看見你們事已辦好了你們回去吧再見。他給他們微笑著,送走了他們。
他解決的是三十六個,比他們要求解決的多了一些。如何分配呢?是好事也麻煩。符馱村為此起了糾紛,但最終還是解決了。三十六個年輕人帶著盤纏去了各自分配到的城市和單位。許多天以后,又陸續回到了符馱村,因為他們沒有找到他所列出的單位。有的找到了,但人家壓根就不要人,也沒有他列出的聯系人,也沒人知道他是誰。他們憤怒了。他們去西安找他,他已經被裝在了骨灰盒里,沒法給他們一個說法了。
他狗日的騙了咱!他狗日的知道他活不了就騙人!太惡毒了他!他害我們糟蹋了那么多盤纏!不愿意幫忙可以說啊咋就起這樣的毒心下這樣的毒手!
這也許是符馱村進入二十一世紀至今發生的最大事件。
但憤怒很快就消散了。符馱村立村多少年多少代,比這樣更大的事件不知經歷了多少,不都過去了么?上當受騙當然是不光彩的,可是,誰能做到一輩子不上當受騙呢?
花了盤纏的人是這么想的:盤纏是花了,可也逛了地方,沒有這件事,恐怕一輩子也去不了北京上海哈爾濱。憤怒消散之后,他們也互相交流各自的經見,比如:上海人說話聽不懂;在哈爾濱好像去了外國;北京日他媽可是太大太大了……
為什么不事先打電話呢?這實在是個疏忽。但他給的兩頁紙上沒寫電話。為什么沒想到給他要呢?這也是個疏忽。但人家要做手術,適合么?也沒想到他會騙人啊。
他沒了,他婆娘還在,為什么不找他婆娘理論?他們說,好男不和女斗,也沒人想看她的那張驢臉!
其他的,似乎也再沒什么了。只要不提起,就和沒發生過一樣。
還要說說骨灰。
他曾想過他死后要埋在符馱村的,尤其在經歷了“雙規”事件之后,以當時的心情,是死后一定要葉落歸根的。但后來就不這么想了。喉癌化療期間就不但不這么想,連骨灰都不愿意存留了。他給陪床的妻子說過的。
他說:“我過去想,周恩來周總理把他的骨灰撒在祖國的江河湖海里,是因為愛,很感動的。現在我不全這么想了。我這么一個小人物,都活得這么難纏難解,周總理的難纏難解就不可想象了,不知擰過自己的大腿揪過自己的頭發沒有?他也許厭煩人了,才那么處置自己的骨灰的。我這么想也許很可笑,但我確實這么想了。我不說周總理,我沒資格說他,他是大人物。我只說我自己。我不要骨灰,也不麻煩你去江河湖海,順手倒在火葬場隨便什么地方就行。”
他沒提符馱村。
以后來的情形,他就是有意愿葉落歸根,符馱村的人也未必歡迎。
他們互相唾棄了。
十結語
至此,我的這篇追憶文字該收尾了。但還想寫幾句。
我從來沒想追憶過誰。這么說似乎有些不確,因為我有時候冷不丁也會追憶起某個人,確切地說應該是,我從未想過以文字的方式追憶某個人。現在要作的這一篇文字,完全是因為鐘紅明和肖元敏。我的心臟一直罩在手術后的陰影里,睜開眼疑神,閉上眼疑鬼,說白了就是怕死。我已經相信,人會像忽兒想做一件事情一樣忽兒死去的。“這怎么行呢?”我的一位朋友很為我擔憂,就拉我出門游玩,就游玩到了上海,就見到了她們。她們請我喝茶,當然也聊天,就聊到了符馱村。她們是知道符馱村的。符馱村怎么樣了?這就聊到了他。我一二三四五地給她們說了他的幾樣事故。她們顯得很有興味,一人一句,以為可以作成一篇小說。
“寫吧寫啊。”鐘紅明說。
“能寫好能寫好的。”肖元敏說。
我就有些忘乎所以了。
我在兩種時候容易忘乎所以,一種是喝酒的時候,再就是聽到好話的時候。那天是喝茶,沒有喝酒,這倒不在她們作為地主的吝嗇,而在我的胃。我的胃早就不接受酒精,見酒就讓我疼。我是怕疼的,就不喝酒了。但我并沒有戒聽好話,據我多年的經驗,好話不僅不傷身而且養心。她們像勸酒一樣,一人一句,我的血脈就旺了起來,以為我真像她們說的那樣,不但能寫,也“能寫好的”。
就說:寫吧寫吧。
就說:寫好寫好。
還說了:一定一定。
正應了一句俗話:人都有犯賤的時候。
但不愿是小說。
但又愿意看它的人作小說看。
我沒有能力完全真實地描述一個人或一件事,也從來不相信別人能。就因有這一點,我不相信任何書寫的或口述的歷史。我把所有書寫的和口舌上的人事都以小說對待。對我的這一篇非驢不馬的文字,我愿看見的人也和我一樣的態度。
如果是符馱村的人呢?如果是我要追憶的這個人的親人呢?看出了不舒服呢?要找我的麻煩呢?打官司呢?
我說過了,我寫這篇文字,完全是因為犯賤,我愿意承擔犯賤之責。還有,我犯賤是因為鐘紅明肖元敏的鼓動。她倆是一伙的,在上海,巨鹿路675號。
我一直沒有提及他的姓名,這并不是我的疏忽。姓名也者,符號而已。若以“魯迅浙江紹興周樹村人字豫才”這樣的寫法,反倒落了俗套。
2007.7.25
原載《收獲》2007年第6期
本刊責編關圣力
作者簡介
楊爭光,陜西乾縣人,1982年畢業于山東大學中文系。現任深圳市文聯專業作家,深圳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影視家協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電影家協會會員。電影代表作:《雙旗鎮刀客》等,電視劇代表作:《水滸傳》等,小說代表作:《從兩個蛋開始》(長篇小說)、《黃塵》(中短篇小說集)等。我刊曾選發其中篇小說:《符馱村的故事》。
- 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的其它文章
- 眾說紛紜看《色,戒》
- 羊毛出在羊身上——談《色,戒》
- 空白的空間,蒼涼的回味
- 色,戒
- 老婦與貓
- 噴泉池中的寶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