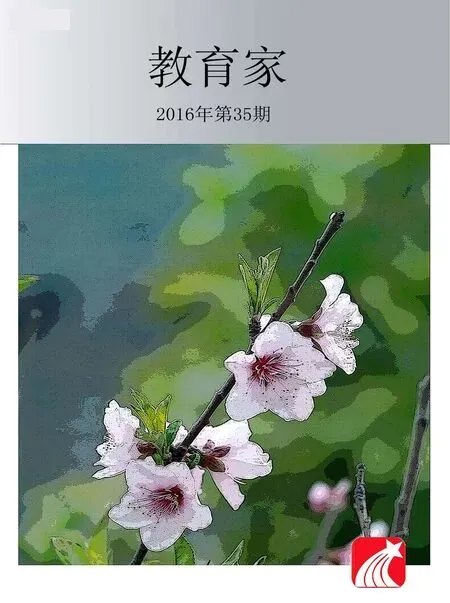掃描
掃描

今年4月以來,教育部協助中央媒體開展了第七屆全國教書育人楷模推選活動。經過各省推薦、媒體展示、公眾投票、組委會推選,日前,共推選出游向紅等10名全國教書育人楷模。
教育部:全國教師管理信息系統明年啟用
近日,教育部在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宣布,我國將于2016年底建成全國教師管理信息系統,開展精準管理。該系統將于2017年全面啟用,嚴重違背師德的情況將被錄入該系統。
教育部教師工作司司長王定華介紹,教師管理信息系統包括教師任職、學歷、年齡、教學情況和師德情況等內容。該系統由全國、省級、市級、縣級、學校層面分層管理,各自擁有不同權限,教師也可以對系統中部分信息進行閱覽或更新。他指出,該系統的建成將有利于開展精準管理工作,提升對教師的服務能力。在義務教育階段,可通過這一系統了解教師的準確情況,有利于推動縣域教師輪崗交流。
據介紹,教師的師德表現在系統中也有記錄,特別是教師的獲獎、典型善舉等情況。同時,違背師德規范的嚴重事件也將記錄在案。王定華表示,對于師德嚴重不良者,在晉級、提職等方面要實行一票否決。
重慶:頒布首個地方性家庭教育法規
日前,重慶頒布了首個家庭教育地方性法規《重慶市家庭教育促進條例》。《條例》共七章四十四條,對家庭教育范圍、原則、內容等做出了明確規定。
《條例》規定,父母或監護人采用暴力、侮辱等方式實施家庭教育的,未成年人可以向學校、父母或監護人所在單位、社區等部門投訴、求助,或者向公安機關報案。公安機關將出具包括加害人身份信息、家庭暴力的事實陳述、禁止實施家庭暴力等內容的告誡書。
江蘇:貧困家庭學子免費上高中、大學
江蘇省自2016年秋季新學期起,對建檔立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將全面免除普通高中學雜費和本、專科學費。
江蘇省教育廳學生資助管理中心主任陳虎解釋,建檔立卡家庭是指按照扶貧部門規定、建立困難家庭相關檔案,并發放貧困卡的家庭。“按照我省今年最新的扶貧標準,人均年收入低于6000元的家庭,都可以在扶貧部門建檔立卡,免除高中學雜費及大學學費。”
長沙:城區小學生上課推遲半小時
日前,湖南省長沙市教育局下發通知,決定從2016年下學期開始將城區小學生早上上課時間由8:00調整到8:30。長沙縣、望城區、瀏陽市和寧鄉縣結合實際參照執行。
《通知》指出,調整小學生上課時間,關系到學生的身心健康,關系到減輕中小學生課業負擔的落實和素質教育的實施,也關系到長沙市委關于城區道路交通“倡錯峰”要求的落實。時間調整后,學校要根據本校實際情況保證小學生每天睡眠10小時和陽光體育鍛煉1小時。